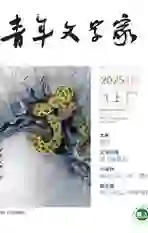雪趣
2025-02-20陈玉珍
小时候,最期盼的便是下雪。当雪色的光芒照进窗棂时,母亲已早早地起来了。她打开炉子盖,加上炭火,再熬上一锅黏糊糊的玉米糊糊,然后喊一家老小起床。
“起床喽……”母亲喊着,随手把早就缝好的厚棉裤、厚棉袄递过来。刚絮好的棉花摸上去软软的,十分蓬松。我和妹妹谁都不想起床,母亲却说:“下雪了,再不起来,就化了!”
听到母亲的声音,我一个翻身爬起来,三下两下穿上棉衣,围上母亲织的围巾,戴上毛线帽,脸都顾不上洗,就听咣当一声门响,人就跑没了影子,只剩下母亲在门后面喊“手套,戴手套……”
然而我们已经听不见了,胡同里落满了雪,一脚踩下去,脚踝都要栽进去了,踩在上面咯吱咯吱地响,地面上就像铺了一层棉被,摔倒了也不疼。我抓起一把雪,悄悄朝妹妹的后脖颈儿里塞,妹妹缩缩脖子,扭头一个雪球就冲我打了过来。
母亲从家里追出来,一边给我和妹妹套手套,一边絮叨:“冻疮还没好呢,待会暖和过来,又要痒了……”我和妹妹却不管那些,挣脱母亲的束缚,继续团雪球去了。各家各户的小孩子都出门了,胡同里的人越来越多,我和妹妹得联手作战了。邻居家的胖小子肉墩墩的,正适合当靶子。前几天因为薅他家鸡毛做毽子的事,可没少和我们吹胡子瞪眼睛。如今,不正是报仇的好机会吗?我暗暗地想着。雪球像雨点一样往他身上招呼,胖墩儿一开始还笑呵呵的,弯腰,团雪球,扔出来,可惜没等砸到我们身上,几个硕大的雪球就已经准确命中了他的大腿和上身,气急败坏的小胖墩儿顾不上回击我们了,左躲右闪,上蹿下跳的,胡同里顿时乱作一团。
满胡同的大孩儿、小孩儿,个个头顶上冒着一团热气,手套湿透了,小手被冻得通红,谁还顾得上冻疮的事呢?
城市的雪,来得快,消失得也快,远不及乡村的雪来得厚实和持久。在乡下,一场雪带来的乐趣远远不止这些。等到雪稍微有些融化的时候,地面上便结了冰,上了年纪的人大都窝在家里不敢出门了,年轻的小媳妇、小伙子可不怕这些,照样在村子里来来去去的,街道上时不时会发出几声咣当咣当的脆响,接着就是一阵哎哟声和哈哈的笑声。路边上的小树笑得花枝乱颤,枝头上的雪扑簌簌地往下掉,从地上爬起来的小媳妇、小伙子,龇着牙咧咧嘴,拍拍屁股上的雪,又哈哈笑着往前面去了。很快,远处又传来一声声悦耳的银铃声。
屋顶上,烟囱周边的雪总是化得最快的。各家门前的雪,也早早就被勤劳的男主人堆到一边去了,倘若门前有几棵树,这几棵树便遭了殃,树根处堆满了雪。不知道谁家的孩子,拿来铲子,几下就堆成了一个大雪人。家里的笤帚啊,塑料盆呀,全都有了新的用途。墙上挂着的几串红辣椒,如今也遭了殃,被拿来做鼻子用了。沿着街道往前走,雪人东一个西一个的,只等放学的孩子来和它玩耍。最小的那个小雪人到哪里去了呢?它只有一截儿短树枝那么大,噘着嘴巴蹲在墙角的花盆里呢!孩子们说,好孩子要学会自己长大。
冬天的场院安静又寂寥,谷子呀,高粱呀,全都归了仓,堆满谷物的粮仓上面,也落满了雪,像个戴斗笠的胖娃娃。地上的雪,化了又冻,和冰块一样了,一到放学的时候,孩子们成群结队地往这儿跑,一个侧身,脚下用力,就能滑出去很远很远。几个孩子,手拉着手转圈圈,一不小心就倒了一地,像掉落的糖葫芦。年纪小的妹妹缠着哥哥,找来一个大纸箱,推着她在冰面上起舞。
玩着玩着,各家房顶的烟囱又咕嘟咕嘟的冒烟了,做好晚饭的主妇们陆陆续续地走出家门,喊贪玩的孩子回家吃晚饭。
屋檐上,冰溜子高高挂,像葡萄一样成串地挂下来,吸引着馋嘴的孩子。一根冰溜子吃进嘴里,嘎嘣脆,比城里卖的冰棍儿还要好吃。有心的主妇敲下几根好的,拿回家里,放热油里炸了,一道油炸冰溜子便上了桌,惹得四邻八舍的孩子都赶来瞧上一瞧。
要是赶上过年下一场大雪,就更有意思了。正月十五雪打灯,一个谷穗打半斤。瑞雪兆丰年,人们赏灯,玩雪,又是一年好收成。
转眼间,很多年过去了。可下在童年里的雪,似乎永远都不会化。一回头,它还在那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