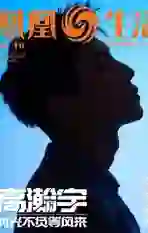情趣的价值
2025-02-13王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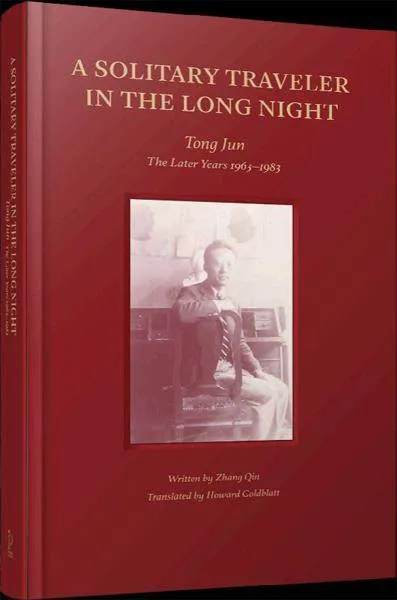
张琴的书《长夜独行者》中文版出版后,她第一时间就寄给了我。我读了之后,就想为童寯先生再写点什么,尽管从1997年开始到现在,关于童先生我已经断断续续写了很多东西。但是张琴的这本小书,丰富了很多我对童先生的认识,而且文字直接简明,情感朴实细腻,也很符合我对童先生的一向感觉,一系列的琐事仍然让我叹息不已。
在我1998年发表在《建筑师》杂志的短文《造园记》里,就引用了童先生在《东南园墅》里的一段文字:“文人,而非园艺学家或风景建筑师,才能善于因势利导去设计一座古典中国园林。他作为一位业余爱好者,虽无盛名却具差强人意的情趣,可能完成这诗意的和浪漫的任务。如果情趣得以强调,在这里要比仅具技术知识重要得多。”在我看来,童先生这么说,不仅只是在讨论对江南园林的一些特殊领悟,这几句看似轻飘飘的话,尤其是这种往往“不合常规”的情趣,实际上足以颠覆中国当时正统建筑学界的所有宏大叙事。而就江南园林本身,读完童先生的文字,得出一个结论:它是中国传统中出现过的最有先锋精神的建筑学。童先生没有这样说,但他用他的后半生践行了这种精神。
《造园记》是1998年发表的,但写作是在1997年。而我看到《东南园墅》,是在1996年。从1996年到1997年,我把《东南园墅》反复读了六遍,经常读到浑身发抖,然后开悟。这就是为什么,当我读到张琴书中关于《东南园墅》的部分,感慨良深的原因。童先生是1983年初在病床上最后截稿的这本书,当他的孙子童文问他,谁看得懂你这本书?童先生流泪了,说,这本书是为30年之后的人写的。我很感慨,13年后,我仔细看了,看懂了,多少可以告慰先生。
但我的“看懂”,也是有一个过程。我尽管一直钦佩童先生的为人,但是,从我1982年第一次在南京工学院建筑系馆中大院的楼梯上见到童先生,到我因为细读《东南园墅》而对江南园林,这个我曾经觉得各个都差不多,互相因袭,审美疲劳,因此坚决不看的东西重新爆发兴趣,也是间隔了13年。
多年以后,重新回忆我第一次见到童先生的情景,不得不感叹人世间确实有缘份这个东西。那应该是1982年,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在中大院从二楼到三楼的中央楼梯上,我见到,不如说是有些冲撞到正在下楼梯的童先生。那时候我读本科二年级,正是年轻,上下楼梯几乎都是飞的。下楼梯一个梯段只需要一步,整个人像鹰一样飞翔下去,上楼梯也只需要两步,速度飞快。我在那里撞到童先生,应该是我的教室在三楼,而童先生正好从三楼的建筑研究所下来。我只记得童先生用他有几分忧郁的眼神严厉地看了我一眼,但什么都没有说。我很快低下头,正好看见先生脚上的那双鞋,很老的牛皮鞋,按张琴书中所写,是一双美国皮鞋,从1949年一直穿到我见到的那个时刻。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童先生,居然也是唯一的一次。
但是从此,我就对和童先生有关的事情特别的注意。很多关于童先生的故事都在师生间流传,或者说,学院里的那些老先生中,如杨廷宝、刘敦桢等,童先生的故事最多。譬如资料室那张不变的座椅。譬如帮助学生画效果图,特别是补树,一挥而就。等等。但我印象最深的是童先生的著作还有语言文字。他的著作文字总是极其简练,是那种带有文言味道的白话文,质朴无华,几乎没有形容词。多年以后,当我开始带研究生,我就要求学生的论文尽可能不使用形容词。读了张琴这本书,我才发现这也是当年童先生对学生的要求。不仅如此,我印象更加深刻的是,童先生对他讨论的问题,总是一针见血,极有独到见解,敢于做出判断,从不含糊其辞,从不捣糨糊。我记得读他的《西方建筑科技史》,对西方传统建筑中的材料、结构与施工方法的演变脉络描述清晰,对我大有启发,再次读到这样有深度的建筑史,是要等到90年代初见到肯·弗兰普顿的《西方现代建筑—一部批评的历史》和他的《抵抗建筑六点》。不过,直到1987年,当我写下那篇引起剧烈非议的文章《破碎背后的逻辑——中国当代建筑的危机》的时候,我仍然对江南园林没有特殊的兴趣,除了觉得童先生那些描绘江南园林的水彩画,实在是画得太好,是我这辈子都望尘莫及的。
我和童先生再续前缘是因为晏隆余老师。那应该是1988年,但我为什么会认识他我就记不清楚了。他那时候是在学校出版社做编辑,并不在建筑系任教。但我这个建筑系著名的叛逆学生就认识了他,并且成为莫逆之交。他曾经做过童先生的助手,所以很多童先生的故事都是他告诉我的。那一年我研究生临近毕业,他就经常请我去他家吃饭,做红烧肉给我吃,让我补充营养。五月份,我论文答辩全票通过,寄了三本出去,给三位我认为值得寄的教授,分别是清华大学的汪坦先生、陈志华先生和《建筑师》编辑部的王明贤先生。汪坦先生1986年曾经在东南大学做过关于西方现代建筑相关理论的六个系列讲座,对我影响很大。陈志华先生的《西方建筑史》有个人激情和文采,我很认同。王明贤先生则因为我1985年在《建筑师》发表论文“皖南村镇巷道空间结构解析”(应该是中国建筑界第一篇用罗兰·巴特式的法国结构主义哲学分析中国传统乡村空间的论文)后,跟我保持着通信联系。
好像是六月,暑假前,晏老师拜托我去一趟北京。他正在负责编辑《童寯文选》,是用童先生1930年代在上海用英文撰写的一批稿子翻译成中文来编辑的。估计是害怕邮寄丢失,他让我亲自带稿子去汪坦先生家,他已经请汪坦先生写一篇序言,并通篇校对全文。另外,他让我再带一份稿子的副本去童先生儿子童诗白家,也请他校对一下。那个时候,我并没有看过稿子的内容,但因为是为童先生的事,而且能够见到汪坦先生,我就欣然前往了。
汪坦先生在家里接待了我,很热情,给童先生的书写序,在他是毫无问题。读了张琴写的这本小书,我才知道汪坦先生和陈志华先生都是童先生老友,1982年童先生去北京化疗,最后一次拜访清华建筑系,他们是拍过一张合影的。谈完童先生的事,汪坦先生就拉着我坐下,问起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的事,论文的题目是《死屋手记》,以先生的学识,他当然知道我借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名字的影射含义。他又说,陈志华先生也收到了我寄的论文,特地让他转告我。今天回忆起来,那一天都说了其他的什么,我都记不清楚了,我只是觉得那一刻很美好,尽管只有汪坦先生在,但是似乎童先生、陈志华先生也都在。我记得很羡慕汪坦先生这个书房,四壁堆满书。房子中央有一棵高大的橡皮树,茂盛的已经挤住屋顶。阳光灿烂,汪坦先生又热情地邀请我一起吃午饭,我那个时候还很土,第一次在汪坦先生家见到烤面包机,至今嘴上还残留着那一天烤面包片微焦的香味。
午饭后,和汪坦先生告别,我又去童诗白家。他不在,但我见到了他的夫人郑敏——著名的诗歌评论家。她让我把稿子放下,就开始问我的硕士论文,并追问为什么要借用《死屋手记》这个名字。我已经完全记不得当时的谈话,只记得郑先生坐在沙发的一张拖地的老虎皮上咄咄逼人的语气。有意思的是,从张琴书中看,对于童先生用莎士比亚式的英文写给她和童诗白的信,郑敏是相当服气的。
今天看来,一切都是过程。1988年秋,我接到通知,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学位委员会开会决定,取消我的硕士学位。我想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论文的名字,因为这些教授应该根本看不懂我的论文。对这件事,我一笑置之。和童先生1950年决定不做设计相比,这不算什么。接下来我就去了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因为当时我觉得那里有更自由的空间。
1990年代初,晏老师经常来杭州,除了聊天吃饭,他还让我帮着正在编辑的《东南园墅》画一些徒手的园林平面插图。有一次的聊天我印象很深,应该在1992年左右,他提到童先生以往讨论园林从来不谈及植物花草,但临终前最后修订这本书的稿子时,童先生希望要补上所涉及园林的主要植物的照片。他谈者无心,我听得有意。突然,我意识到《童寯文选》那句话的价值:“中国园林原来并非一种单独的敞开空间,而是以过道和墙垣分隔成若干庭院,在那里是建筑物而非植物主宰了景观,并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园林建筑在中国是如此令人愉快,自由、有趣,即使没有花卉树木,它依然成为园林。”后来,我在《造园记》中再次讨论了这句话。这对我来说,是建筑观念哲学转折的决定性的开始。这个转折点应该影响了很多后来的中国青年建筑师。而我重新认识花草树木的价值,则要等到2000年后,当我思考中国美院象山校园整体设计理念的时候。
所以,我在1996年拿到的《东南园墅》,应该是晏老师给我的。比正式面市的时间要早。尽管那时候童明已经和我成为同济建筑城规学院博士班的同学,他学规划,我学建筑。我想童明对建筑学的热情多少是受了我的影响。他是一个典型的理工男,但我们住隔壁宿舍,他就经常来一边看我写书法,一边海阔天空地聊天。我那时候在写《散氏盘》,吴昌硕一路的写法,每个字巴掌大小,八尺整张。写完的就满墙贴上。那个时候的字,我毕业后都扔了,但童明说他还保留的有。那一年,当我第一次读《东南园墅》,开篇第一段,当我读到:“当人们观赏一幅中国画卷时,很少会问这么大的人怎能钻入如此小的茅舍,或一条羊肠小道和跨过湍流的几块薄板,怎能安全地把驴背上沉醉的隐士载至彼岸?”我的脑子就轰的一下,我知道,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虚构世界,这是又一个关乎建筑基本观念的决定性的开始。那些时候,我一定经常对童明说他爷爷的这本书有多么重要。也就是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这个时刻,我意识到童寯用自己的后半生实践了自己的思考,一个杰出的建筑师停止设计,转而投入书斋,就如同这样一个有精神高度的伟岸的人,蛰伏在一个小小的茅舍之中。当然,从建筑学的角度,这句话不仅开启了对园林的另一种理解,也开启了对中国山水画的理解:它们都不只是视觉对象,是一种让你进去才能理解的对象,它的核心意义在于:对这个世界的可理解性。
十多年前,台湾的诚品书店要出版童寯先生的《江南园林志》,让我写一篇给读者的推荐短文,我在文中把童先生不做设计比拟为沈从文停写小说,我觉得,童先生不仅开启了对江南园林的近现代研究,更加重要的是,他代表了中国建筑师身上稀缺的风骨,至今意义不减。更有意思的是,这种风骨是以情趣的状态自然流露出来。2000年,我和陆文宇一起在杭州太子湾公园亲手参与建造了我们的第一个夯土作品《墙门》,我后来就一直用元代画家倪瓒的作品《容膝斋图》来讨论这件小作品。前两日,为了写张琴拜托的这篇任务,我又读了一遍她的这本小书,不经意间发现一个小惊喜,我上一次读的时候似乎没有看到。童先生在“文革”期间的一次检讨里写到,他的这种隐逸状态,主要是受他喜爱的元人山水画和明末小品文的影响,特别是倪瓒的画,几棵杂树,一个简单的亭子,隔着水,一抹远山。看来我和童先生还真是意趣相投,气息相接的!
《A Solitary Traveler in the Long Night: Tong Jun—The Later Years 1963–1983》
《长夜独行者:童寯最后的岁月——1963年—1983年》
作者:Zhang Qin(张琴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