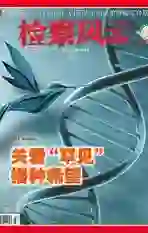新型隐性腐败的依法惩治与履职机制
2025-02-13乔丹
新型隐性腐败是相对于传统腐败犯罪而言,公职人员采用更加隐蔽、复杂、间接的方式进行“权钱交易”的行为,往往隐藏在看似合法的程序、商业活动或人际交往背后,这对司法查处和认定造成一系列困难。
主持人

为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保持打击腐败犯罪的高压态势,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举办“新型隐性腐败的依法惩治与履职机制”专题研讨会,对新型隐性腐败的主要特点、司法认定和检察侦查履职等问题进行研讨。
新型隐性腐败的主要特点
逄政:当前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持续深入,腐败的手段也愈发的隐蔽变形、翻新升级,给司法实践带来一系列难点。在司法实践中,腐败犯罪具体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或行为方式?
袁媛:从近年来职务犯罪案件办理情况来看,新型隐性腐败的特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主体的隐形化。腐败分子从以前传统的站在台前(“一手交权一手收钱”的形式)慢慢站到了幕后,行、受贿双方对于权钱交易的沟通内容往往比较模糊。二是利益输送市场化。比如行贿人以收购技术为名收购了受贿人名下的“空壳公司”,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利益的输送。三是谋利的间接化。比如以参加饭局或出席仪式“站台”,或引荐行贿人和其他人相识的方式来为请托人谋利。四是财物占有的非本人化。受贿人指定行贿人或第三人来占有行贿人给予的好处。五是收受财物形式的非传统化。比如输送股权、分红、预期利益、商业机会等非实物的贿赂。
徐姿:与传统显性腐败相比,新型隐性腐败更具伪装性、欺骗性和迷惑性,危害更加深远。对于纪检监察机关而言,发现和查处的难度更大。
在实践中,新型隐性腐败案件办理存在难点:第一,对新型隐性腐败的类型和认定缺少明确的规定,实践中的线索发现和行为认定存在一些困难。第二,主观明知查明难,“权钱交易”往往采用一种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心领神会的沟通方式进行。第三,行为性质辨别难,新型隐性腐败往往游走在“红线”边缘,呈现出表面“精心伪装”的特征,这给精准识别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新型隐性腐败的司法认定
逄政: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新型隐性腐败犯罪手法的不断升级,目前出现了收受预期收益、行贿人代持等一系列疑难复杂问题。对于这些新的问题,在检察办案中应当如何把握和认定?
袁媛:关于新型隐性腐败的认定主要有三个问题与大家分享。第一个是利用职务便利的问题。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具有制约关系的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能否认定利用职务便利,相关司法解释尚未明确。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的是其职务行为给非国家工作人员带来的现实约束,是公权力的一种自然延伸,应当视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
第二个是关于离职以后受贿的认定问题。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了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在职时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利,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的性质,必须以离职前有约定为前提才能认定为受贿犯罪。但在司法实践中,我们认为,虽然行、受贿双方在离职前并没有约定,但是离职前的谋利行为和离职后的获财行为具有对应性的情况下,也可以认定为受贿犯罪。这个问题的认定思路也可以适用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履职时未被请托,但是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而收受他人财物的,应当以受贿犯罪定罪处罚。
第三个是收受预期利益的问题。目前出现比较多的是收受原始股的情况,我们认为,由于原始股具有购买的稀缺性,购买渠道的封闭性和较高获利可能性等特点,国家工作人员通过为请托人谋利,进而获得本不应当获得的“小投入大回报”的巨额收益,严重违背了一般的市场规律,其行为侵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应当以受贿罪评价。
嘉宾





高静:目前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发现了以下几种新型隐性腐败类型。第一种主要是国家工作人员通过在岗办事、转岗兑现等“期权腐败”的方式来掩盖实质上的“权钱交易”或规避责任。对于此类案件,应侧重于分析企业给予行为人的定制高薪等是否与其在职时为企业所谋取的利益之间存在关联性。
第二种是“预期收益型”受贿。关于收受预期股权的数额认定,有以下几种意见:第一,案发时还未上市,需要通过第三方评估认定尚未上市公司的股权价值,从而认定受贿数额。第二,案发时已上市,可以按照上市第一天的收盘价或最低价认定受贿数额。如果上市之后连续涨停,可以按照涨停板结束开封之后第一天的收盘价或最低价认定受贿数额。第三,如果是在破发状态下,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目前倾向于按照交易时实际获得的数额认定犯罪数额。不过,如果破发导致价值确实很低,也有可能不予认定为受贿犯罪数额。第四,案发时还没有过禁售期,可以根据到案发时的最低价来确定相应的浮盈价值,从而确定犯罪数额。当然,在个案办理中需要综合行为模式、案发时间节点及证据状态来确定最终的受贿数额。
第三种是“收受商业机会型”受贿。如果行为人收受商业机会之后付出了较高的劳动成本,谋取利益主要还是依靠市场交易规则的情况下,很难被认定为犯罪。在司法实践中需要深挖收受商业机会的背后是否具有确定的收益,如果收受后没有付出或者基本没有付出劳务的情况下获取了利益,这种情况下可能会被认定为受贿。
第四种是“放贷收息型”受贿。个人认为,对于是否构成犯罪,在审查中主要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借款人有没有真实的借款的意愿或需求,如果完全没有资金的借贷需求,可能就是以借贷的形式来掩盖受贿的事实,可以认定为受贿犯罪;另一个是调查当地民间借贷的习惯性借款利率,在借款人确有借贷需求的情况下,如果利息明显高于当地民间借贷通常利率,可以根据差额来认定受贿数额。
第五种是“他人代持型”受贿。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可能争议较大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受贿人是否对财物达到实控性的认定;二是既遂未遂的认定,比如收受银行卡案件中,行贿人反悔挂失后,如何认定既遂未遂金额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有待统一思想认识,统一法律适用。
第六种是“定制金融产品型”受贿。行贿人专门为受贿人定制金融理财产品,并将受贿人放在劣后级的层面,但实际上所有表面设定的条件都是为了确保行为人能够安全退出,从形式上来看似乎没有问题。在司法实践中,需要办案人员具备一定的金融知识,对这类案进行穿透式审查,作出准确认定。
检察侦查履职之思
逄政:此前,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成立了专门的检察侦查部门,负责对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非法拘禁罪、刑讯逼供罪等14项罪名进行立案侦查。从检察侦查的角度看,如何突破新型隐性腐败的难点,有力惩治新型隐性腐败问题?
董思毓:从检察侦查的角度看,重点在于在前端将各种新型隐性腐败问题的线索挖掘出来,从源头上查清事实证据,减少起诉和审判阶段的争议。新型隐性腐败犯罪最直接的认定方式就是行、受贿双方都能如实供述,相关证人、书证等如果能够予以佐证,后续起诉、审判认定上争议就比较少。然而在没有口供的情况下,侦查部门需要尽可能将所有案件关联的客观证据、证人证言等都调取完整。
对于新型隐性腐败案件的查处,应重点把握两个方面:一个是“人”的问题。以前可能只查行、受贿的“本人”,现在需要进一步排查直系亲属、朋友甚至同车人、同住人等相关人员,调查相关人员银行账户、行程轨迹,等等。另一个是“物”的问题,也就是财物。传统的职务犯罪案件主要查清行、受贿双方名下登记的各类资产,新型隐性腐败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对隐性资产进行侦查,比如名下房产,是否定期有钱款进账,是否可能是借由隐性房产以租金形式实现行、受贿;比如车辆,行为人日常驾驶的是其名下的汽车,但是否可能在处理违章、保险等事项时对应的还有另一辆车。
总而言之,不管是何种新型隐性腐败问题,核心是“人”和“物”的问题,司法实践要牢牢抓住这个核心问题。
王晶:检察侦查既有追诉权性质也有法律监督性质。就追诉权性质而言,相对于公诉权,检察侦查更具有前瞻性、前置性、主动性和强制性。目前检察侦查工作总体分为三部分:一是直接立案侦查,二是补充侦查,三是机动侦查。直接立案侦查,主要涉及与监察机关的协作配合。总体来说,监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基本是全覆盖的,但在特定的14项罪名中,检察机关也可以直接立案侦查。通过一段时期的磨合,检察机关对于特定14项罪名可以优先办理,需要进一步加强与监察机关关于管辖的衔接配合。机动侦查,涉及与公安机关的衔接问题,目前检察机关也正在稳步、慎重探索。补充侦查,涉及检察侦查同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问题。
总的来说,对于检察侦查,上海三级院要形成合力。相信在反腐败斗争中,检察侦查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
(声明:本内容仅代表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编辑:张宏羽" " zhanghongyuch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