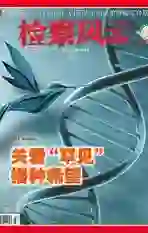应着力推进自贸区数据跨境专项立法
2025-02-13吴玄
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既是为数字贸易的开放与繁荣奠定基础,同时也对数据跨境流动提出了更高的安全与合规要求。
随着数据成为数字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和重要国家竞争资源,大规模的数据流动日渐常态化。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同月,国务院发布《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总体方案》,提出“在上海自贸试验区规划范围内,率先构建与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在全球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如何对标国际数字贸易基本规则、创新国内数字经济制度体系,已经成为各国共同关注的议题。
高标准经贸规则正形成新的“数字壁垒”
随着世界经济高速数字化,大国间博弈的场域也由单一的数字经济发展、技术应用创新等领域扩展到包括数字经贸规则在内的数字时代的全面竞争。各国纷纷加快构建本国数字经贸规则,力图在博弈中占据优势地位。
2024年7月26日,WTO 电子商务谈判达成了一个稳定的《电子商务协议》文本,标志着全球电子商务规则制定取得重要进展,即各缔约国就若干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达成实质结论。该谈判于2019年1月正式开始,目前已有91个成员国参加,占全球贸易总额90%以上。谈判力求在现有WTO协议和框架的基础上,实现高标准成果,并向所有WTO成员开放。各方在3大领域13个议题上达成共识,其结果已经覆盖了大部分数字经贸内容,但仍未触及本地化存储、源代码保护等关键性议题。由于各国在国家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公共利益和监管传统等方面短期内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不大,因而具有全球普遍约束力的数字经贸规则暂时难以确立。
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在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协商过程中正积极抢占主导权,转而将区域与双边经贸协定作为推进其数据跨境主张的主要途径。这些国家寄望依托其技术优势和产业发展地位,通过“制度性权力”的扩展,实现其数据自由流动的核心主张。此外,这种规则制定的主导优势和产业先发优势将转化为在国际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上的竞争优势,从而迫使发展中国家未来在融入新的规则体系中将付出更高昂的规则成本。
当前,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为代表的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正推动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向更高水平、更严标准和更加开放的趋势发展。相对而言,中国近年来签署的国际经贸协议,在数据跨境流动的开放程度和规则水平上与之还有一定差距。
因此,对我国而言,能否顺利达成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国际对接,已经成为我国能否在未来国际竞争格局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因素。
传统机制无法适应大规模数据跨境活动
当前,国际贸易已经从贸易数字化向数字贸易化转型,数字贸易已经成为各国重要的经济增长动力。据报道,2024年上半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规模达到了1.42万亿元,增长3.7%,创历史新高;跨境电商进出口1.22万亿元,增长10.5%,也达历史新高,对贸易高质量发展支撑作用不断增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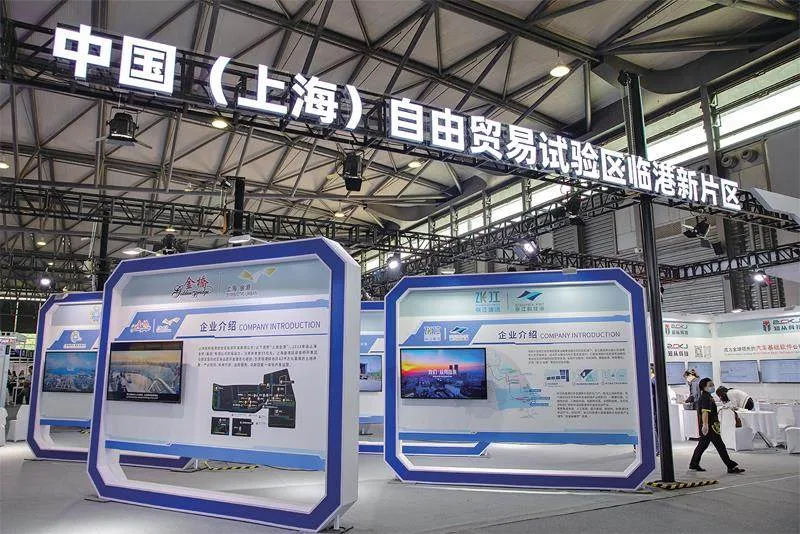
伴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跨境数据流动治理框架持续完善。在网络信息法领域相继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逐步构建了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为主要路径的数据跨境流动“3+3”模式。该模式以网络主权和数据主权为基础,强调国家对数字贸易活动的合法规制权。然而,基于种种原因,当前数据跨境制度体系与数字贸易活动仍存在一定的不适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基本原则上,监管与流动的不平衡。当前主流国际经贸协定均提出了合理性要求,即缔约方在对数据跨境流动采取限制措施时,该限制措施对国际贸易造成的负担应当维持在最低水平。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国际贸易协定均以“跨境流动为原则,限制(监管)为例外”;《区域全面伙伴经济关系协定》虽然对缔约国赋予了较大的监管自由,但仍然遵循上述原则。而我国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制度涵盖了较多场景,很难援引“合法公共政策目标”条款予以正名。
二是制度设计上,安全监管能力制约标准提升。高标准的数据跨境流通规则对主权国家的数据跨境活动监管能力和数据安全技术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我国监管机构的资源调配和技术支撑能力有待提升。
三是制度实践上,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和灵活性。数据跨境流动制度的落地,依赖的是法律法规的执行和企业合规环节。自贸区/自贸港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对外经贸合作的前沿,也是数据跨境制度实践的首选之地。近年来,各地虽然制定了一系列实施细则和落地规范,但总体而言实践效果并不理想。数据跨境涉及应用场景众多、数据类型复杂、数据处理目的多元,要求制度实践中为企业提供更为明晰和个性化的指导与支持。
推动自贸区数据跨境体系性立法
以数据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面对挑战,唯有继续推进开放,推动我国数据跨境制度向更高水平、更严标准和更加开放发展。
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展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数据二十条”)提出,“促进数据有序跨境流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持续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措施,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探索”。2024年3月22日,国家网信办公布《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更新和明晰了数据跨境相关要求,为数据跨境流动“松绑”,并授权自贸区制定数据跨境负面清单,进一步推动数据跨境流动制度升级。在此基础上,2025年1月实施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以专章的形式将上述数据跨境规则予以明确。
由此,上海自贸试验区进行数据跨境专项立法的时机已经成熟。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突破:
首先,立法应具备更高的体系化程度。针对自贸区数据跨境规范碎片化的现状,专项立法应当整合各项法规和规章,发挥制度枢纽和指引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数据跨境流动分类分级管理办法为基础,连接数据跨境“负面清单”、特定场景“一般清单”和重要数据目录,为企业提供清晰的数据跨境合规指引。此外,立法还应当成为国际协议、国家政策和企业需求的桥梁,充分发挥连接性、综合性与指引性作用。
其次,立法应当设立更高的开放标准。专项立法可以积极运用浦东新区特别立法权,在国家相关部门的指导下,完成《区域全面伙伴经济关系协定》数据跨境规则的国内落地,以“一般清单”为抓手,明确可自由跨境数据的范围。同时对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更为开放的国际数字经贸规则,在立法中预留接口,为后续制度升级探索做准备。
最后,立法应当适应更高的可操作性要求。数据跨境涉及场景繁多,风险动态多元,区域性时效性较强。制度的落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为相关企业提供及时的风险提示与政策说明。一方面,要求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工作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在单一被动地解答企业的疑问外,还应主动发布数据跨境实施报告,全面介绍相关政策法规的执行情况。另一方面,需要引导鼓励数据中介服务行业的发展;通过市场的方式提高数据跨境流动效率,以贸易助力数据要素功能发挥。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教育部教育大数据与教育决策实验室研究员)
编辑:黄灵" "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