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水《问学记》:如烟往事忆旧人
2025-02-11袁恒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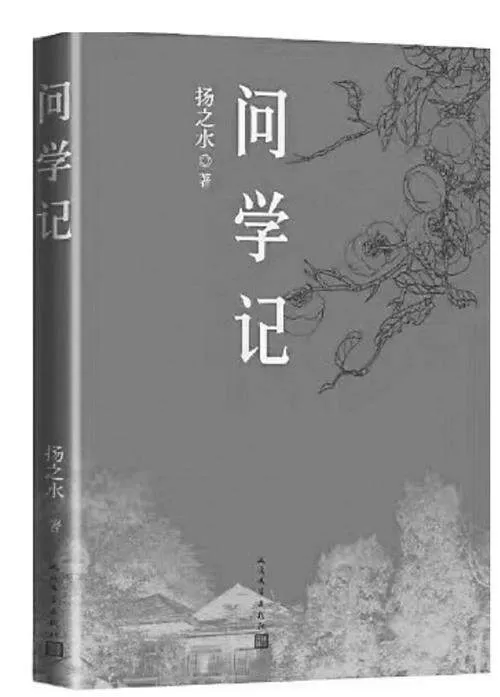
在阅读扬之水《问学记》之前,我时隔五年再次搜出康震在《百家讲坛》讲授的“唐宋八大家”系列讲座视频,尤其是重点听了欧阳修的专题。对欧阳修生平稍有了解即可知,其四岁丧父,多亏有堪比中国古代三大“贤母”的欧阳母“画荻教子”,加之其刻苦攻读,十岁时偶得《昌黎先生文集》残卷,甚爱之,从此以韩文为榜样,终成北宋前期文坛一代宗师。当我翻开扬之水《问学记》后发现,她因种种原因与大学失之交臂,但自学路上是幸运的,她得遇诸多名师垂青,为其成为卓有成就的名物学家助力巨大。当然,其多年来矢志不渝的刻苦努力仍是其成功要因。一卷《问学记》,将其和数十位名师的结交过往或详或略地记录下来,那些充斥其间的求学真知,那些前辈先贤的音容笑貌,似如烟往事一般再次浮现在眼前,成为激励后辈的航标明灯。
转益多师求真知
据笔者粗略统计,在《问学记》中扬之水提到的名师多达二十余位。这其中,主要源于其从1986年至1996年供职于《读书》杂志的经历。工作约稿让其需要结交诸多作家学者,而这些作者又往往令其获益良多,使其学识境界得到了全方位提升。
在这些作者中,尤以本书开篇重点提到的徐梵澄对她早年的影响较大。扬之水向这位被誉为“现代玄奘”的著名学者问学是多方面的。他们的交流轻松自然,不经意间,徐梵澄就会流露出富于学养的启示,比如徐梵澄提醒她学诗的路途和学书法类似:“先从《古诗十九首》入手,熟读《文选》诸诗,而唐,而宋,元、明可越过,清初王渔洋诗不可不读。”徐梵澄如此纵贯谈诗,绝不是简单信口一说,那是源于其扎实精深的诗歌学养。徐梵澄身为学贯中、印、西的著名学者,在古诗上造诣也是非凡。他的古诗源出近代诗坛大家王闿运的湘中诗派,学汉魏及三唐。青年时在上海与鲁迅过从甚密,每有诗作,则寄给鲁迅,时常得到鲁迅的点拨。《蓬屋诗存》是徐梵澄多年古诗研习的集萃,徐梵澄堪称近现代学者中创作古体诗的大家。
所以,扬之水面对这样一位诗学大家,其交流虽然远远不止诗学一域,但这方面的交流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而得出的结论自然也会令人信服。比如,对同样是古诗文功底深湛的俞平伯的诗文,扬之水和徐梵澄的交流就体现出了客观公正的可贵。当扬之水拿出俞平伯新出的《俞平伯旧体诗钞》,读到《遥夜闺思引》的小序时,徐梵澄的评论是有理有据的:“骈文的作法,是要高、古,像‘不道’‘仆也’这种辞,是不能用的。此外,‘孰树兰其曾敷,空闻求艾;逮蹇裳而无佩,却以还珠’,‘兰’字平仄不对,易为‘蕙’字方可读。当然俞氏也算是一位高手了,但绝不是大家。我说:如今早不是骈文时代了,哪里去找大家?毕竟强弩之末难穿鲁缟。先生以为是。”
实际上,对扬之水诗学有影响的当然不止徐梵澄,还有王泗原等人均鼓励她学诗,扬之水甚至一度发兴想做“诗人”,无奈,她很快发现自己不是这块料,努力了,但也放弃了。不过通过和王泗原的结交,她在其身上进一步学习到了不盲从名家名作,敢于提出质疑的治学精神。比如杜甫《秋兴八首》为千古名篇,但王泗原能够有理有据地予以评判:“‘香稻’‘碧梧’一联,偏要倒装,全无必要。这也是他故意出奇,故意出奇,即不能算是好诗。”再比如对《说文解字》段玉裁注的批评也很严厉,以至于说到段的解释不可信据者不在少数。王泗原的批评是绝对能拿得出令人信服的例证的,他的多次批评对扬之水产生了明显影响,她说:“这些年时常翻检的是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段注便很少查阅。‘疑’,可以说是先生读书治学最鲜明的一个特点。”而从王泗原这里学到的“疑”,显然是作为一名学者的基本素养,那便是在扬之水授业恩师孙机处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在扬之水看来,是从孙机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观念和方法。“问题意识”即“特别有着发现问题的敏感”。在其看来,孙机的全部著述,可以说都是先“发现问题”,而其“解决问题”直接导致了其著述的分量。扬之水师从孙机后,受到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成为一名著述颇丰的名物学家。相对来说,“名物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显得有些小众。实际上,这是先秦时代即已产生的一门古老学科,由于现代考古学的兴起,它才退避三舍。对于名物学,孙机、扬之水师徒,让这种鲜为人知或者说淡出人们视线已久的学科再度回归大众。在书中,扬之水以通俗的比喻让读者先明白何为“名物学”:“好比欣赏一首诗,吾人总是先要知道诗里的典故:故典、新典,典故用在这里的意思,然后是整首诗的意思。面对器物,也可以像读诗那样,看它的造型、纹样、设计构思的来源,找回它在当日生活中的名称,复原它在历史场景中的样态,在名与物的对应或不对应中抉发演变线索的关键。所谓‘名物研究’,可以定义为研究与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有关的各种器物的名称和用途。换句话说,是发现、寻找‘物’里边的故事。”
如此一来,我们作为普通读者,确实就明了了何为名物学了。那么问题接着就出现了,扬之水从孙机那里,具体学到了怎样的研究方法呢?她说:“从遇安师问学,自‘读图’始。‘看图说话’,似乎不难,其实并不容易。真正读懂图像,必要有对图像之时代的思想观念、社会风俗、典章制度等的深透了解,这一切,无不与对文献的理解和把握密切相关。大胆假设必要有小心求证为根基,这里不但容不得臆想,更万万不可任意改篡据以立论的基本材料。总之,是要靠可靠的证据说话,力避观念先行。”当读到此处时,我用手边笔立刻在旁边写出了一句话批注:“真正学到的方法,很有普遍性。”从扬之水这段既是学业内容复述,同时也是感悟的话语中,还可以看出功夫仍然在诗外。
孙机告诫扬之水做学问谨记三点:“一、必须依凭材料说话;二、材料不足以立论,唯有耐心等待;三、一旦有了正确的立论,更多的材料就会源源涌至。第一、二两条虽苦,却因此每每可得第三条之乐。”扬之水谨遵师命,用其扎实丰富的材料与科学严谨的考证,陆续撰写出了《诗经名物新证》《古诗文名物新证》《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湖南宋元窖藏金银器发现与研究》《物色:金瓶梅读“物”记》《中国金银器(五卷)》《诗歌名物百例》等大量名物学专著,终成一代名物学大家。
音容笑貌记日常
扬之水在本书中记述的与诸多前辈的故事,主要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而当扬之水结合当年的日记撰写这些回忆文章时,许多前辈已经作古了。扬之水这些客观真实的记录,再现了当年她与前辈们交往的诸多宝贵细节,特别是前辈们的音容笑貌,因其记录如同再现一般呈现于读者面前,让广大读者得以知晓这些大家们寻常生活的一面。
比如前面提到的富于学术质疑精神的王泗原,别看他批评起名家名著来如同怒目金刚,私下里,他却是位不折不扣的戏迷。且看扬之水记述的一段王泗原谈自己看戏的经历,就对其非玩票的真实戏迷身份称赏不已:“他说,有一位叫作李翔的旦角,唱功做功都极好,演《失子惊疯》一场,尤见眼神和腰腿的功夫(曾得过尚小云的亲授),却一直受压,票价始终提不上去,先生每为此不平,故只要上演李翔的戏,他必是场场去看(当然是坐第一排)。但李翔终于是被迫转业了——久不见其演出,多方打听,才得知还有一位李冬梅,也是同样的情况。”王泗原显然于京戏能看出门道,会赏识演员的真功夫,并且对李翔、李冬梅等底层演员的遭遇极为同情,但凡能够予以支持都尽力而为。如此一则小事,就能彰显出王泗原对弱者受欺压的义愤填膺,对富有才华的演员的大为怜惜,这样的书写是非常能够凸显这些老师们的性格的。
再比如扬之水记述和赵萝蕤的交往。她们的交流当然会有各种学术内容,比如扬之水全文展示了赵萝蕤20世纪3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创作出版的三首现代诗,这三首诗最初收录于阎纯德主编的《她们的抒情诗》。比起她们较为严肃的学术与文学交流,赵萝蕤请扬之水吃台湾产的“凤梨酥”、在她八十寿诞时请扬之水到新开业的麦当劳吃汉堡包和菠萝冰激凌等轶事,显然更加轻松活泼。扬之水的细节记述再现了八旬赵萝蕤爱吃甜品的可爱模样:“但她说这里的冰激凌不及国际快餐城的冰激凌好,她要请我吃一份。于是从王府井南口一直走到北口,在快餐厅又各吃一份‘美国迪克冰激凌’(每份5.00元)。”
同时,还要提及的是,本书恰如以点带面一般,通过和这些前辈的交流,不仅对诸多名家自身的轶事多少有些记述,还能够通过他们之口,进一步拓展其他名家的轶事进来,从而大大拓展了文本的边界。虽然另外一些名家并未直接与扬之水产生互动关系,但通过这些讲述,扬之水以及广大读者的确有开眼界长见识之感,包括一些鲜为人知的轶事,让学术研讨之间融入了轻松活泼的内容。比如在和徐梵澄聊天时,不仅说出当时仙去的几位老先生:冯友兰、俞平伯、唐圭璋,还由此聊到了“千年国粹、一代儒宗”(梁漱溟语)的马一浮。扬之水这样记叙了马一浮的轶事:“马一浮曾与汤寿潜的女儿订婚,但她不幸早亡,马于是终身不娶。汤很看重这位‘望门女婿’,知他生计并不宽裕,便时常送钱来,但马坚拒不受,即使悄悄放在桌子上或抽屉里,马发现后也立即追还。”对于这样一位在古代哲学、文学、佛学上造诣精深,于书法上更有杰出成就的近现代名家,扬之水自然对其名望与著作早有耳闻,但这种相对鲜为人知的轶事经由徐梵澄等师友讲出,无疑对扬之水和广大读者来说,会十分喜闻乐见。也足见徐梵澄等前辈,的确未拿扬之水当外人,能讲出诸多尘封已久的往事来,也令这样的对谈变得叫人神往。
图文并茂展风采
《问学记》一书除却记述了扬之水与诸多名师的日常交往与生活轶事外,还收录了人物照片、书信书影、题字书影、书封书影、书法书影等各类图片。这些图片数量不多,但它们的出现和本书内文实现了优势互补,让人物形象与文章内容变得更加立体直观——尤其是让他们叙述的轶事变得更加生动可见。
这其中给我第一个深刻印象的,当属扬之水与赵萝蕤的交流及相关图片。大学时代,赵萝蕤是他们当中最小的一个。她的同学名家辈出,如王世襄、萧乾等,也都比她大。那时她苗条温婉,外号“林黛玉”,有许多追求者。她却主动追求陈梦家。这自然引起了扬之水的好奇,且看她们的问答:“是不是喜欢他的诗?不不不,我最讨厌他的诗。那为了什么呢?因为他长得漂亮。”这如同闺蜜间私聊的话题就这么和盘托出了。如果没有照片为证,我们无法想象八十余岁的赵萝蕤在年轻时该是怎样的“林黛玉”,而她主动追求的陈梦家又该是怎样的貌美男子。好在赵萝蕤馈赠了扬之水当年她与陈梦家的合影。照片上的赵萝蕤的确是花季少女,苗条温婉,但文静内敛的赵萝蕤居然能主动追求陈梦家,实在也是因为旁边的陈梦家足够俊朗阳光——照片上的陈梦家剑眉星目,浅浅笑靥露于脸上,一席白长衫落地,微微背着手,风度翩翩。也难怪赵萝蕤拒绝了诸多追求者而倒追陈梦家了——实在是有图有真相了。与此对比强烈的是,扬之水与晚年赵萝蕤的合影放置在本书扉页——彩色照片。她们主要交往于20世纪90年代初,彼时的赵萝蕤已是八旬老人了。往日的温婉少女,“而从今天的苍老面容上,已经一点儿都见不到昔日的影子了(几个月没见,她好像老了许多)”。这种人物的今昔对比,自然会让所有人生出时光流逝的唏嘘感。但这种人人皆会有的自然规律谁也能理解接受,赵萝蕤这种今昔图片的赫然呈现,反而拉近了和广大读者的距离,让我们觉得这些著述等身的前辈如同我们的亲友乡邻一样亲切。
在本书的诸多图片里,我最为看重的当属沈从文《关于飞天》手迹的影印图。扬之水早年对沈从文的了解自然是源于其诸多文学名篇。但自从扬之水入手名物学后,沈从文晚年撰写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就成为其无法避开的专著,本书也对沈氏研究有所评价:“就服饰研究而言,沈从文先生的著作即早着先鞭,并且有着很好的成绩,但此著毕竟只是粗勾服饰史轮廓,许多专题尚未涉及。”扬之水特别看重沈从文对名物学的启示:“沈从文先生也不是考据家,然而小说家的悟性与敏感——这里还应该包括想象力,成就了他对物的独特解读,‘名物新证’的概念最早便是由沈先生提出。”特别是沈从文先生对《红楼梦》“贾宝玉品茶栊翠庵”一节中两件古器的研究文章,深得扬之水叹赏:“这里的功力在于,一方面有对文学作品的深透理解,一方面有古器物方面的丰富知识,以此方能参透文字中的虚与实,而虚实相间本来是古代诗歌小说一种重要的表现方法。”沈从文与其他德高望重的学者一样,在取得卓著成果后,还能知晓自身的不足,为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希望,扬之水转述为:“作者希望有人结合文献和文物对古代名著进行研究,并且直接提出了撰写《诗经名物新证》的课题。”
1995年,当扬之水师从孙机后,孙机即告诉她要把这篇文章好好读几遍,认为该文是“名物新证”的范本。沈从文与孙机之间自然不能构成孙机与扬之水这种大力提携的师徒之情。但哪怕沈从文只是送给孙机一幅书信手迹,而这幅手迹对于扬之水,乃至我等读者来说,是具有明显师承关系的。恰如扬之水认为的那样:“半个多世纪过去,《关于飞天》的价值,已不在于内容,而更多在于它留下了作者思考的痕迹或曰探究问题的思路,同时也是珍贵的墨迹……‘飞天’的传递,似乎可以成为一个小小的象征:沈从文开启的文学与文物相互结合的路,是不会寂寞的。”从孙机和扬之水的谈话中,沈从文“好人”的形象跃然纸上,是“长者襟怀和厚、气度宽雅的音容”。我们看着这三页《关于飞天》手迹的影印图片,真的是如同汪曾祺在《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中所说:“他搜集、研究这些东西,不是为了消遣,是从中发现、证实中国历史文化的优越这个角度出发的,研究时充满感情。”而当扬之水将沈从文二页书信工工整整地印在本书内页时,我相信书信内容她早已熟稔于心。她也必然铭记恩师孙机的殷殷嘱托,将名物学继续开拓精研,发扬光大。
2025年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