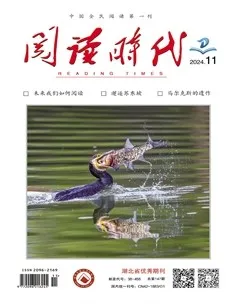看画
2024-12-31草予
地图挂在墙上,我常常拿它当画看。
看疆看界之外,也看河看海。大河如经,小溪如络,经络交贯,血脉奔流,大地于是浑然一体。湖是点,海是面。所有的水,在地图上都是澈澈的蓝,不垢不染,好看至极。
当世界变成地图变成画,惊峰险渊也好,怪禽猛兽也好,全都消失了。山无色,水无声,草木鸟兽鱼虫,万物齐刷刷从地图上掉落下来。大地,只是好看的平面,点、线、面,都很好看,天成地造之作。
越草的书,也越像画。满纸笔墨奔走跌撞,天上来,奔海去,分不清哪段是哪段,认不出哪个字始,哪个字终。
为什么要执意分出认出呢?那本就是一张画,如同水墨一幅,拨不开半天江南的雾,撩不开一帘三月的柳,好去看清乌篷船头立着怎样一位佳人。朦胧,是画的属性,也是诗的属性。
书,是写出来的,也是画出来的,照着捉笔人的心事,落在纸上。初临《兰亭集序》,眼前是有画的:三月的春山,一群才子曲水流觞,饮酒赋诗。皆已薄醉,皆已微醺,此时,王羲之提笔,为众人的诗写序添花。心情不算太差,字也都俊朗飘逸,虽然克制,往后细看,还是看出一层浅醉的。《丧乱帖》不敢临,字字悲郁,已经先吓到我了。看得出他在努力平复自己,也在努力平复手中的笔,可心到底是乱的,笔又如何平静得下来?你看他,间行间草,时轻时重,什么都隐瞒不了。
看画,常有束手无策之感,知道拿笔人的悲苦愤懑,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帮不上忙,解不了劝。《红楼梦》就是这样一轴长画,一开始就把人物命运交底了,画外人明知那是悲剧,还要目睹悲剧步步酿成,无能为力,一声长吁。
不当画,只当字,这一切就不存在了。字是美的,是艺术的,永远不会是悲剧的。
他们告诉我,临摹颜真卿《祭侄文稿》,是要一并临摹错字误词的。那是全书的一部分,甚至恰是旨趣所在。没有了率意涂抹,没有了随心所欲,颜真卿的那一腔悲愤便无法跃然纸上。越正确越干净的笔墨,就离颜真卿越远。
要我说,这一幅大可不必去临,临字不难,难的是那份长歌当哭与郁结痛彻。那就当画看好了,这一回,不是端庄稳重的颜体,是一笔血一笔泪的颜真卿。可以想见,他飞笔翔墨,涂涂抹抹,末了,愤然掷笔出窗,一眶热泪湿了衫。画外人,隔纸心疼。
对着诗词,往往发呆,仿佛也看见了画。

诗家都是译家,他们把画译成诗。
在街头,百看不厌的,是陌生人的面孔。我既无打量各式人生的好奇,也无窥探百态人间的贪图,单纯看时间在他们脸上作的画。时间塞给每个人的,原来是不一样的笔墨,没有谁与谁是一样的面目。即便五官相似,面目依旧各异。好看的画展很多,最动情的还是在街头,看人往来如画。各人有各人的作品。
人早晚都会洗脸,脸上的妆是可以洗去的。脸上的画,却总是挂在那里,洗不去,也摘不下。
我们不知道时间那么忙,它一直在我们脸上创作,攒笑如花,镂纹如壑,敷尘如霜,皆出其手。这样看来,生与死之间就是一场画事,我们空白而来,携作而去。
(源自《今晚报》,方可荐稿)
责编:王晓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