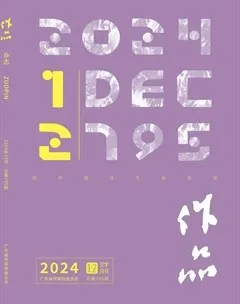普洛斯彼罗的魔杖,或哪吒闹海(印象记)
2024-12-31杜峤
1
真正的想象是炸塌大坝、勾动地火、召唤风暴。海底喷涌出雪白岩浆,障天蔽日,覆空卷地,小岛像只正栖在某位庞贝城居民头皮上的小昆虫,保持着某种极富动能的静止(如骰子在空中被握住,或高速旋转的粒子彼此对撞)。岛上人的命运呈现出贝母般游移不居的幻异光泽,他们望着前所未见的大风暴,目眩神摇,身僵如木,双脚难拔离土地一寸。在那大风暴中,他们看见火中危楼,沥青路面杂乱无章的脚印,成千上万一次性用品积成的茔冢,无形无相的海市蜃楼,只剩半边脸的镜中少女,褪色相片般泛白的乡人衣衫,被大巴车窗切割成块的桉树林与山雾,鬼魂们不知疲倦地永远翕动的嘴唇。
大风暴的源头是一柄魔杖。
那柄魔杖握在顾骨手里。我们站在远岸看不真切,那或许并不是魔杖,而是把火尖枪。枪尖膨胀变圆,变成麦克风,蘸着永不生锈的血。最后,最后,它一块块崩解,显出内里璞玉般的本相——它只是一支笔。
2
在康德的“崇高论”中,暴风以及其生成的荒墟带给人类某种瞬间性的恐惧与阻滞,继而重新激起了更为强烈的、渺小之“人”欲图与自然伟力相抗衡的超感使命与精神震颤。魔杖之于暴风骤雨,火尖枪之于狂浪怒涛,皆出于这股滞而后通、挫而愈勇的心气。顾骨是莎翁《暴风雨》中呼风唤雨的大魔法师普洛斯彼罗,视文学“胜过世上所称道的一切事业”,醉心于研修小说的炼金术,欲穷究世间万千叙述技法,将黑洞般包罗万象的命运凝练成某种钻石般透彻的小晶体,再以其为能源制造出一场想象力的核爆。当然,同样是召唤风暴卷起巨浪,比起肃然的长袍尖帽白髯甘道夫形象,顾骨的文学形象显然更贴近那位穿机甲肚兜、舞霓虹红绫、骑风火轮摩托的哪吒三太子。以信誓旦旦的嘚瑟,以飞流直下的激情,以神挡杀神的反骨,甩着膀子,梗着脖子,走向东海。他有要弑的“父”,也有要屠的“龙”,他追逐着那种震颤,本身又成为某种震颤。他腾身钻进风暴瞬息万变、永不停息的风眼,直到自己也变成风暴的一部分。正如布勒东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所预言的那样:“我将把自己置身于暴风雨之中。在暴风雨的护佑下,我万物不侵,除了那道迅烈的闪光。”
3
顾骨是个特别有“红尘气儿”的人,他很少会显示出那种文青的弱质与疏离(好像对身处的世界感到迷惘与陌生),而是与周遭环境洽然地融为一体,是这百丈红尘里的地头蛇,是曳尾于浮世的老龟仙。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书读得杂,人识得广,更得益于他混世魔王般对一切人事物“自来熟”的能力。他学东西很快,虽然也算是个211硕士,但常常自称“文盲”“野人”,对学院派那一套精英路数嗤之以鼻(我这样不学无术的人,因为偶尔拽拽生词,也常被他斥作学院派)。他有自己的野路子、土方子,即使什么专业性颇高的领域,他凭着一股子韧劲儿和超凡的理解力钻个几天几夜,也似乎能速成到毫不露怯的地步。比如,讨厌学院派的他,写博尔赫斯式的小说,写以考古学家为主人公的小说,也能写得有声有色,本色当行。一同去广州时,他仅比我早落地两个小时,见面时就带我走街串巷,俨然是这座城市的东道主了。和人打交道算是他最无须努力的领域了。他来西安一趟,我带他“偷渡”进学校,安排他住在我隔壁宿舍的空床位。我本来还担心是否搅扰,不想我们上完课回来,他跟隔壁舍友已经勾肩搭背,无话不谈,俨然多年老友。当晚他们秉烛夜聊,在他的叙述魔法下,他故乡毗邻的国度越南,莫名其妙成了那位舍友的第二故乡。他离开时,我的九位同学都成了他的兄弟。有时候我们想结交一些欣赏的写作者,若对方看上去像是高冷寡言的“硬茬”,我们就会派顾骨去执行社交任务。不出半日,对方大概率就会跟他称兄道弟、相见恨晚(有时我悲哀地想,我和顾骨成为挚友,会不会只是我们认识得早,而非真正最投契),顺便也爱屋及乌地将我们引为朋友。在写作初期,我们哪里认识什么刊物编辑,投稿的邮箱地址十之七八都是他积累整理的。他当然也是江湖百晓生,大多数的文坛趣事,我都是从他那儿听来的。他情商时高时低,周围朋友发一些道歉或解释之类的重要信息,措辞总要发给他帮忙把把关,但跟朋友们在一块儿时,他又总是懒得调用他的满级情商,常常一出口调侃打趣,就损得人家要跳起来打他。我和南音,都被他走马灯似的起遍了绰号,最初还会绞尽脑汁反击,后来也就慢慢免疫了。当然,若哪句话真惹我们生气了,他也会立马察觉,瞬间变身嘴甜心热的粘人精,定会把人哄得扑哧一声笑出来才罢休。他当然也很讲义气,你与人生摩擦,不管你是对是错,有理没理,他一定第一时间冲过来站到你身前怒斥对家,不退半步。我想,如果生在古代,他一定会是单雄信或柴进那样的人物。龚自珍那句“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更结尽、燕邯侠子”,我们都极喜欢,若日后真通达至此,他大概会有那种魄力与豪义。
他是非常典型的直觉型人格,我很羡慕他的笃定,无论你问他什么问题,他都会即刻不假思索地回答(即使答案可能挺荒谬),好像“沉默”“犹豫”“思索”这些词早就从他的处事词典里删掉了。好像爆几句“丢那妈”“烦得黑纹”,这世上就没有真正的困境与难关,他所经历的那些乖蹇曲折就会变成小石子和小飞虫。我觉得两广地区最能代表他气质的一句话是“洒洒水啦”,和我印象中广东人说这句话时那种几无负担的松弛感不一样,顾骨说这句话的同时是在承荷着什么,抵抗着什么,宣泄着什么。他的放松绝不是那种“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的清闲,而是“藩王小丑何足论,我一剑能挡百万兵”的自如。
4
我和顾骨结识于“匪帮”文学群(这名字就挺说唱)。文学群一般不是万马齐喑,就是群魔乱舞,我大多设置为“消息免打扰”。顾名思义,“匪帮”无疑是后者,妙人挺多,闲来无事爬爬楼颇有意思。某天我突然看到群里有人转发分享了说唱歌手西奥的叙事说唱作品Mr.boring,应者寥寥。嚯,我心中暗暗吃惊,退出去检查是否错入说唱演出群。在彼时我的潜意识里,所谓的严肃文学创作者大多有某种自命高雅、目下无尘的文艺病,对hiphop这种起源于贫民窟的粗俗乐种即使不鄙夷,也很难生出好感。这首歌因为色调晦暗尺度略大,曾被长时间下架,一般人根本听不到,这家伙应是个相当有品位的地下hiphop发烧友啊。这感觉像是荒锈已久的半失灵雷达在谬误的时空接收到某个清晰而笃定的信号。我当即在群里说,我听过两次这首歌的现场,一次是在西奥巡演的livehouse,一次是在Fullhouse满堂音乐节。几十秒后,通讯录里冒出个小红点。
那天晚上,我们竟找到了彼此九个共同点(后来才知道,甚至我们曾喜欢过的女孩儿的生日都是同一天,真是宿命中的难兄难弟),当即决定结拜为异姓兄弟。默契而激动地隔着网线赛博进行了一套rapper结交时的secrethandshake后,我们就开始“对暗号”。那时我才刚发表了一两篇小说,顾骨则干脆是个完全无任何作品付梓的纯素人写作者。两个二十岁青年写作者在文学圈边缘徘徊而不得其径,非常符合说唱文化里“Day1”“hustlefrombottom”这一类底层叙事。那些平日里潜藏在我们耳机里、羞于宣之于口的歌词像一条条金色鲤鱼从深潭中跃出。从宋岳庭的“我从命运的天台放眼却看不到星空”“life’sastruggle日子还要过,品尝喜怒哀乐之后又是数不尽的troubles”到幼稚园杀手的“我的存在只是宇宙中的一瞬间”“无论遭受什么苦难太阳依旧升起”,从MC热狗的“我把帽子反戴,还在期待逆转”“写着差不多的字,发着差不多的誓”到阴三儿的“当夜幕降临在我的城市,有另外一种人的生活即将开始”“想让我尊重你,你得先尊重别人”,从谢帝的“老子明天不上班,巴适得板”“笑话对我来说是笑话,也是天大的奇迹”到Gai的“老子一抬手就摸得到天,看白云青山和袅袅的烟”“看我的鞋儿也破,帽儿也破,看我的袈裟也破,但我的心比你干净得多”,我们一人说出上句,一人接出下句。打字不过瘾,就发语音唱两句。我们记诵着这些句子,这些句子似乎也阐释着我们。古人说“我注六经,六经注我”,这些歌就是我们的六经。后来我们常在朋友圈用各式歌词评论或回复对方,几乎臻至老杜“无一字无来历”的境界,朋友们估计看得云里雾里,我们也不解释,带着某种“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小得意。
就像诗人常以古贤人自比一样,我们也常以说唱歌手自比。他最喜欢杨和苏挑战人类极限的超速快嘴与燃烧着熊熊烈火的怒音腔调,而我则更偏爱Gai与C-block义气深重的江湖流。那时杨和苏和Gai在节目上打了一场巅峰决战,Gai数票险胜,他气炸了,跟我大骂不合理,我则认为Gai赢得畅快淋漓,光明磊落。我们为此还大吵一架(不过后来,Gai的那首《朝天门》成了我们KTV的必点曲目,杨和苏的《王位》我也经常在跑步机上循环播放)。平静下来后我想,他大概完全代入了杨和苏所扮演的角色——因锋芒毕露而被平庸的同行排挤孤立,因咖位尚轻而被节目组恶意剪辑,屡败屡战,愈挫愈勇,无数次向自己心中的最强者发起挑战。他希望抛却一切身份与地位的羁束,来一次最纯粹的对决。顾骨与杨和苏一样,是拳比天大的“武痴”:“三年时间过去了,我还是舞台上最疯的神经刀……才明白我从来没憎恨过谁,我只是想成为最强的。”“我知道早晚我都得走回曾经的路,因为我真的要废了这些人情世故,我靠真本领致富用不着神明指路,老子们逆着流走上大反派的成名之路”。杨和苏至少还有音乐上的家学渊源,而顾骨则是完完全全的白手起家。他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只能靠手里这支笔。他没有“好风凭借力”,只能单枪匹马在百万军中杀出一条通天的血路。
5
第一次接到他的电话是在某个冬夜。那段时间我像只河蚌般将自己封闭起来,打游戏打得不知昏晓,和他昼夜颠倒的作息不谋而合,聊天竟罕见得能对上频道(平日早上给他发消息,下午才能收到回复)。那晚不知几点,我结束一把游戏,他突然弹了个微信电话过来。我为人社恐,很少给人打电话,尽量打字沟通。接通后我问什么事,他说,没事,就是想和你聊聊天。他就是这样真诚直白得近乎冒昧。大部分时间都是他讲我听,他聊到中学时的糗事,聊到广西本土的说唱歌手,聊到原生家庭,聊到那些在他的前二十年生命中留下重要印记的单相思故事。我们很难说他的嗓音磁性动听,但却有种奇异的亲和力。声音大但不粗犷,狂笑或假装哭诉时会极为顺畅地转换为假声。有朋友戏称他的声音像“咆哮”,但这种“咆哮”绝不让人感到恐惧或冒犯,而是让人嘴角不自觉上扬。抑扬顿挫的腔调配以广西口音的塑普,他是天生的脱口秀明星。当然,这种浑然天成的幽默不仅仅来源于他的嗓音,更来源于他的叙述天赋。他的叙说不是概括性的、高蹈式的,而将根茎深深扎入每一帧场景与细节中。那些寻常或不寻常之事一经他的嘴,似乎就鎏了一层幻异迷人的七彩。某一刻,他突然说,零点了,今天是情人节。我们双双沉默,随机他爆发出一阵哭号,说,两个孤寡Loser的情人节竟然是在分享没品笑话中度过的。我看他说得悲凉,也大笑起来。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叙述中的龙州风土。在那部口述的《龙州日记》里,他每天睡到正午,便约友仔骑电动车嘟嘟嘟上街。那些窄仄的街道自然无法容纳鬼火少年的疾速,但即使他们优哉游哉荡着,半个小时也能逛遍县城全境。昏蒙的街道,低矮的砖墙,潮闷的带着土腥味的空气,电扇上打旋的飘带,缓慢的、仿佛永不褪色的三色灯转筒……在顾骨的叙说中,关于龙州的想象渐渐在我脑海中构建落成。那个蜂窝大的小县城,在我的印象中变幻为无数首县城说唱的MV取景地。Gai在《威远故事》里写:“堰塘角茶楼门口的玉溪,等到六点半一百块一包,楼上下来的人有的哭有的笑,有的生气要回家去提刀”,顾骨笔下的故事也经常发生在茶楼里;夏之禹的《姐姐》开头采样了杨钰莹的《轻轻地告诉你》,将“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繁衍出另一种甜腻到凄清的意涵与韵味,那种黄昏雨雾般轻柔潮湿的氛围也同样笼罩着顾骨的小说;我曾幻想过自己要是与顾骨生在同一座小县城里的发小,我们的日常大概就同《夜郎溪》中MV里王齐铭与刀脚大差不多,嗦碗老友粉便用白话高喊着“老板上分”拍老虎机拍到巴掌疼。那么“人”之外呢?县城之外呢?旁若无人穿街而过的牛羊(我想,这一幕若出现在城市里,则几乎近于安哲罗普洛斯电影中那种极富荒诞意味的诗意画面),噬人又自噬的蛇,用毛茸茸长臂在深林中荡跃的南征交趾的东汉大将的遗嗣,甩着长鼻从安南传说中轰隆隆踏出的巨象,洪流般淹没整个世界的甘蔗地,涠洲岛上世界末日般壮烈的落日,星河般从天而降的跨国瀑布,创世纪神话中的大洪水(他描述的场景让我记忆极深:水淹过二层楼,蛇在街上游,老鼠站在写满英文单词的化肥袋上乘风破浪,老头坐在阳台上钓鱼)……这些造物所钟眷的、远超人力的山野精灵与自然力量,成为了顾骨小说的另一大构成。他的小说由此显示出浑然的巫觋性,成为了某种被赋予自然伟力的祭器。
6
有时你会觉得他是世间第一等洒脱人物。天生地养、破石而出的泼猴儿,削骨还亲、莲藕化身的野哪吒,管他地厚天高,管他神鬼佛魔,统统一棒敲碎,一枪戳烂。他从没怕过谁,也从没服过谁。从同龄作者到文坛宿老,从茅奖作家到诺奖作家,顾骨从来只认文本,不认声名。写得牛逼,绝不吝惜自己的respect,主动结交,不为别的,只为喝一声彩;写得平庸,就算名头大过天,说不得也只能效仿阮籍“举觞白眼望青天”了。我们南京一聚,把酒扬子江畔。看大江风波浩渺,听顾骨臧否人物,颇有煮酒论英雄之感。可惜当日天无雷震,我也没有失箸种菜的演技,便激起失落已久的意气与野心,同他一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当时那股云蒸霞蔚的少年心气,如今回想,当是“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收获》《十月》,此事何难?”。
我们在天地间活得礼貌腼腆,畏缩不展,在他面前常觉自惭形秽。他写恨,恨得歇斯底里,他写爱,爱得轰轰烈烈。如果把“写”字拿掉,我以为亦是成立的。在纯文学界,秉持“作者已死”的理念,小说家往往以将真灵魂深深隐藏于无数重假面后为荣;而在地下说唱圈,“keepreal”是闯荡江湖的第一铁则,而“人歌合一”亦是对说唱歌手的最高评价。在我看来,担得起这四个字的人屈指可数:老Gai、谢帝、echo、刀脚、揽佬。或许还要加上顾骨。
但有时候你又会觉得他非常拧巴。就像武侠小说里面修习绝世神功的少侠,他屡屡遭遇心魔,又总是挣扎着想把它亲手打碎。广西有个“相思湖文学大赛”,面向所有广西大学生,规格挺高,会请全国各地的作家编辑们来颁奖。第一年,他还没正式开始写作,朋友获奖却因故缺席,他上台帮同学领奖。作家李约热问他,同学,你得了几等奖?他怔了怔,随即答道,今年没得奖,明年一等奖。约热老师哈哈一笑。这次经历大概在他心底生发出一点羞惭与倔强,他开始埋头写作,决意履行这个玩笑般的承诺。第二年,第三年,他继续报名参赛,都只得了二等奖。那一年他被“放飞鸽”错过了一次发表,我们为他抱不平,他沉默不语,心结似乎也愈加深重。他说他再不要什么推荐,只想靠自己写出头,去争一个平等对话的权利。这是他一贯的傲骨与心气。时间来到第四年,他再次参赛,这一次,他拿了一等奖,才算是如愿以偿。我常说他像杨和苏,因为杨和苏当初比赛也如出一辙:2017年只为比赛唱了宣传曲,18年止步于十五强,2019年终于夺冠。这简直是为顾骨量身定制的同款剧本。那天结束,顾骨把发表获奖感言的视频发给我,这小子笑容可掬,没说什么“莫欺少年穷”,倒是当着几百人的面为自己公开征婚。那一刻,我知道他郁结了三年的小心结已经不复存在,“万一禅关砉然破,美人如画剑如虹”。
考研的那半年,他又陷入一种极度患得患失的状态。连麦听歌时,我会特意挑一些热血点的燃歌放给他。但有时候听着听着就没声了。我问他是不是睡着了,在一阵死一般的沉默后,他说,峤,你说如果我考不上,会不会就不写了?我身边有太多人写着写着就不写了,我怕我也没时间写了到时候。我说别多虑。他接着说,我明年六月就毕业,可能找不到工作,到时候我找个工厂打螺丝,或者找个餐馆洗盘子,每天下班回家就很累了,只想躺在床上刷刷短视频,感觉这辈子一眼就望到头了,哈哈哈。我说,不会的,你注定要写小说。那段时间里,他有时沉默得像另一个人,有时又话多得像在宣泄什么。除此以外,便是近乎疯狂地写作,他边复习边写,好像在以写作来对抗濒临崩溃的情绪。他是我见过最勤奋且最有杰才的写作者,考研那一年,他写了接近三十个短篇小说,每篇小说一般几天就能写完。他非如此不可。他说,一旦把时间拉长,那种郁结的情绪与氛围便会散掉,那这篇小说就废了。
考研结束没过多久他就收到“超新星大爆炸”过稿的喜讯。那天他几乎是哽咽着打电话给我,听他讲完,我也激动得说不出话,最后我说,兄弟,守得云开见月明。我们本以为他会“飘”一阵,事业学业双丰收,春风得意是应有之义嘛。但他反而陷入了一种更深的焦虑中,我早上醒来时,常常会收到他凌晨三四点发来的消息。写不出满意的好小说真是一件让人痛苦绝望的事,他说,我想写出牛逼的小说。峤,你说我能做到吗?我想当一个对得起自己良心与尊严的小说家。考研时,他更多的是在焦虑自己往后的写作之路是怎么样的。现在,他焦虑的是自己能不能把这条路走踏实,踏得步步扎实步步生莲(这似乎又与哪吒无异了)。他来西安时,伍小迪给他看手相,说他先天困顿,命中的大运须靠自己一拳一脚争来。当时听到这句话,我心里揪了一下,眼睛涩涩的。他这一路走来真的太不容易,我时常觉得只要他稍微懈怠一分,便会堕入他厌弃的另一种生活。
7
顾骨是抓娃娃圣手。
我和白石豪掷几十枚游戏币,你塞一枚我塞一枚,初时饱满如熟桃的情绪在循环往复的校正、猛拍、屏息、惊呼、惜叹中逐渐被机械臂一掌掌捏烂,我们感到自己正在向一只永不知餍足的巨鲸口中投食。这场糟糕的马戏终于迎来谢幕——保底夹像半截伪善者施舍的面包被丢在我们面前,出了,出了,是只貌寝的绿毛小怪物,头发像《哈利·波特》里打人柳狂舞的葳蕤枝条。我们还剩下四五个币,这才想起来在一旁冷眼观战的顾骨。我们显出败军之将的愧怍和尴尬,互相推搡着说,就不信这个邪了,再续五十个币!顾骨摆手拦住,说,等一下,你们喜欢哪个?愣了片刻,我选了线条小狗,白石选了玲娜贝儿。顾骨接过零星几个币,转骰子样掂了掂,丢进机口。摇杆左三右四,拍下按键,机械臂嘟嘟移动,下沉,抓取,上提,松开,就在我们再次惋惜叹声时,线条小狗在出口挡板上一弹,竟奇迹般落入出口。我与白石瞠目结舌,忘了欢呼。顾骨不管我们,走到玲娜贝儿身前,投币,调杆,按键。这次没出。我们暗自舒了口气,差点被惊得脱臼的下巴也像梦醒般复位了——也没有那么神嘛。顾骨不响,再次投币,调杆,按键,机械臂松开时一甩,玲娜贝儿被他塞到白石怀里。
又续了十个币并收获了一大袋毛绒玩具后,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小子不只是运气好,手上确实有两把刷子。眼准,心快,手稳,能抓的可不只是毛绒的娃娃。我想起大江健三郎在《被偷换的孩子》终章,写古义人给千㭴带回一本莫里斯·桑达克的寓言画册。故事是这样的:少女爱达的妹妹被精怪葛布林偷走,换作冰雕孩童。当冰开始融化,爱达披上妈妈的披风,飞到海边的洞穴。她看到成千上万个孩童仰头露出纯真笑容,每一个都像自己的妹妹。但爱达并不慌张,她从腰间取下妹妹最爱听的圆号,开始吹奏。号声清亮,葛布林们纷纷现出原形,不由自主狂舞至死,真正的孩童终于浮现。顾骨就是爱达,我想,他有在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复制品的幻扰与诱惑中保持清醒并辨认出那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娃娃的能力。在后现代纷繁幻惑的万象中,他拨云见月,拂叶分花,一探手将那只独属于他的、双翼璀璨的文学小精灵捉在掌中。这几年“县城文学”火了,“新南方”也火了,但这些跟顾骨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还是埋头写,把无关的标签当成电风扇上赶蚊蝇的飘带。他甚至厌憎它们,以它们为贩卖地域刻板印象的伪命题。以他的桀骜倔强,断然不肯在“新南方写作”的康庄大道上老老实实、四平八稳地正步走,若逢见丛枝障目荆棘绊足的野路,必要钻上一钻,遇见路边无人拴驯的野马,必要骋上一骋。几番闯荡,或许就践出一条自己的路来。以前我常劝顾骨多学学《雨》和《野猪渡河》,争取当个“广西黄锦树”或“龙州张贵兴”,实则低觑了他的野心与能力。他谁也不用当,只当他自个儿。
8
2023年3月3日,顾骨、南音和我一拍即合,创立了“三只野猪”厂牌。最初群名叫“00后の一席之地”,一看就是顾骨取的,致敬了他最喜欢的杨和苏、早安、黄旭在《中国说唱巅峰对决》上的逆袭夺冠组合。但后来我们觉得“00后”这个代际的标签意义不大,最初我们可能会因为这种分类而享受到新手红利,但作者最终还得靠作品立身。从那时起,我们就生长出了一点志气:要写点不一样的东西,要写点没那么容易被看透、没那么容易被分类的东西。借着这股气儿,我们把群名改成“三只野猪”。最初是“三只小猪”,有点可爱,不太酷。那时我们的写作都有点叛逆,绝不肯老老实实地写文坛主流的现实主义风格。南音是“香港马尔克斯”,我腼着脸自封“鼓楼区波拉尼奥”,顾骨则谁也不学,谁也不像,自辟蹊径。总而言之,我们希望自己能“野”一点,就像“野兽派”一样。在野兽里,“一猪二熊三老虎”,野猪最蛮横、最愤怒、最疯狂。它们横冲直撞,强突猛进,不为捕食或繁衍等生理欲望,因为冲撞与突进本身即是意义。
九月,Gai和王齐铭的新歌《我的兄弟》的开头采样有一句“山猪下山咯”,我们都很喜欢的另一首《三滴血》里也唱:“我们三个,要下山咯,唱起山歌,闯险滩啰”。
去年十月,我在“超新星大爆炸”栏目发了五篇小说。今年十月,顾骨在“超新星大爆炸”栏目发了五篇小说。我那五篇写得匆忙,他这五篇也同样是快手之下写出的作品。我们秣马厉兵,箭在弦上,都准备好靠自己的作品打场硬仗。
野猪要下山咯。
9
我有时候会升起某种近乎狂妄的自信,觉得自己非常了解顾骨,就像了解一个从童年起就贴近瞳孔凝望的万花筒;有时候又会产生某种如坠深谷的失落与惭愧:谁又能真正了解万花筒呢?“万花筒”这个比喻并非说他像现代性一样有五副及以上面孔,抑或是佛经中“具二十七面,有千手千眼,黄金色”的观世音菩萨。这是风暴的缩影,是小说家独有的神通与诅咒,是梦得彩笔者那颗紫水晶般分出无数切割面的七窍玲珑心所必须包蕴的敏感与复杂。就像把无数株药性相悖相克的仙草扔进老君炉中,一朝丹成,浑然一气,宝光圆转。
无论如何,可以预见的是,这场从万花筒中,从普洛斯彼罗杖端,从风火交燃的稚嫩脚下刮出的风暴,将愈行愈烈,席卷万象,将世人笼罩在他独有频率的宏大震颤中。
责编:郑小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