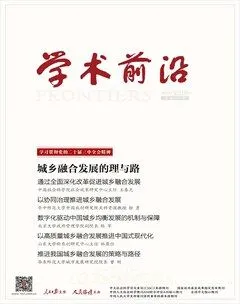美国总统选举与外交政策走向
2024-12-18张文宗
【摘要】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是在美国政治极化严重、深度卷入乌克兰危机和中东乱局的背景下进行的。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通过“司法武器化”等手段激烈竞争,哈里斯与特朗普围绕美国经济、移民等国内议题和是否应继续援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如何处理巴以冲突等外交议题进行辩论。美国维护霸权的目标和聚焦大国竞争的国家安全战略决定了美国外交的基本特征。经过激烈竞争,特朗普赢得总统选举,未来“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将对大国关系、热点问题和国际格局的走势产生重大影响。
【关键词】美国总统选举 共和党 民主党 政党政治 对外政策
【中图分类号】D77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21.011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在欧亚大陆这个“世界岛”上,欧洲、中东、亚太三大地区同时经受地缘政治冲击。美国深度介入这些冲突和竞争,以服务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与此同时,2024年是美国大选年,美国内部政治极化严重、社会撕裂加剧,民主、共和两党围绕下届总统职位和国会议员席位展开了激烈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险遭刺杀、谋求连任的拜登总统被迫退选、哈里斯副总统“接棒”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让大选选情跌宕起伏。经过两党各自的全国代表大会,特朗普-万斯组合、哈里斯-沃尔兹组合被推到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心,进行极为激烈的较量。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美国的选择不仅关乎美国自身,也关乎国际热点问题走向与国际格局的演变。特朗普最终击败对手赢得大选,执政后将继续推动“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给世界带来新的巨大不确定性。
政治极化背景下的美国总统选举
自2016年大选特朗普代表的右翼民粹势力搅动美国政坛以来,美国政治就进入了“亢奋期”。两党建制派与特朗普的激烈斗争使美国的政治极化现象更加严重。特朗普执政期间,针对他的各种司法调查和国会弹劾、围绕2020年大选结果的争议,乃至2021年1月6日“国会山骚乱”事件等政坛乱象,充分暴露了美国政治弊端。2021年民主党总统拜登执政以来,对特朗普和共和党的多项政策推倒重来,特朗普本人却高调参与2024年大选并获胜。美国大选历来是两党及候选人激烈竞争的政治活动,但此次总统大选的竞争程度之烈、意外状况之多,不仅在美国,在整个西方发达国家中也是少有的。
首先,美国政治暴力对选举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司法武器化是美国政治暴力的重要形式。从特朗普投身2016年大选到上台执政,“通俄门”“逃税门”等针对其个人的各种调查此起彼伏。2020年大选后,拒不认输的特朗普煽动了被建制派视为“国耻”的“国会山骚乱”事件,美国精英们引以为豪的“选举公平公正”“政权平稳交接”的“民主神话”被打破,特朗普本人也受到一系列新的调查。2024年大选期间,特朗普卷入的四起刑事案和两起民事案一度全面发酵(包括在“封口费”案、“不当处理机密文件”案、“干涉联邦大选”案、“煽动叛乱”案中被刑事指控并面临审判,在“名誉诽谤”案、“财务欺诈”案的民事案件中被罚款超过5亿美元),共涉及90多项罪名。特朗普的此等遭遇,主因是其不承认败选结果,执意再次参选并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面对如此状况,保守派控制的联邦最高法院积极介入,暂时叫停或终止了这些司法调查和审判,给特朗普继续参选提供了“护身符”,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司法武器化”的威力。
现任总统拜登也一样尝到“司法迫害”之苦。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对拜登发起了弹劾调查,以查清其是否从儿子亨特的海外商业交易中不当牟利。在两党动用司法手段打击政治对手的过程中,国会、司法部、联邦和州的检察官及法官都主动或被动地卷入政治斗争,这不得不说是美国法治的悲哀。
2024年7月13日,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巴特勒开展竞选活动的特朗普遭到枪手刺杀。美国媒体评论称,刺杀事件发生后,尽管拜登政府迅速谴责了政治暴力并呼吁国家团结,但正是两党之间的言论攻击、司法斗争、舆论抹黑招致了这种暴力行为。[1]哈里斯接替拜登担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仍难以摆脱政治暴力的窠臼。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表示,“美国人使用政治暴力的意愿可能达到内战以来的顶点”。
其次,美国政党与候选人的相互塑造改变了选举轨迹。美国选举是以候选人为中心的选举,美国选民既选政党,更选政党推出的候选人。此次选举,共和、民主两党呈现出不同的政治形态。
由于特朗普对共和党的改造更为剧烈,共和党在很大程度上“特朗普化”。自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以来,共和党“亲资本、亲自由贸易”的政策延续下来。为了和民主党竞争更多的选民群体,共和党也一度在移民问题上采取较宽松的立场。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改变了共和党的政治路线,通过极端的贸易保护和反移民策略实现了对共和党的接管和改造。在2018年中期选举、2020年大选和2022年的中期选举中,特朗普以总统和前总统的地位和权威,利用其在基层选民中的影响力,通过有选择地支持或打压一些议员、州长候选人,持续塑造共和党的发展方向,维持其个人在党内的巨大影响。一些学者认为,共和党已经被“特朗普化”,或者进一步说,共和党已经成为“特朗普的党”。[2]此次大选中,那些在政见上“模仿”特朗普但又想在党内挑战其地位的共和党政客,在退出初选后都很快成为特朗普的支持者,而那些共和党内的“反特朗普”力量则被完全边缘化。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特朗普选择坚持走右翼民粹路线的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万斯为竞选搭档,进一步凸显了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强势主导地位。
与共和党不同,民主党则呈现出政党对候选人的强大塑造力。寻求连任的拜登总统在初选中没有遇到任何挑战,但在锁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后,由于高龄引发的健康问题及民调落后,开始面临巨大的党内外压力。从2024年6月27日在与特朗普电视辩论中表现不佳,到7月21日被迫宣布退选,拜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受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前国会众议长佩洛西、部分民主党州长及议员、《纽约时报》等自由派媒体、上百个有实力的民主党捐款人等施加的强大退选压力。由于支持率大幅落后于特朗普,拜登难以说服本党相信其能够赢得大选,最后不得不支持副总统哈里斯“接棒”。现任总统在经过了本党初选并锁定总统候选人提名后又被迫退选,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头一遭。哈里斯被确立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其在全美和关键州的民调支持率均迅速上升,甚至一度反超特朗普,所获得的竞选捐款也迅速增加。在提名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担任竞选搭档后,哈里斯在民主党内的政治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再次,美国两党围绕“两条道路”的竞争事关重大。总统是符号化的政治,两位候选人竞争背后是两党之争,是不同的政治理念、治国方略和利益集团的较量。经济是美国选民最关心的议题,也是两党斗争的焦点。实际上,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两党都关注到美国制造业衰落和中产阶级萎缩,也都在反思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弊端,在重振制造业、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推行贸易保护、保持美国科技优势等方面存在高度共识,而双方的分歧主要体现在未来发展理念和利益分配上。
特朗普偏好大规模减税并发展化石能源,重在对大企业和富人减税,配以对企业放松监管,而对传统的社会弱势群体关注不够。民主党则攻击共和党的“涓滴经济学”制造了惊人的贫富差距,并标榜自己的政绩。哈里斯强调若当选,将对中产阶级家庭减税,同时也持续关注应对气候变化,将发展清洁能源、电动汽车、节能环保材料等新兴产业作为推动产业转型的重点。
炒作社会文化议题是两党动员选民的重要途径。特朗普要求驱逐非法移民,逆转少数族裔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争取更大权利的“觉醒运动”。这一立场有助于动员共和党的选民基本盘。哈里斯则支持平权运动,注重提高少数族裔在住房、教育、就业等方面的权利,动员的对象自然是民主党的选民基本盘。美国经济的吸引力和拜登政府释放的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信号,导致从南部边境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数量激增,边境执法人员和边境州面临巨大的压力。[3]在大选的压力下,民主党政府提出了加强边境管控的举措并在国会推动相关立法,但特朗普与共和党则出于政治目的加以阻挠。
随着政治斗争的加剧,两党将“道路选择”上升到“自由对抗专制”的高度。民主党人认为,特朗普掀起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简称为“MAGA”)运动代表着一种极端的意识形态,具有反民主、反移民、排外的“非美国”特征,是一种必须予以压制的极端主义。对于特朗普本人,民主党为其贴上“威权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的标签,声称特朗普的所作所为“使美国民主面临自内战以来最严重的威胁”。[4]特朗普则声称哈里斯为“激进左翼”,攻击其政策是要把美国引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按照这种逻辑,此次大选已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党派之争”“主义之争”,而具有了关乎美国立国之本和前途命运的意涵。
为何美国的两党斗争如此激烈?除了特朗普这位“非典型总统”加剧政治混乱外,美国政治生态和选举制度的退化难脱干系。《波士顿环球报》网站刊文称,两党在大多数问题上的分歧,实际上并不像政客们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大。尽管合作的方案一目了然,但两党却没有,或者说不会寻求共同点。这种恶性竞争和美国政治的机能障碍密不可分,两党的任何一方都只想通过“掌控”另一方来“胜出”。这种零和思维源于极端党派政治和让这种政治成为可能的“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美国的选举制度持续放大并强化分歧,导致不信任对手的局面逐步升级。如今政治冲突的二元结构(永远都是“我们对抗他们”)导致“为赢得权力而战”比“为解决分歧而战”更加重要。[5]
总统选举中两党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争论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近年来中美关系历经风雨,美俄关系则因乌克兰危机降至冰点。这一方面与大国之间的权势转移和战略博弈相关,另一方面也受到美国国内政治发展变化的影响。美国政治内斗持续升级,两党精英因此急于通过树立外敌来凝聚国内,向外转移矛盾和转嫁危机。与围绕此次大选而加剧的美国内部矛盾相比,两党关于美国外交政策走向的争论也非常激烈,焦点是乌克兰危机、新一轮巴以冲突、“中国挑战”等议题。双方政策主张的差异既反映两党外交传统理念的不同,又体现个人偏好和背后利益集团的博弈。
首先,围绕乌克兰危机,双方在是否应继续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美国联合欧洲盟友向乌克兰提供了大规模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对俄罗斯则实施了大规模的金融战、贸易战、科技战、网络战、法律战和认知战。这些援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冲突的进程,将其拖入拉锯战和消耗战的阶段。冲突的长期化必然加剧美国国内的分歧,特别是在美国大选的压力下。拜登政府支持乌克兰“将俄军赶出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乌克兰全部领土”。为表明“援乌抗俄”的正当性,拜登还不断渲染俄罗斯的“侵略”构成了对“乌克兰领土完整、欧洲安全、美国安全乃至西方民主和自由”的威胁。2024年7月在华盛顿召开的北约峰会上,拜登政府推动北约发表宣言,作出了“长期援助乌克兰,帮助其赶走全部俄军,推动其最终加入北约,以及继续全面对抗俄罗斯威胁”的承诺。[6]哈里斯在芝加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同样展现了要联合盟友援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意志,体现了民主党政策的延续性。
特朗普则反对继续援助乌克兰,声称自己有能力推动俄乌停火。特朗普表示,美国应该首先解决好自己的国内问题,包括加强南部边境的管控、打击非法移民等;美国持续援助乌克兰是“花费纳税人的钱、消耗自己的弹药库”;对俄罗斯这个核国家搞代理人战争,将使美国持续面临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乌克兰应该作出妥协并与俄罗斯实现停火。两党主张暴露出美国选民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根据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的调查,超过半数的共和党选民反对继续援助乌克兰,而绝大多数的民主党选民则支持本党精英的立场。
其次,围绕巴以冲突,双方在是否应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问题上立场不一。拜登政府对外战略的核心是全面遏制中俄以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战略重点在亚太和欧洲,而中东是其进行战略收缩的地区。不过,由于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执政时在巴以问题上全面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包括继续落实《亚伯拉罕协议》,推动更多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巴勒斯坦人感到被严重边缘化。如果在阿拉伯国家享有特殊地位的沙特与以色列建交,巴勒斯坦将面临灾难性的结局。[7]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在2023年10月7日对以色列发动了代号为“阿克萨洪水”的突袭,造成1400多人死亡,200多人被绑架,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哈马斯袭击平民的行为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招致以色列的严厉报复,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
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内塔尼亚胡政府进攻加沙以消灭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拜登政府和国会两党主流均同意向以色列提供新的军事援助。但以色列在打击哈马斯时导致数十万巴勒斯坦平民伤亡,上百万民众流离失所。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通过决议,呼吁冲突方立即实行持久和持续的人道主义休战,而沙特、埃及、约旦等阿拉伯国家则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实施“集体惩罚”,敦促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推动停火。中国、俄罗斯甚至美国的部分盟国也谴责以色列滥杀无辜的行为。同时,长期支持民主党并同情巴勒斯坦的美国民众也通过游行示威抗议拜登政府支持以色列的政策。其中,作为美国大选关键州的密歇根州,聚集着几十万高度同情巴勒斯坦的阿拉伯裔居民,他们向拜登发起了明确的选举威胁,迫使拜登重视他们对以色列施压的诉求。[8]内外压力下,拜登政府多次敦促内塔尼亚胡政府遵守战争法,允许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加沙,尽快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并在向以色列提供军援过程中暂停运送部分重磅炸弹。哈里斯与拜登的立场基本一致,一方面宣示了坚定支持以色列捍卫自身安全的政策,另一方面则表达了对加沙人道主义灾难的关切,敦促巴以尽快停火,表态支持最终以“两国方案”解决问题。[9]
对大选年的共和党来说,巴以冲突提供了一个攻击拜登和民主党的新借口。特朗普在竞选活动中不断展现对以色列的“无条件地支持”,抨击拜登暂停向以色列运送部分军火的行为。为了显示更有能力保护以色列的安全,特朗普吹嘘“如果我是总统,哈马斯就不敢攻击以色列”“以色列遇袭,是因为我们的政府被视为软弱无能”。特朗普还抨击拜登政府2023年9月与伊朗达成的换囚协议,并声称自己在任内对伊朗的军事和经济压力严重削弱了其实力。
再次,遏制打压中国是两党共识,但双方的具体主张有所区别。对于特朗普和哈里斯而言,应对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具有相当的紧迫性,而中国则是一个更大的长期挑战。在2024年大选中,“中国议题”并非两党关心的首要外交议题,但其分量不容忽视。特朗普和共和党延续了2016年大选和2020年大选期间的竞选策略,即展现出比民主党更强硬的反华“鹰派”立场,以显示自己更有能力“应对中国挑战”“维护美国领导地位”。2016年大选期间,特朗普大肆炒作中国的“经济侵略”,将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和工人的失业归咎于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上台执政后,特朗普挑起对中国的大规模贸易摩擦,开启全方位遏压中国的政策模式。2020年大选期间,特朗普将自身应对新冠疫情失败、支持率滑坡的责任归咎于中国,大肆散布病毒来源的阴谋论,借此煽动选民对中国的不满,但选举结果表明了该策略的失败。此次选举,特朗普故伎重演。他攻击拜登政府对华“软弱”,威胁要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60%的关税,威胁取消给予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待遇(PNTR),制造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是要“买下美国”的恐慌。德桑蒂斯、拉马斯瓦米等共和党民粹派政客,则声称“中国是比俄罗斯更大的威胁”“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停火的一个目标是要集中精力和资源对付中国”。
对拜登政府来说,与中国进行全方位竞争并最终“竞赢”是基本战略。为了提升“竞赢”中国的能力,拜登通过加大对国内的投资重振制造业和发展高科技,直接制裁中国企业,拉帮结派构建“排华”小圈子来遏压中国。拜登就是要通过增强美国实力、拉拢盟友、削弱中国,来塑造对美国更有利的力量对比、战略态势和国际格局。因此,美国不断出台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政策,怂恿和支持欧洲国家、日本、韩国、菲律宾等盟友共同对付中国。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在美国已经深度卷入欧洲与中东“两场冲突”的情况下,并不希望亚太局势失控,不愿看到中美爆发进一步冲突。因此拜登政府既出台新政策遏压中国,又试图确保“竞争不失控”,两面性十分突出。哈里斯同样以竞争心态看待中国,她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我将确保我们在太空和人工智能方面引领世界走向未来。将赢得21世纪竞争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我们要加强而不是放弃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10]。
美国外交的变与不变
自冷战结束后,美国就确立并实施了维护其“领导地位”的国家安全战略,将防止出现一个实力强大的挑战者和竞争对手作为该战略的重要内容。经过十多年的“反恐战争”,自2017年特朗普执政后,美国非常明确地将国家安全战略聚焦到“大国竞争战略”上。因此,该战略具有跨党派特征,且具有长期性,大选周期不会对其造成剧烈影响。探究未来美国外交的“变”与“不变”,可以更好理解美国政治变化与外交政策的关系。就中长期而言,美国外交不变的趋势至少有两个。
一是美国频繁使用暴力和胁迫手段的霸道行径不会改变。美国信奉实力又滥用实力,为了维护霸权地位会继续对别国实施霸凌行为,包括对自己的盟友和伙伴。美国的盟友与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不完全一致,而为了促使盟友服从和服务于其实施的大国竞争战略,美国对盟友的控制将不断加深。当前,美国正通过强化军事捆绑、情报监控、政治施压、舆论塑造等手段加大对盟友的操控,以使盟友更好地服务于美国的“护霸战略”。当然,为了促使盟友的配合,美国正与相关国家开展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的合作,继续强化小圈子。对于美国眼中的“假想敌”,不论何人执政,美国政府都会继续使用政治渗透和颠覆、军事威慑和胁迫、外交施压、金融制裁、出口管制等手段予以打压。这种拉帮结派、霸凌霸道的做法,将持续撕裂国际社会,制造新的混乱和动荡。
二是美国大搞贸易保护的趋势不会改变。在选举政治、新冠疫情、俄乌冲突、中美竞争的影响下,美国高度重视美国经济安全,以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弹性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在提高关税、推动海外制造业回流、驱赶和吸引别国制造业资本投资美国的同时,美国政府会继续实施“购买美国货”、补贴国内产业等政策“维护经济安全和保护国内就业”。这些政策延续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的做法,是对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一种重大调整,是美国政客应对国内民粹主义压力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崛起的经济方略,具有长期性。由于两党在推动逆全球化、“去中国化”等方面存在战略共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会延续下去。
经过激烈的竞争,特朗普击败哈里斯当选美国第47任总统,重返白宫。特朗普重新执政后, 美国外交中的贸易保护主义、右翼民粹主义和单边主义色彩会更浓,相关的具体政策也会发生不小的变化。
特朗普的外交战略,是以现实主义的手段维护现实主义的目标,维护以“美国优先”为导向的霸权。“美国优先”理念本身具有浓厚的单边主义色彩和一定的孤立主义特征,其核心是美国应更加聚焦国内发展,更加维护美国自己而非其他国家的利益。特朗普首度执政期间,不愿受国际机制的约束,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万国邮政联盟、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12个国际组织和条约。可预料的是,特朗普在第二个任期中也难改其执政理念,其对部分国际和地区组织表现出明显的厌恶和反感,可能会影响气候变化等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的全球性挑战。
在欧洲地区,乌克兰危机的走向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拜登政府联合北约盟友将乌克兰作为战争代理人,试图长期消耗俄罗斯。为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减少乌克兰危机对美国战略资源的消耗,以便以相对小的成本维护美国的霸权,特朗普可能会兑现竞选承诺推动俄乌停火。如果美国不愿在援助乌克兰上投入更多,必然会施压乌克兰与俄罗斯进行停火谈判。这将有助于缓和已走到直接军事冲突边缘的美俄关系。但由于美国国内存在强烈的反俄仇俄情绪、北约的强大惯性以及欧洲盟国对俄罗斯的长期担忧,美俄关系的改善并不容易,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欧洲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尖锐对立也难以迅速改变。
特朗普的重新执政将使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变得复杂。特朗普惯于以胁迫性手段施压盟友“承担更大责任”,可能导致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之间的龃龉增多。另外,美国的一些西方盟友与美国民主党和建制派的意识形态相似,对特朗普“破坏民主制度”却能卷土重来感到失望。加拿大学者尚恩·纳琳提出,美国的盟友可能会认为,特朗普代表的“美国法西斯主义”会侵害他们的利益,因此需要重新考虑与美国的关系。一些国家的战略自主意愿将上升,未必会在所有问题上追随美国。对西方以外的其他国家而言,美国的胁迫行为加码,会让他们更加支持一个多极化的世界。[11]
在中东地区,美国将支持以色列消灭哈马斯,推动更多阿拉伯国家参与加沙的战后重建。由于美国严重偏袒以色列,可能不会在巴以问题上投入太多外交精力,而是会着力推动更多阿拉伯国家恢复和改善与以色列的关系。如果巴以冲突降温,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伊朗的冲突也可能降温。在政府内“右翼鹰派”和国内犹太势力的推动下,特朗普很可能对伊朗及“中东抵抗之弧”实施更大的军事威慑和经济制裁,以试图全面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
在亚太地区,美国的极右翼“鹰派”势必推动更极端、更激进的反华政策,中美之间的脱钩断链可能愈演愈烈,新冷战色彩会更浓。对于拜登政府为围堵中国构建的美日韩、美日菲、美英澳(AUKUS)等三边机制,以及强化的美日印澳四边对话机制(Quad),特朗普未必会给予同等重视,但可能会加以方便地利用。如果特朗普在贸易和安全等问题上向日韩施加更大的压力,届时亚太安全环境将变得更加复杂。
结语
2024年美国大选是美国政治和世界政治中的大事。美国两党的深刻分歧和激烈较量,随着大选选情的发展而变化,而这种分歧和较量,并不会因为特朗普的当选和未来再度执政而消失。在美国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的背景下,特朗普及共和党必然会受到民主党及其支持者的质疑和挑战。在国际政治中,美国也按照“赢者通吃”的规则行事,追求绝对安全、大搞霸道霸凌,导致大国失和、冲突频发,国际社会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保护主义、保守主义、单边主义、民族主义一旦再度释放,将给国际社会带来新的冲击。对于这个冲击,中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以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予以应对。
(本文系202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美国政治生态变化和两党对华政策比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2AGJ011)
注释
[1]P. Baker, "An Assassination Attempt That Seems Likely to Tear America Further Apart," 14 July 2024, https://www.nytimes.com/2024/07/14/us/politics/trump-shooting-violence-divisions.html.
[2]刁大明:《美国共和党“特朗普化”的新发展》,《现代国际关系》,2024年第2期。
[3]根据国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报告,美国2023财年(从2022年10月到2023年9月),在美墨边境被执法人员逮捕的非法移民数量超过240万,比2021财年增长40%,比2019财年增长100%。See "Fact sheet: Final FY23 Numbers Show Worst Year at America's Borders," 26 October 2023, https://homeland.house.gov/2023/10/26/factsheet-final-fy23-numbers-show-worst-year-at-americas-borders-ever/.
[4]“Remarks of President Joe Biden —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2024, https://www.whitehouse.gov/state-of-the-union-2024/.
[5]《美媒:两党恶斗折射美政治机能障碍》,2024年2月26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91945473931017717&wfr=spider&for=pc。
[6]Washington Summit Declaration, 10 July 2024,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227678.htm.
[7]牛新春:《加沙冲突的背景与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23年第11期。
[8]A. John and D. Gallagher, "Arab American Democrats Push for 'Uncommitted' Vote in Michigan Primary to Send Message to Biden about Gaza,“ 26 February 2024, https://www.cnn.com/2024/02/26/politics/michigan-primary-uncommitted-biden-gaza/index.html.
[9]"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Harris Following Meeting with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of Israel," 25 July 2024,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4/07/25/remarks-by-vice-president-harris-following-meeting-with-prime-minister-benjamin-netanyahu-of-israel/.
[10]"Kamala Harris' Full Speech at the 2024 DNC," 23 August 2024, https://www.cbsnews.com/news/watch-kamala-harris-full-speech-at-the-2024-dnc/.
[11]S. Narine, “Whether It's Trump or Biden as President, U.S. Foreign Policy Endangers the World,“ 21 Mary 2024, 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ether-its-trump-or-biden-as-president-u-s-foreign-policy-endangers-the-world-225524.
责 编∕李思琪 美 编∕梁丽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