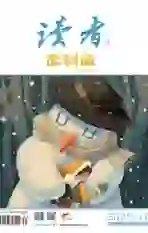奶奶的花
2024-12-18苏七七
一
我的四姐有个小花园,她种了许多娇艳的花,月季啊,绣球啊,郁金香啊,但也种了一种很朴素的花—千日红。这种不需要过多打理又能开很久的花,不属于高级的园艺品种,我们小时候身边常见的花往往如此,比如紫茉莉(地雷花)、鸡冠花、凤仙花都是。
四姐种千日红,是因为奶奶。奶奶是个很有修养的人,即便她没读过书。她生在小村庄的农民家庭,但家境还算富裕。她有个很端正大气的名字,叫陈家凤。从这个名字中可以感受到家庭对这个女孩的爱重。15岁时,她嫁进了不远的另一个村庄的大家族,但彼时已经家道中落,有几亩田出租,丈夫在家里开私塾补贴家计,孩子们在家里读《三字经》,她做饭、打扫、做衣服、纳鞋底时听听,背得比孩子们熟练得多。
她有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儿,小的是儿子。女儿上过学,绣花绣得很好,参加县里的工艺品展览得了第一名,十六七岁时嫁人,不久后就去世了。女婿又娶了妻,他带这个妻子来看奶奶,她认了奶奶当干妈,之后,他们是我家一直走动的亲戚。
后来祖父也去世了,在我爸爸13岁的时候。奶奶的兄弟们问她要不要把孩子送回去学种地,奶奶没有同意,说这个孩子个子小,身体也不结实。我不知道她想了什么法子,把儿子送去了穆洋师范学校。他去报到时已经晚了,但是因为毕业考试时是屏南县第一名,所以校长还是把他收下了。
爸爸在的时候,常跟我回忆起在师范学校的快乐时光。他说他考完试就提前交卷了,在操场的双杠上玩,校长来问他为什么在玩,他说“我考完了”。说这些时他还有点得意。还说师范学校里的饭装在一个大桶里,他吃完一大碗再去打第二碗,因为个子矮打不到桶底的饭,所以他每次打个半碗快快吃完,再去结结实实打一大碗。说这事时他也有点得意。
但他在师范学校是肄业的,最后一年他生了重病,只能回家养病。医生不能确定他得了什么病,他持续发烧,难受,卧床不起。当时的情况对于奶奶是很艰难的,本来就是孤儿寡母,要是这个孩子再没了,她只怕也留不下。天可怜见吧,爸爸喝乡里郎中的草药,慢慢地好起来了。病好后他去当了代课老师,后来又成了正式老师。
奶奶一直没有再婚。小时候我听长辈们议论,说她是在书香门第得了教化,所以守贞不移。后来我长大了,觉得并非如此。我的奶奶是个从生活层面到精神层面都很强大的人,她在收入极其微薄的情况下让自己过得尽量体面,她能在丈夫、女儿都早早离去的情况下,上奉婆母下教弱子,并且在乡村的舆论环境中始终让自己立得住脚。
因为她是这样强大的人,所以她不见得相信再婚能给她的命运带来什么好的转折和变化。她不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不指望别人解决她的问题,像她这样一个身份背景不算好的寡妇再嫁,成为另一个贫穷家庭(当时绝大多数家庭都是赤贫的)的妻子,对她,对她的孩子更有利吗?我想她的内心是权衡过的—并不会。不同于绝大多数人身处绝境会心存幻想,她非常理性和现实。
二
如果说真正的独立是内心独立的话,奶奶便是真正的独立女性。她靠儿子给她的很少的钱,以及乡村生活的自给自足来维持最朴素的生活。家中的读物很少,但覆盖了各个年龄阶段,几本《小说月报》里夹着鞋样,还有《少年文艺》。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暑假跟奶奶住的时候无书可读,把这些《少年文艺》都读了。订《少年文艺》这种事情只有我爸爸会干,我小时候他也给我订过《儿童时代》,也许他小时候见过家里订的各种读物,所以无论如何时移事往,内容如何更新换代,他还是保持着某种奇怪的惯性吧。我在《儿童时代》里读到一篇《星孩》,有图有文,看后大哭。长大后知道那篇文章的原著是王尔德。人性的光辉永远是像星星一样闪耀并感染人的。
爷爷走后,奶奶要扫村里的巷子,肯定会有人欺侮她,但她挺住了,没有被打垮。她的境况很糟,但也没有太糟:生活虽然勉强糊口,但儿子毕竟是有工作的,孙女孙子们一个个被送来,她并不那么寂寞。她不是一个需要男人当主心骨的女人,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奶奶和妈妈之间是有矛盾的,但她们从不当面起冲突,从没撕破脸。奶奶跟孙女们抱怨,妈妈不怎么抱怨—这不说明妈妈更好,而是她身上可被吐槽的点真的很多,特别是重男轻女,把唯一的男孩宠坏了,奶奶可被抱怨的点是很少的。我家在县城起了新房子后她们便一起住了,那时大的姐姐们都出嫁了,最小的姐姐住楼下客厅边上的房间,哥哥住楼上的单间,爸爸妈妈和我住一个套间。我的房间和哥哥是同样的朝向,有大窗户。奶奶住二楼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她说过那么几回:“要是房间有窗户就好了,但住了新房子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对于儿子和媳妇把自己从乡下接来养老这件事,奶奶是知足的,孩子孝顺,这是多么体面的事。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终于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新时代的生活。奶奶在她那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门口放条长凳,坐那儿晒太阳。那个走廊阳光非常好,她把一些小吃食存下来藏在怀里,我路过时跟她说话,她就拿两瓣橘子,或者是一块很硬的小糕点给我吃,细水长流又很“小确幸”地释放她的爱。
姐姐们回来,都是跟奶奶挤在一张床上睡,我有时也跟奶奶在一张床上睡。她没有什么所谓的“老人味”—也可能是我们美化了记忆,在当时的卫生条件下,洗澡的频次不高,而且她还有一点儿漏尿。但她换洗衣物是很勤快的,也或许是她的人格魅力打败了这么点儿气味。妈妈会大发脾气,奶奶不会;妈妈重男轻女,奶奶不会,她有超越她的时代的认知。
别人跟她说:“你有一个孙子吧?”
她笑着说:“我有7个孙子。”
三
一个人能超越时代真的是不可思议,特别是大半辈子处境如此困难的女性。我想,也许是因为奶奶的爸妈给她起名叫“陈家凤”?也许是因为我的祖父是个温和的人,信任她,爱重她?她能力强、心态好,面对时代与社会,她没有抗争的可能与机会,但她还是保全了自己。她从来没有出门工作过,却一直保持独立、自信,没有被摧折,也没有去摧折别人。
但人性的弱点她完全没有吗?还是有一个。我的大姐是第一个被送到她身边请她抚育的孙女,她也特别偏爱这个长孙女,即便后来被送去的姐姐们都能感受到奶奶是那么好,但奶奶对大姐的偏爱依旧存在。只是她的偏爱没有变成溺爱,也没有不讲道理地偏心,所以大家就都谅解了。
奶奶去世时是个冬天,她似乎有预感,提前给自己换了干净的衣服。大家发现那天她没有出屋,很安静地躺在自己的床上。我是后知后觉的,上学回来才知道奶奶去世了。开始办丧事,她的娘家来了很多人,干女儿也来了,干女儿的女儿也来了。
我简直都哭不出来,我像是还没理解、没接受似的。爸爸很烦躁地要我去写个悼文之类的东西。我已经上高中,大家都说我文章写得好,但我不知道怎么写。我真的不知道。我没写出来,爸爸有点儿生气,但也没怪我。
每年清明节,我家都有扫墓的大行动,曾祖父、曾祖母和爷爷在同一个地方—奶奶独自把他们合放在一起,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件了不起的事。奶奶把自己放在另一个地方。听姐姐说,奶奶是嫌爷爷太早把她抛下,她一个人承受了太多。爸爸在一座风景优美的寺庙里。他们俩都很有个性,自己走了后去哪里待着都自己说了算。我的姐姐和姐夫们在三处地方忙活了一天。我因为嫁得远,没有去成,大家对我很纵容,没说我不好。
哥哥成家后,我和爸爸妈妈住的套间就让给了他和新媳妇。妈妈住进了奶奶住过的没窗户的那间屋子,我回去了有时候跟她挤着睡。
不知道为啥,这间没有窗户的不算好的房间,因为奶奶住过,倒也没有特别不好了,甚至还让人觉得有点儿好。可不可怕?人就是这么主观的动物。
回到千日红吧。为什么四姐要种千日红呢?为什么我在花市里见到千日红也忍不住买一束呢?因为奶奶住在乡村时,到春天就总要种两三盆千日红,摆在屋头矮墙上,好看上大半年,一直到秋末,花尽了,她又把种子收起来,等着第二年再种。她还把种子分给村庄里的女人们,村子这里、那里都开着花。
她是个有创造力、有审美的人。她输出她的审美。有喜事时,乡邻们互相送红蛋。在我们那儿,红蛋是在鸡蛋上贴一个剪纸花样,喜鹊啊,石榴啊,是极美的小写意。花样是女女相传的,但到了奶奶这里就有了变化,有了改良,大家来她这里要花样,她用一支很钝的铅笔给大家画花样。我把奶奶剪的一帧剪纸镶在小画框里,去很远的地方时,生活有变化时,都一直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