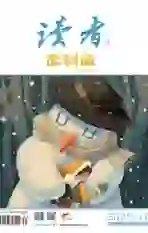聋表叔
2024-12-18徐徐
前些天在旧书页里翻出一张20多年前的照片,看见了聋表叔的背影。照片里他扶着犁,春天的土地在他身后看上去粉扑扑的,两头牛也矫健,远处的苍山像有了一点点青气。
聋表叔姓方,是舅爷的长子,祖母的大侄。侄子来看姑,是天经地义的事,自从我出世,我们就常见面。有时舅爷让他提来新摘的桃、苹果,或者一块羊肉;有时让他来帮着我们春种秋收;有时什么事也没有,就是来看看,也要走30里山路。
我总能最先发现他来了。我喜欢看着门前那条山路,像是在等他来。总有人从山路上经过,要是有个穿红挂绿的,从远处看,就像水墨山水画里的一树桃花,惹眼。大多数人不停留,偶尔也有人抄小路下来,像聋表叔。真看见他来了,我要跑着去迎。
要么他指着一朵花叫我看,或者我指着菜地里一个又大又圆的南瓜叫他看。要么他给我比画什么,我慢慢地觉得看懂了,就学着给他比画。我喜欢他,据说我四五岁时,跟着他,一声一声地喊“表叔,表叔”,想要他答应一声,直喊得声嘶力竭,他看我哭了,伸手擦拭我的眼泪,顺便揪一下我的胖脸,依然笑眯眯的。祖母说:“你表叔听不着,是聋表叔啊。”像是被破了题,自此之后我就不想着有一天他开口说话了。
我十二三岁时,我们那儿终于要修公路了。那时修路,几个乡镇的人齐上阵,叫“大会战”。聋表叔他们在离我家四五里远的地方扎营,几乎每天晚上他都会来,一头汗,送给我们一个碗大的白馍,用手帕包着。祖母比画着说,他干重活,要他吃到肚里去,回头别送了。他比画着说,一顿有两个馍,他吃了一个。他鼓着肚子,表明他吃饱了。后来,听别人说,每人只有一个馍,他舍不得吃。缺衣少食的日子里,这份心意格外珍重。
聋表叔两岁多时,有一天指着远处冲天而起的土石,那儿正在修大寨田,他跟舅婆说:“放炮,不响了……”舅婆说:“轰响,咋不响?”他没有回话。他听不见了,因为发烧打过链霉素。舅婆说,之前会说的话,之后慢慢地也不会说了。
别人叫他的名字只叫了几年,后来喊了不应,也没人喊了。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英祖。
他的世界彻底安静了,眼睛依然有神。上不成学,小小年纪就在庄稼地里,拿着小小的锄头挖呀挖,挖成了一把庄稼好手。等能砍柴挑水了,就砍柴,就挑水。
大多时候,他脸上有些笑意,看上去干净柔和。偶尔也会发牢骚,就像别人来请他帮工,跟舅婆说,舅婆答应了;舅婆跟他比画时,他摇头,意思是自己的庄稼还没弄完呢。不过,他听话,第二天还是去了。总有人请他帮工,他一辈子都没有学会偷懒,这样,他总有干不完的活儿。
有一年春天,他带着桃树枝和苹果树枝,又在山路边折了一捧兰草花,香喷喷地来了。和了稀泥,泡了构树皮,背着刀,提着锯子,他去嫁接桃枝,我跟在他后头。他站在桃树下,选一枝锯掉,抽出镰刀在留下的枝丫中间开口,用小木片顶着,再仔细削好他带来的桃枝,插进裂口,取下小木片,给接口那儿抹些稀泥,再用构树皮缠紧,事情就这样成了。后来我看书,知道了这一种嫁接法为腭裂嫁接。3年之后,他接的桃枝长出了红脸蛋一样的桃子,着实叫人欢喜;至于苹果,又红又脆,他在老枝上接的那几枝新枝成了主枝,结了好多果子。
中学课本里有一篇鲁迅的文章,开篇写:“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每每读到这句,我便想起聋表叔。
有一年他来我家,夜半鸡叫,他打了手电去看,一只黄鼠狼正在鸡笼里。他找根棍子打,黄鼠狼灵巧得很,眼看着要从侧面逃走,他伸手一把掐住黄鼠狼的脖子,那一刻,他简直神勇极了。
舅爷过了中年,就和他睡在一起,直到去世。冬天烧暖炕,夏天铺凉席,颇有《弟子规》里“冬则温,夏则凊”的韵味。舅爷风烛残年,身上痒,他给挠,挠得细微,常常挠着挠着,舅爷就睡着了,他还在挠……他只是做他能想到的、看到的,他不晓得老有人说他是父母的贵人。
听不见,世上所有的纷争与他无关,污言秽语也与他无关。他的眼神一直清澈,偶尔有点儿跳跃。小麦扬花,葡萄满架,或者遇到一条胖胖的小狗,他的眼睛有些笑意,脸上还有浅浅的酒窝。赤子也许就是这样的。
一晃眼,聋表叔老了,好几年没见着他。前两天在网上问小表叔:“聋表叔可好?”小表叔说:“好着。”好多话不知从何问起,愣怔了一会儿。“好着”胜过千言万语。
有位长辈叹息说,人生不过就是种了六七十回麦子,收了六七十回麦子。
我又想起了聋表叔,那些地,他种了麦子,便收了麦子;他种了玉米,便收了玉米;他栽了苹果树,便结了苹果。一抬头华枝春满,再抬头天晴月圆,好像什么也没有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