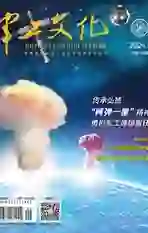文字里的时代不会远去
2024-12-17沈俊峰
四川女作家、三线军工二代晓露近日出版《远去的天星沟——我的三线人生》(新华出版社)。阅读这本书,我脑海中许多往事被唤醒,仿佛重走一遍青春路。这让我坚信,文字里的时代或人生永远都不会远去。
这本散文集特色鲜明,具有文学、历史与口述史的特性。自古文史不分家,其文字特色与品位,应该属于跨文体写作。这些文字的写生册页,具有时代的原生态,虽然有些线条略显粗糙,许多地方或许只有轮廓大意,却真实生动,精彩纷呈,让人印象深刻。
同为三线军工二代,阅读该书有着十足的亲切感,它唤醒了我许多沉睡多年的三线记忆。从1964年开始,迫于国际斗争形势需要,我们进行了历经三个五年计划的“三线建设”,轰轰烈烈,“好人好马上三线”。
那时,我们将沿海、边疆地区向内地划分为三条线。一线指沿海和边疆地区;三线指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及湖南、湖北、河南等内地地区,其中在西南(云贵川)、西北地区(陕甘宁青)的三线建设俗称为大三线;二线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区。在一、二线地区的三线建设又俗称为小三线。三线建设以战备为中心,以工业交通和国防科技为基础的大规模基本建设,共投入2050余亿元资金和几百万人力,几千个建设项目,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动员之广,行动之快,在中国建设史上是空前的,对其后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几百万人响应号召,从城市转入偏僻的荒山野岭,默默fjfZwKVYZvkD0pjNB+spdD0NftkqsUY9GmaGSWVrKdI=奋斗,命运由此改变。命运被改变的,还有更多像我们这样的三线二代、三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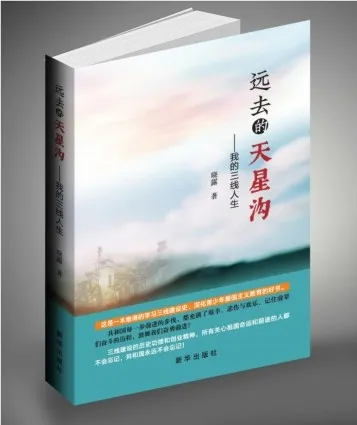
作者晓露在四川省南川县(现重庆市南川区)的天星沟,我在安徽省大别山腹地的霍山县仙人冲,两地虽然相隔一千多公里,但是这本书让我明白,我们的生活几乎如出一辙,有着许多相同之处。
我们都属兔,同龄人,自小都是跟随父母在三线军工厂“散养”长大,都是初中毕业考上中专学校,毕业后重回工厂,都当过团委委员。有趣的是,她上小学要自带高凳矮凳,我所在的子弟学校则桌椅齐全。这或许是中部与西南在当时的差距缩影吧。她在书中写到装配车间因丢失一粒小钢珠而停产寻找,我在总装车间帮忙时,也遇到过一粒小钢珠不翼而飞而翻箱倒柜地寻找。我们都知道那一粒小小钢珠的不同寻常的意义。山区文化生活单调,她经常组织团员去爬山,我也经常和一帮青年去爬山,在山顶比赛谁喊的声音传得更远,往山下滚石头,感受那种天高地阔的力量。
不同的是,她爬山收获了爱情。为了纪念那条爱情小路,她取笔名“晓露”。我进山要比她早几年,她上学却比我早一年。她一直坚守在三线,当过企业中层领导、分厂厂长,经历过三线军工企业从建厂初期到搬迁进城的全过程,感受过企业在保军转民、整体搬迁与二次创业过程中的艰辛与阵痛。我在三十岁时,使尽洪荒之力出山进城。我们习惯说“出山”,他们习惯说“出沟”。

《远去的天星沟——我的三线人生》,虽然写的多是作者自己的经历,其写实文字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具有时代性,生命力应该比一般的文学作品更强大。生活远比文学精彩,当我们拂去时光浮尘,蓦然回首,最能打动我们的,原来是我们曾经的岁月,有着诗一般的品质。当年,身为三线军工子弟(职工),打量父辈三线军工,只觉得普通、平凡,如今站在历史的高度,我感受到三线人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默默奋斗、奉献拼搏、报效国家的精神伟大。我们今天的发展与强大,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硕果,当然离不开“三线建设”夯实的经济基础。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五周年、三线建设决策六十周年,这本书的面世,便有着特殊的意义。原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主任王春才评价该书:“一滴水可以映射出太阳的光辉,天兴厂的发展史,也是许多三线企业发展的缩影。”
文字里的时代,文字里的人生,不会远去,将成为永恒。
(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