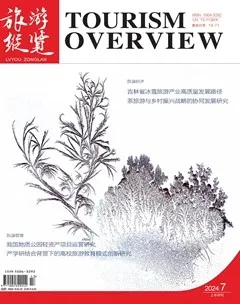世界文化遗产永顺土司遗址的保护与开发研究
2024-12-16张琼李德顺
摘 要:文章梳理了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的代表——土司制度的概况,同时通过调研永顺土司遗址,发现该遗址保存了大量作为中国土司制度有力见证的遗迹。结合该遗址的开发现状,并运用SWOT模型分析其旅游开发所处的环境条件,发现从文旅结合的路径入手更有利于永顺土司遗址的长远发展。因此,本文提出永顺土司遗址应以旅游开发为支撑,兼顾教学与文化传承基地的多功能建设路径。
关键词:永顺土司遗址;保护;开发
中图分类号:F590.7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度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专项课题“乡村振兴背景下湘西州红色文化传承与开发研究”(项目编号:KYZX13)的研究成果。
引言
文化遗产是国家民族文化历史成就的重要标识,永顺土司遗址是证明土司制度存在的重要物证,是研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我们要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是国家与社会的一项重要课题,目前有文旅融合、图书馆数字化、完善法律制度、专业技术等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途径的相关研究[2-5]。本文旨在研究永顺土司遗址在“申遗”成功后的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与开发问题。
一、世界文化遗产及其在中国的分布
文化遗产主要分为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有机进化景观、关联性文化景观三类。从表1中的数据可见,欧洲与北美地区的文化遗产分布最多,占过半总数。除中国外的其他几大文明古国文化遗产的数量占比不多,即使有了2000年《凯恩斯决议》强调的全球平衡原则,也难以避免数据不平衡的现象出现。这一现象与战争与和平、文化与传承、社会经济发展、保护开发力度差异等影响因素相关。

我国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积极申报世界遗产以来,截至2024年已达到40项。表2是中国各个年度申遗成功项目的数据对比,1987年是申遗成功元年,1994—2000年是我国申报世界遗产的“高产期”,随后项目数量处于平稳增长状态。
我国文化遗产的地理分布与地区的历史悠久度、人口稠密度相关,总体是北方的文化遗产多于南方。地域性差异有以下三点:第一,北方地区的文化遗产多与国家政权历史更迭相关、与宗教传播路径相关,比如长城、莫高窟等;第二,南方地区的文化遗产多能反映当地的文化制度、历史变迁有关,比如布达拉宫见证了藏族地区的文化发展;第三,另有一部分遗址是体现历史中人类改造世界的重要证据,比如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等。

二、土司制度的概述
(一)中国土司制度的历史与发展
土司制度的雏形是唐朝的“羁縻”制度(少数民族首领统治);元朝时期中央政府在西南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设立行省的同时建立了土司制度(少数民族以蛮治蛮制度);明朝对土司制度有所继承和发展;土司制度在清代走向衰亡,其重要标志是1726年雍正帝大规模地改土归流,通过对土司采取招抚和镇压的方式基本完成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央集权统治,但土司这一制度直到清末还有残余留存。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民族地区的交流融合,有利于当地社会开放与经济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
(二)土司制度简介
土司制度的显著特点是土司拥有对辖地内的政治绝对权力、经济绝对权力、军事绝对权力以及对土司职位的世袭制度。除以上四条绝对权力之外,土司制度在中央集权的王朝中承担以下义务:军事征调必须服从中央政府的义务;地方土司必须按要求向中央政府履行朝贡与纳赋的义务;中央对地方的恩赏惩戒,这体现在政治中统治阶级倡导的赏罚分明。
三、永顺土司遗址保护、开发现状分析
永顺土司遗址位于湖南永顺县城东19.5千米处的灵溪镇老司城村,地理坐标东经110°,北纬29°,海拔268~360米,整个遗址群占地面积25平方千米,背靠太平山,面临灵溪河。城址可分为宫殿区、衙署区、街巷区、墓葬区、宗教区、苑墅区,城中各种建筑宏伟景象依稀可见,城墙、道路等仍能够辨认。
(一)永顺土司遗址介绍
永顺土司遗址又称老司城,是彭氏土司八百年王朝的都城,是古溪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史称“五溪之巨镇,百里之边城”。939年,土司彭仕愁发动对马楚政权的“溪州之战”,战败后议和,彭氏家族在政治上取得政府承认的合法统治地位。双方以溪州铜柱为证,铜柱铭文2 600余字,记录了双方会盟誓状,铜柱也见证了土司制度的官方确认。
遗址现存功能区简介如下:老司城因山为障、以水为池构成坚固的防御体系,现存城东南方向通往羊峰、王村的古道上有多座石桥,均有防御关隘的特征,老司城宫殿对岸的古牛山顶哨卡遗址也有防御性质。老司城宫殿区位于遗址北部,周长436米,面积14 000平方米。宫殿区有城墙遗址、城门楼遗址、排水沟遗址、宫殿主体建筑遗址等。老司城衙署区位于宫殿区南侧,周长408米,面积87 624平方米,墙体部分保存较好。老司城的街巷区位于西门河岸,1793年《永顺县志》记载的:新街、左街、河街、鱼肚街、马蝗口、五屯街、东门街,现存地灵坊土地庙、人杰坊土地庙、河街、左街、正街、纸棚街等遗址。老司城的宗教区位于城东南郊,是永顺彭氏土司的家族墓地。整个墓园在山脊上筑成4~5列台地,墓地面积1万平方米,已探明土司及眷属墓葬38座。另有牌坊、神道、照壁、石像生等遗址。老司城宗教区的祠庙有祖师殿、观音阁、五谷祠、关帝庙。其中祖师殿是湘西保存最完好的古代建筑,也是湘西的道教圣地。老司城的封邑地在外城,是彭氏家族的封邑圈,目前保留多处石刻、栈道遗址、贵族墓地等。在贵族封邑区与主干道周围,分布着农民的村寨,这里保存很多古老的文化标记,比如摆手舞、毛古斯、梯玛、西兰卡普等。
(二)永顺土司遗址的重大意义
世界遗产委员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土司遗址(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遗址、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展现了中央政权与地方族群在民族文化传承和国家认同方面的人类价值观交流,是中国西南部土司管理制度的特殊见证。
永顺土司遗址是我国多民族国家政治制度创新的历史物证,它的存在与发掘见证了中国封建时期统治者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统治制度的创新,使之从史籍记载的文字上与现实遗存中得到有力的证明。永顺土司遗址同时也是古代中国维护民族多样性的典型样板,永顺土司遗址出土的物证印证了史籍记载封建时期中央对少数民族地方的一系列安抚政策存在的真实性,证明了封建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民族地区的管理策略,支持了古代统治者维护民族多样性的统治方式的存在。
(三)老司城景区旅游开发现状
老司城景区是在土司遗址基础上开发的AAAA级旅游景区。景区依托获评世界文化遗产的契机,在保护遗迹的基础上发展旅游业。目前,旅游开发集中在核心区周围的区域(核心区以保护为主),景区修筑了栈道,将祖师殿、文昌阁非遗展示区与遗址区串联起来;在原有的旅游资源基础上,打造出灵溪河游船、非遗传统习俗表演、特色餐饮等贴合实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
“申遗”成功后,永顺县以老司城世界文化遗产为龙头,整合猛洞河、湘鄂川黔革命旧址、不二门国家森林公园、小溪国家自然保护区、芙蓉镇等旅游资源,将永顺县打造成世界文化生态旅游目的地。但从旅游市场的反馈来看,从2015年土司遗址申遗成功,2016年老司城景区开放至今,仍存在游客数量不及同为AAAA级旅游景区的芙蓉镇的现象。对此,李佳晶等人认为是管理者没有较好地利用遗产地的文化精髓创造出文旅精品。陈晓认为是老司城遗址交通不便、景观观赏性不强、业态融合不足所导致。李然与王春阳认为老司城村村民参与社区建设过程中面临经济场域无权、社会治理场域弱权、自身参与能力不足等诸多困难。针对老司城景区旅游发展现状,考虑其主客观环境情况,作出以下SWOT分析(见表3)。

四、永顺土司遗址开发与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建议
(一)保护建议
首先,树立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合理保护现有文化遗产资源。土司遗址保护者要以保护为出发点,自觉遵守《世界遗产公约》,根据土司遗址的特殊意义,不做机械性、简单性的保护,听取文物专家意见,以保护文化为出发点开展遗产保护工作,坚决不进行游走在公约边沿的功利性开发[6]。
其次,针对土家族没有本民族文字,缺乏本民族对于土司文化文字记录的这一缺憾,土司遗址保护工作者可以走出遗址,深入土家族聚居区进行走访调研,寻找历史文化遗存,考证历史传说,探寻土司历史,采用现代新技术记录与保存文化遗存。
最后,加强本地区居民价值宣传教育,培养文化与遗址的保护意识,提升当地居民的参与程度,依靠群众开展遗址保护工作。遗址中心区附近居民世代居住于此,应注意避免无意识损坏遗址的现象,需要提高居民保护和传承遗产的意识。可将当地居民优先纳入旅游公司的管理体制,吸引当地居民参与旅游产业的开发,提升当地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积极性,实现当地居民与景区开发和谐共生。
(二)开发建议
首先,以生产特色旅游产品为出发点,采用多种形式开发旅游精品。以中国土司制度为主题,建成“彭氏问祖”的寻根问祖主题展览馆、举办“彭氏海内外恳亲会”活动,吸引相关彭姓游客、文化教育工作者。面向研学旅游市场,打造出文旅精品;发挥现有民俗表演优势,推出参与性较强的演艺活动;与企业合作,推出土司文化标记的文创产品[7]。
其次,建设地区文化教育教学基地。针对当地的文化资源禀赋,树立乡土教材基地典范、建设民间传统文化教学基地。依靠遗址背后深刻的土家族文化底蕴,挖掘土家族非物质文化,努力建成土家族文化学习、土司文化研究的传播教育基地,为乡土教材编写、传统文化研究作出贡献。联络大中专学校,培养青年一代学习土家族传统文化,传承优秀文化。
最后,以传承文化为立足点,建设文化研究人才培养基地。与省内外优秀民族学研究单位深度合作,重视遗产保护开发的应用研究,加快专业人才培养,成立研究生校外实践基地。通过校企合作宣传教育,让更多人学习和了解土司遗址遗产的文化价值,培养民族学人才。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永顺土司遗址现状的梳理、对遗址保护与旅游开发的探讨,发现永顺土司遗址的存在不仅有重要的文化保护与传承意义,对于旅游开发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开发与保护的过程中,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和谐的人地发展是关键点,永顺土司遗址的开发与保护可以沿着“以文化旅游开发为支撑,以文化保护和传承基地建设为使命”的路线展开实际工作。
参考文献
[1] 何银春,张慧仪.文化遗产见证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价值阐释——以世界文化遗产永顺老司城为例[J].怀化学院学报,2022(4):14-19.
[2] 张蕾,路云生,刘旭光,等.基于文旅融合的孟府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研究[J].档案管理,2024(1):84-87.
[3] 徐彤阳,黄映思.加拿大公共图书馆文化遗产的数字开发与保护调查研究[J].图书馆,2023(1):65-72.
[4] 任鹏举,马明飞.“区域”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划区管理工具法律问题研究[J].中国海商法研究,2022(3):54-64.
[5] 吴振.基于运动捕捉和虚拟现实技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舞蹈的保护与开发研究——以藏族舞蹈为例[J].舞蹈,2023(4):90-96.
[6] 黄纳,袁宁,张龙,等.文化景观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浅析——以杭州西湖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2(2):187-190.
[7] 龙先琼.土司城的文化透视:永顺老司城遗址核心价值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