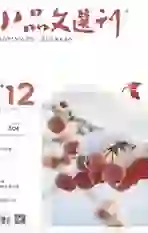大豆至简
2024-12-09宋扬
我幽暗而冷寒的旧日生活曾被一粒粒黄灿的豆子照上一抹暖光。我们宋家坝人说的豆子,只指大豆。那些年,在宋家坝,豆子只是大米、玉米、红薯之外可有可无的陪衬,并没有获得成行成排大规模播种的机会。肚里荤腥少,乡亲们对稻谷、红薯、玉米的需求量大,豆子产量低,又不当顿,只能在稻田边的田埂侧或玉米地的边边角角见缝插针零星点上一些。
稻谷渐黄的时候,豆荚慢慢鼓起来。忍不住馋嘴的可以开始剥青豆吃了。此时的豆子,清嫩之豆香气最为浓郁,用来烧猪肉、烧鸡最合适不过了。第一批青豆上市,其价钱都快赶上猪肉了,我家自是舍不得轻易吃青豆的,母亲把青豆一粒粒剥下来,背到镇上卖给吃得起的人家,母亲也兼卖其它蔬菜——茄子、生姜、黄瓜、南瓜……她心疼我和妹妹正在长身体,卖掉青豆,有时也割回两斤猪肉,用来炒青椒。如果恰逢雨天,生意不好,青豆没卖完,我和妹妹就也能吃上心心念念的青豆烧肉了。
收走稻谷,砍掉玉米秆,配角儿豆稞俨然成了深秋田野的主角。秋风吹,百草黄,豆叶渐枯,一粒粒饱满的豆荚只等时间赋予它们深沉,赋予它们金黄。找个晴朗的日子,母亲把豆稞从田埂里一窝一窝拔起来,背回家,让它们平躺在院坝里晒太阳。连续几个响日头,豆子在豆荚里收缩变小,一翻,能听到豆子在滚动,哗哗响。有的豆荚已被晒开口,“啪嗒……啪嗒……”,连枷声起,无数豆粒在空中飞舞,它们终于见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抹秋阳……
母亲把晒干的豆子收拢来,装了小半蛇皮口袋,小心埋进谷仓里的谷堆中,她要用谷子的干燥保障豆子不回潮,不被虫蛀。这些豆子,将在腊月二十八九派上大用场。
转眼到了腊月二十八的晚上,母亲从谷堆里刨出那小半袋豆子,择了择,挑出两碗留作种子。剩下的,洗干净了,通通倒进大盆里,泡上清水。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几家共同出钱找老石匠,他凿的那块大磨盘,一下子热闹了起来。磨盘放在表婶家的屋檐下——只有她家的房子是宽屋檐,下雨也淋不着。大家端着头晚泡好的豆子,挑着一副准备装豆浆的空桶。往磨盘心添豆子的掌勺工作,大人们不放心交给我们小孩子操持。勺中豆多豆少、水多水少,全靠经验,还得手快——推磨人的节奏几乎是恒定的,掌勺的稍慢,被快速转动的磨杆打断手的可能都有。这样危险且精细的活儿,自然只能交给心灵手巧的女人们。磨盘“嘎吱嘎吱”的单调韵律中掺着大人们爽朗的笑声,小孩子们在磨盘旁的院坝里玩弹珠,打纸烟盒,真真假假地干仗……直到所有豆子都推完了,各自回家去。
豆浆挑回家,用纱布滤掉豆渣,立即上灶煮豆浆。父亲把豆浆翻进锅里,浆水一开,母亲舀出两大碗,兑上过年才买一些的白砂糖,招呼我和妹妹赶紧热热地喝下。多年后的今天,豆浆早已是最稀松平常的早餐之一,但我固执地以为后来喝过的所有豆浆都远不及那些年母亲做的豆浆的万分之一,大概是因为那豆浆里有母爱的滋味,有乡亲们的欢声笑语,有时光远去的背影,还有那些涩滞生活中的点滴光泽。
豆浆不再翻滚时,父亲减去了灶膛里多余的柴禾,母亲开始往锅中均匀抖洒石膏水。不一会儿,锅中那一汪原本黄白的豆浆慢慢变得淡绿清澈了,松松散散的豆花也魔术般沉淀析出。母亲轻轻舀出一小盆白玉般的豆花。此时,柔弱的浆水,已经站立成挺拔的姿态。这座白玉一样的小山,就是我们的午饭。母亲双手捧起一个筲箕,在锅中反反复复不轻不重地按压,压实了,抄起菜刀横平竖直走几刀,那些豆花儿又蜕变成一方方豆腐。父亲早已准备好一块新抹布,摊在大筲箕中。母亲捞出豆腐块儿,把它们逐一平铺在抹布上,那一方方“白玉”似乎瞬间明亮了四壁黢黑的厨房。
豆浆和豆花儿都只是“一顿鲜”,豆腐才是老家餐桌上经久抵事儿的。豆腐切片,菜籽油烧烫,煎成“两面黄”,能放十天半月不坏,做蒜苗回锅肉时放上几片,若绿锦上添金花。豆腐不煎,哪怕只是与白菜一道做成素汤,也一清二白。豆腐也舍不得全吃完,父亲还要留下一些做红豆腐。把大块的豆腐改刀,铺在洗净晒干的稻草上,再盖上一床厚棉絮,不出几天,毛茸茸的白絮便爬满了整个豆腐。父亲用筷子小心夹起霉豆腐,先过白酒,然后放进调jbBH+slHRsN93SHvSyWHXJeWRMIf5Z6EylbZKDjDuCA=配了盐巴、花椒面、辣椒粉的盆里轻轻滚几圈,一块乳白的霉豆腐就成了红豆腐。装坛,掺入熟菜籽油,密封好,等过年的腊肉吃尽,蔬菜也青黄不接时才取出一两块,闻着臭臭的,一筷头进嘴,却奇香无比。如果保存得当,一坛红豆腐能紧紧巴巴对付大半年,它恒久为我家大半年寂寥而寡淡的白饭着色,让生活多出聊胜于无的微弱色彩——父亲最是懂得普通人家过日子需细水长流的生活秘笈。
偶尔,也有敞开肚皮吃豆子的时候。外婆家在我们宋家坝上头的泡桐崖,不远,但那里地势高,渠水难上去。外婆家与我家恰恰相反——她家田少地多。地多,点的豆子就多。记忆中,每年冬天,外婆总要喊我们去她家磨两次豆子,不做豆腐,只为饱饱吃两顿嫩豆花。父亲和母亲忙完一天的活儿,夜幕降临了,才背着新碾的米匆匆赶去。昏黄的油灯下,外婆、舅妈、母亲有一搭没一搭拉着家常,父亲和舅舅慢悠悠喝着土酒。老八仙桌上,滚烫的豆花冒着白气,凉了,端进厨房烧滚了再端出,接着吃……烟火暖身,豆花暖心,浑然不觉间,屋外已是白霜满天。离合悲欢人间事,如今外婆早已辞了人世,舅舅因车祸离开了我们,我与表弟也都离开了故乡。关于豆花的往事就像一部蒙尘多年破损不堪的电影胶片,我无数次努力试图修复出儿时清晰的影像,到头来才发觉都是徒然。
去年回老家时,我从表婶家门口经过。不经意间,我又看见那个老磨盘,它半陷在表婶家门前的自留地里,已经太久太久没有豆子与它亲近,它干缩着,蜷曲着,四野的苜蓿、刺苞、络石藤黑潮一样漫过来,几乎就要将它完全淹没了……
汪曾祺先生说:“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人间可大,人间可小,最温暖人心的那一碗还得是故乡的烟火,母亲的烟火。心间事,舌间解,人间至味是清欢,那青豆炒肉、那甜豆浆、那嫩豆花儿、那能把一碗寡淡的白饭点缀成似锦繁花的红豆腐,无以取代。
选自《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