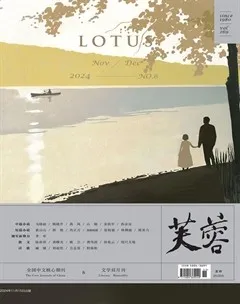在中国的蝉声里
2024-12-06耿立
耿立,本名石耿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散文家,诗人,教授。散文集《向泥土敬礼》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提名,《遮蔽与记忆》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前十,《悲哉,上将军》入选“2009年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缅想的灵地》入选“2010年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曾获第六届老舍文学奖、山东省第二届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广东省第十届鲁迅文学奖、第二届三毛散文奖大奖、第三届丰子恺散文奖。
四月秀萎,五月鸣蜩。
——《诗经·七月》
小引
这个暑假,从岭南回到中原腹地的老家,朋友款待,当把一盘炸金蝉端上来的时候,我说,谁愿意吃谁吃,我不吃。
我站起来,走掉。
大家一时惊愕。
在现实生活里,中原腹地的百姓,有吃蝉的习惯,或油炸,或煎爆,大街饭店的招牌菜必有一道美食:炸金蝉。围绕人们的口福,就形成一个产业,在夜幕低垂或黎明之时,在村头树下,在河堤树林,有手电、马灯、矿灯,寻觅刚出土的蝉;在白日,又有人用现代的工具粘树枝上的蝉。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的交界地带,蝉的交易,以数十吨数百吨计,对一个小小的蝉来说,那是多么庞大的数字,多么恐怖的杀戮。
吃野味,是某些人的不良癖好。我想到画家韩美林,有一次,他到南方采风,当地干部盛情款待,宴席中有野味火锅。天性珍爱动物的美林先生看到秃鹫的头在沸汤里滚动,心中不忍,甚是愤怒。待到招待者过来献殷勤,问美林先生“吃得高兴吗?”,率直的美林先生直接国骂爆了粗口。
我没有骂人,我从吃金蝉的酒席走掉,把尴尬留给了朋友,把内心的羞耻留给了自己。我只能阻止自己不吃,但阻止不了别人。
这个夏天,我从岭南回中原腹地的故乡,归家伊始,顿觉故乡的异样与不适,也总说不出是哪里出了毛病,心里只是压抑,只是空落,手足无处安放,陷入惊恐与心慌,觉得有巨大的静寂带来的难受。静寂吗?汽车声、工地的打桩声、空调昼夜的滴水声,各种工业美学带来的噪声,扰我思绪,使我彻夜不眠。这个夏天,在故乡,似乎比往昔多了什么,又好像少了什么。一天,我终于觉察到,所谓的心慌,所谓的难受,不就是中原腹地的这个夏天没有了蝉鸣吗?从我的童年,从我们民族的童年,那历史深处回响了几千年的蝉鸣声,它们一下子隐遁了,失落了,我一时慌张地惊问:它们去哪了?
是季节的变乱,让蝉声消失了吗?是人们的杀戮,还是别的?
我一时接受不了,在文化心理和精神上,我觉得,没有了蝉声,往大了说,就如被掘了祖坟。华夏的夏,夏朝的夏,这夏字的来源,或者图腾,就是一只蝉呢,没有了蝉声,从《诗经》开始那些塑造我们心灵的审美,到唐诗宋词里的意象,就这样,无声了吗?就这样在自然里,一下隐遁消失了吗?
没有了蝉鸣,我的耳朵好像陷入了一种别样的耳聋,犹如戈雅在一次与女儿谈论绘画时,戈雅告诉女儿的一个秘密。戈雅告诉女儿,他46岁耳聋以后,“现在听到的,比以前更多”。
女儿不相信,摇摇了头。
“因为,现在我用自己体内的耳朵(内部的听力)在听。你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愿意吗?”
女儿闭上眼睛聆听。
“听见了什么?孩子?”
“什么也听不见吗?”
女儿说:“能听见,但是没有什么特别……我听到一些遥远的声音……有一个小孩在哭……”
“那不是!那些不是!”戈雅厉声斥责。他突然滔滔问道:
“你没听见一种嘈杂在逼近——
“它沉默、恐怖,若数百头公牛践踏大地?
“你没听见一个女人的哀号,她嘶吼大哭,为着她的儿子被杀?
“你没听见她痛苦的喊声?
“没听见一个魔鬼的号叫?!
“你听!
“你听!!!”
戈雅虽然耳聋了,他依然能听到人类遭受一切之后灵魂的叹息。耳聋而心不盲。
我现在也觉得自己不如耳聋了,我现在所处的充满噪声的世界,也折磨得我近乎耳聋,耳聋反而内心的听觉更丰富,好像那远古的蝉声、魏晋的蝉声、唐宋的蝉声迢递而至,汹涌澎湃。
一
回溯4000年前的盛夏,那时我们民族最初的一抹朝霞,开始投影在历史的幕布,灿烂如锦。
初民时期,蝉是民族的精神意象,是我们民族的审美原型。中原第一个世袭制朝代——夏朝的国号就来源于蝉。
夏朝虽然没有文字,但甲骨文卜辞中的“夏”的象形就是蝉,有触须、有宽阔的额头、有网状的细纱一样的羽翼……这就是蝉的简笔画。
张晓风有这样一段文字:
关于春天的名字,必然曾经有这样一段故事:在《诗经》之前,在《尚书》之前,在仓颉造字之前,一只小羊在啮吃草时猛然感到的多汁,一个孩子放风筝时猛然感觉到的飞腾,一双患风痛的腿在猛然间感到的舒适,千千万万双素手在溪畔在塘畔浣纱的手所猛然感到的水的血脉……当他们惊讶地奔走互告的时候,他们决定将嘴噘成吹口哨的形状,用一种愉快的耳语的声量来为这季节命名——“春”。
夏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那必定是,随着炎热的天气到来,人们汗腺打开汹涌成河,头顶太阳炙烤更烈,而不管天地之间,还是白昼黑夜,一种在树间的声音,好像占去所有的时间和空间,你逃不脱它的范围,它环绕你,在清晨,在午夜。人们惊讶,说出一个声音“夏”来命名,人们捉住了它,看这个飞到树间的虫子是什么模样,它来了,夏就来了。
人们以它为图腾,以它为国号,并且,它还嵌在我们民族的名讳里,和“树间花朵”组成了一个词:华夏。
造字,命名,那可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惊天地泣鬼神的创举,《圣经》开篇即谓:泰初有词。有了词才有世界的出场,没有语言和词,一切都黑暗不彰,所以海德格尔说:凡无词处,一无所存。仓颉造字时“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这动静不可谓不大,那些鬼啊、龙啊,知道人的时代来了。
我们的先人造出华夏,这是多么惊天动地的事啊,华夏这名字多俊美,安在一群中原人的头上,为这一群人命名。华,就是花的原本,花朵是我们民族标志;夏是热烈,是我们民族的激情。
古人对蝉,充满想象、敬畏与神性的思索。先民眼里,蝉乃灵物,从泥土中来,再复归泥土中,历数载甚至上十载,再出土羽化升空,如此周始往复,“生生不息,绵延不绝”。这也是夏朝统治者的理想,想着自己的朝代世系如蝉一样永远“不死”,死而复生,万世永祚。
夏朝没有万世,就在今年的夏季,在中原的腹地,蝉没有了,蝉声也没有了,我像失魂落魄的孤苦魂灵,在寻找着蝉声,从白昼到黑夜,从城市到乡村,河道、沟渠、树林,一只蝉都找不到,一点蝉的声息都没有,不但夏朝没能万世永昌,而且这蝉声也当世而斩,断绝在文明的21世纪的今日。
蝉乃人们的崇拜之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就有了玉雕的蝉,在红山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等许多古遗址上,都有形制古朴、线条简单、器身有穿孔的玉蝉。那时蝉不仅在夏天秋天用声音陪伴先民,而且先民还把它们佩戴在身,时时刻刻与蝉同频。蝉是我们的种族记忆,我们可以从蝉的意象,来抚摸我们民族精神的脉络。陆机在《寒蝉赋序》中说蝉有“五德”,曰:文、清、廉、俭、信。“夫头上有緌,则其文也;含气饮露,则其清也;黍稷不享,则其廉也;处不巢居,则其俭也;应候守常,则其信也;加以冠冕,取其容也。君子则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岂非至德之虫哉。”这是蝉吗?这样的灵物,世间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能做得到吗?从这段话里,我们知道古代的“崇蝉”情结,人们以蝉为精神的标杆,事君立身,这是一只历史的虫子,至德之虫。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讲:
……夏铸九鼎,大概是打开青铜时代第一页的标记。……陶器纹饰的美学风格由活泼愉快走向沉重神秘,确是走向青铜时代的无可置疑的实证。……它们以超世间的神秘威吓的动物形象,表示出这个初生阶级对自身统治地位的肯定和幻想。
那时的青铜器的器物,多是突出一种原始的力量,一些夸张的造型,突出神秘、恐惧,是一种超人的历史力量与原始宗教的神秘观念的结合,我们觉得那时的青铜艺术散发着一种浓重的命运幽深气氛。
李泽厚说那些纹饰:
以饕餮为代表的青铜器纹饰具有肯定自身、保护社会,“协上下”“承天休”的祯祥意义。
在青铜器鼎、爵、觚、盘上,就常铸有蝉纹。蝉纹是先民重生、永生、沟通天地、洁净、守护的观念的显现。古人认为蝉只靠餐风饮露维持生命,却能够飞天入地,又蜕壳变化,是奇特而神秘的生物,因此喜爱和崇敬它。
玉也是古人喜欢的,再加上喜欢蝉的寓意,于是就有了玉做的冠蝉、佩蝉、琀蝉。冠蝉是古人用于冠上的帽饰,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权势;佩蝉常常被古人佩戴于腰间,寓意腰缠万贯、一鸣惊人;琀蝉含于逝者口中,仿佛在告诉世间:“今天,我入土,像蝉的幼虫一样,不要悲伤,这不叫死,有一天,生命会复活,会展翅,会如夏日出土的鸣蝉……”
先民立象以尽意,这是成熟理性后的一种情感诉求、形象表达,因为丰富的现象界有着比理性更丰沛更广大的内容和联想。这是我们民族独特的一种思考方式,用一个形象放在那里,让人直观感受它解读它,得鱼忘筌,得意忘形。这有意味的形式,既是写实,也是象征。荣格说:“每一个意象中都凝聚着一些人类心理和人类命运的因素,渗透着我们祖先历史中大致按照同样的方式无数次重复产生的欢乐与悲伤的残留物。”在蝉的身上,有我们民族太多的情感意蕴,我们先民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用最基本的形象去表达我们最丰富的情感、最丰富的思想,我们的先民“托事于物”,就如这个蝉,它不再是单纯的物理形式,一个大自然的歌手,它是富有意味的文化系统,是一个精灵,一个灵魂的符号。
蝉,蝉鸣,牵扯着中国人的历史深处的神经,也塑造了一代代中国人的敏感的听觉和耳朵。
二
蝉是有家族谱系的。它的堂亲、表亲,一串串一排排,从亚洲到非洲,从欧洲到美洲。蝉在生物学上,属于同翅目蝉科,目前世界上的蝉大约有2000种,而我们中国的蝉也有200种。
蝉自幼生活在土中,通常会在黑暗的土里待上几年甚至十几年,如3年、5年,还会有17年,这些数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质数。
这是因为质数的因数很少,在钻出泥土时可以防止和别的蝉类一起钻出,争夺领土、食物。蝉将要羽化时,蝉们于黄昏及夜间钻出地表,爬到树上,然后用爪抓紧树皮,出壳蜕皮羽化。
当蝉蛹的背上出现一条黑色的裂缝时,蜕皮的过程就开始了。6月末,幼虫开始羽化为成虫,刚羽化的蝉呈绿色,最长寿命为60~70天。
在蝉界,只有雄蝉才会鸣叫,它的发音器在腹肌部,像蒙上了一层鼓膜的大鼓,鼓膜受到振动而发出声音。由于鸣肌每秒能伸缩约1万次,盖板和鼓膜之间是空的,能起共鸣的作用,所以其鸣声特别响亮。
蝉能轮流利用各种不同的声调激昂高歌。雄蝉每天唱个不停,不管不顾,就是为了引诱雌蝉交配,但雄蝉却不能听见自己的美妙“歌声”。
雌蝉是“哑巴蝉”,它们的乐器构造不完全,不能发声,只能享受情郎的歌声。
在自然界里,蝉家族里的蟪蛄是最早登台的,蟪蛄体长约2厘米.全身黑褐色,鸣声尖而长,连续不断。
知了又叫蚱蝉、鸣蝉,在蝉的家族中个头最大,体长约4厘米,浑身漆黑发亮,鸣声粗犷而宏阔,高亢,响遏行云,像是男高音。
伏了蝉到夏至时才登台歌唱,“伏了、伏了”地连声不停,伏天刚到,它便迫不及待地告诉人们“伏了”。
寒蝉,体长约2.5厘米,头胸淡绿色,因它在深秋时节叫得欢,故又称秋蝉。寒蝉人秋才开始呜叫,它们的歌唱才是这场“蝉声系列音乐会”的压轴戏。不过它们的叫声只是简单的“嗞嗞嗞”。
蝉的生活方式较为奇特。夏天,蝉产卵后一周内即死去,卵经过一个月左右即孵化,孵化后若虫掉落到地面,自行掘洞钻入土中栖身。在土中,以刺吸式口器吸食树根汁液为生。它们要经过漫长的若虫期。老熟幼虫爬出洞穴后,慢慢爬上树干,然后自头胸处裂开。不久,成虫爬出蝉壳,经阳光的照射,翅膀舒展、干燥。羽化过程需1~3小时。成虫飞向丛林树冠,以其刺吸式口器刺入树木枝干吸食汁液。成虫性成熟后,雄虫开始鸣叫,吸引雌性进行交配。交配后雄虫死亡,雌虫产完卵后也相继死亡,从而完成其传宗接代的使命。
蝉的谱系不仅局限在自然界,我们还会想到那些蝉的意象群,有的是蝉本身,有的是与蝉联袂演出,比如垂柳、白杨,比如新蝉、金蝉、暮蝉、秋蝉、哀蝉、嘶蝉、鸣蝉、寒蝉、残蝉,比如乡心、月下等。蝉,常与羁旅、闲居、夕阳、秋露、孤独、家园连在一起,蝉声是一种氛围、场景、衬托,蝉声给人的恰恰是万籁俱寂的静,蝉的噪是辩证法,是另一种静。
“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这是王维的一句诗,出自《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雨气燕先觉,叶阴蝉遽知。”这是李商隐的一句诗,出自《送丰都李尉》。
相较于虞世南的“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还有骆宾王的“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的直白,我更喜欢王维和李商隐的蕴藉。我有时写书法,就常写这两首诗,给人的回味多,少了那种蝉噪。还喜欢书写山东乡贤辛弃疾的“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那是一种丰年的意境。多年前,在上饶,我曾去过辛弃疾的黄沙道,但不是夜里,也未听见鸣蝉。
我们了解王维的“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的赠诗,这是写在辋川的。这是在秋天的时候,写给他的小友秀才裴迪的,王维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忠实践行者,他的散文也有这特质,在他给裴迪的信中,王维笔下辋川的冬夜,乃至玄想春天的辋川,那都是一幅绝妙的山水图轴。
这诗和文,串在一起的,是听觉,是辋川,是友情。
王维在《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开笔就是“现在正是农历十二月的末尾,阳光很好”,王维的散文和他的诗一样,妙于裁剪,物在灵府,辋川的冬夜,是那么朦胧而清晰,处在真幻之间。地上玄灞、头上清月,两两相应,明暗互别;水光也,月光也,月在水上,水在月中,上下相合,月也水也?寒山远火,一冷一暖;寒犬深巷,吠声如豹,一动一静;而疏钟杵臼,出家与在家,出世与人世,心灵世界与人间烟火,天人相应。这个时候,他想到的是裴迪,携手同心,互相唱和,求其友声。
冬夜的犬吠和疏钟,是王维耳中的常客,就如秋天的暮蝉。
而蓝田辋川的春日呢,在王维的笔下,那种心设的幻影,更加斑斓。“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轻鲦出水,白鸥矫翼,露湿青皋,麦陇朝雊”,这六个四字句,直如《诗经》的辋川版。春草蓬勃,白鲦跃水,白鸥羽翅在空,野雉发情,麦陇鸣叫,草木染绿春山,露水滋润堤岸,这春山图与辋川冬夜图,给我们一种诗人澄怀味象,从自然美,进入美的自然之感。柳宗元是对的,如果兰亭不遇见王羲之,王羲之还是王羲之,兰亭还是兰亭。
王维的听觉十分发达,在这里,麦陇野雉的叫,是春天蓬勃的情欲,那种撕心裂肺也如秋天的暮蝉。
我们欣赏了辋川的冬春之美,现在要回到我们的主角蝉上来了。辋川的秋色如此,“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谖”,秋山经霜,其色渐深,其味愈浓,透出一种苍劲之气,秋山是静止的,但王维一个“转”字,就透出无边的意蕴,秋水是时间,寒山如智者,它们一动一静,有坐有卧,日夜不息。
“渡头馀落日,墟里上孤烟”——看那渡头,夕阳正缓缓下落,只剩一个火红的半圆;再看远处的村落,一缕炊烟袅袅升起,在天空画出优美的曲线。渡头、墟里,一水,一陆;落日、孤烟,一自然,一人事,一下一上,一点一线,但这些都是为了突出裴迪和他,“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这是王维和裴迪的日常。每到黄昏时候,凉风忽至,暑热散去,王维便伫立在柴门外,拄着手杖听蝉鸣,而裴迪呢,应和蝉的天籁之曲,醉态踉跄,狂歌如接舆,那时的王维,就是五柳先生的转世啊。
蝉是夏的象征,也是秋的终结。“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有了这两句诗,我们感觉辋川的这个秋天完整了,王维的这首诗也完整了。
暮蝉,日暮天晚,不是断肠人在天涯的那种伤感,而只是时间意义上的,不是荒村不是羁旅,不是日暮在外的旅人,也非送别,这里的日暮蝉声,是与苍翠的寒山、渡头的落日、墟里的炊烟和可爱的裴迪连在一起的,有点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手法。暮蝉,脱离了感伤,进入了一种温馨的审美意蕴。
我十分熟悉这种暮蝉嘶鸣的场景。童年时,从野地回来,肩头上是一粪箕子的草,这时,在村头的蝉声里,应和着的是谁家的娘在呼唤孩子的声音。那一声一声的呼唤和蝉声分割着天将暮的时刻,蝉声负责的是村头的槐树柳树榆树,娘的呼唤负责的是树下的揪心,村庄的蝉和娘比赛着,没有聒噪,而是另外的不可描述的声音。
寒犬深巷,吠声如豹。
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
这一文一诗,听觉传递得十分鲜明。无论犬吠,还是野雉的叫春,抑或暮蝉,它们是物象的存在,也是意象的审美。它是内容,是背景,是一种艺术符号,人们读后,感觉到的不再是物理的对人们心灵的叩问,而是艺术空间的拓展。是神韵是天籁,从某个角度来说,听觉意象比视觉意象更具画面感,更有想象补充的空间。犬也好,野雉也好,暮蝉也好,这三个意象都是时间的,特别是暮蝉,它是在催促吗?还是在抚慰?这自然界的回声,给我们的是一种生活的宁定和安详。
蝉声,是我们民族的审美意象,它从远古走来,成为夏天和秋天的标配,而且,它又是一个象征物。
王维是写秋蝉的物理形态,而李商隐写蝉,让人体会到秋蝉的象征意味。李商隐写蝉,是托物寓慨,以蝉的高洁,不与污秽为伍而自况,“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这蝉居高处声嘶力竭,不偷懒不耍滑,却难求一饱,尽管日夜不息地呜叫,却无人同情,唤不来大树的怜惜。难饱是因为不愿屈尊低就,胸怀大志却备受冷落,满腔怨怼的李商隐在看到“难饱”“欲断”的蝉时,自怜身世,四处飘零,如今家乡田园早已一片荒芜,还能归去吗?
写蝉写人,写人写蝉,钱钟书对此诗如老吏断狱,字字中的:“蝉饥而哀鸣,树则漠然无动,油然自绿也。树无情而人有情,遂起同感。蝉栖树上,却恝置(犹淡忘)之;蝉鸣非为‘我’发,‘我’却谓其‘相警’,是蝉于‘我’亦‘无情’,而‘我’与之为有情也。错综细腻。”
李商隐说蝉给自己警示,但正因为像蝉一样矜持、独善其身,才保持着一身“清”啊,这样的李商隐多么让人敬佩。但李商隐最终却还是陷入“费声”的绝望,大树是多么“无情”,蝉再怎么可劲嘶鸣也撼动不了树。撼山易,撼树尤难,这是蝉吗?这是李商隐吗?矜持的诗人,也想建功立业,人世做一番功名,但漂泊无定,家园荒芜,前没有进路,后没有退路,这该是多么丧啊。颓丧,号丧,恼丧,沮丧,悲丧,气丧。但又因为环境,李商隐只能拿蝉说事,还不敢明目张胆地表达,这也许就是李商隐朦胧诗朦胧的内在原因吧,欲言又止,欲说还休,不是语言的问题,是逼仄环境的问题。
“雨气燕先觉,叶荫蝉遽知”,对于这两句李商隐写蝉的诗,作家王蒙敏锐地感知,这还是外在的大环境问题。王蒙说:“体会了一下燕、蝉、身外的生命的感受,‘先觉’‘遽知’则仍然是且疑且惊,无定无力。‘先觉’固然觉了,仍然吉凶难卜,更不知‘先’以后的事会发生些什么;‘遽知’叶荫则更含有一种夏将尽晴日将尽的触目惊心的颤抖。”
这里的蝉,灵敏的感知,真的具备人的感知器官吗?这“且疑且惊,无定无力”的内在的心理感受,这“一种夏将尽晴日将尽的触目惊心的颤抖”,写的分明是特殊年代暴风雨来临前的王蒙啊。
也许是受李商隐的触动,王蒙也写过《咏蝉八首》,我最喜欢的是王蒙的这首:
想哭恁痛哭,要叫便欢呼。鸣止皆天籁,律节岂计谋?响翼生而就,高声唱便出。何劳糠稗妒,损肺伤肝无?
这是什么样的蝉啊。就如蝉中的自由人,无精神束缚,无外界压制,痛则大叫,怒则大骂,乐则大笑,了无羁绊,任意西东。听从自己的内心,按照自己的“律节”,鸣也好,止也好,都随天籁而出。
王蒙笔下的蝉,从“深文复周纳”,到“哀怨将哭绝”,到陷入各式各种人类陷阱,“或伸长竿粘,或掘土三尺。拔翅裂蝉体,涂炭成笑谑。玩赏掌中泣,人性可疑也!”
这些虫子何其不幸,王蒙说出蝉有四苦,这是从文化意义、象征意义上来说的——“蝉类苦其多,蝉身苦其弱,蝉寿苦其短,蝉声苦其烈”——苦多,身弱,寿短,且声烈,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画像呢,是断肠文,是断魂曲,是诔辞。
王蒙笔下的蝉,不是夏季的蝉,是悲秋模式的现代版:
昨日蝉鸣如海啸,今夕蟋蟀啼伤调。促织唧唧天渐清,盛夏未已已秋风。
但秋天也是收获的,令人沉思的,王维的暮蝉,给人的是另一种意义,是黄昏晚照,有一种回归家园的温馨。
三
我三楼书房的窗户外,有一楼人家种了枣树、椿树和柿子树,枝叶扫窗,往年树上的蝉鸣,是我沉浸在书房最好的陪伴。举首望蝉,相看不厌,耳闻蝉声,如沐春风。
在没有蝉声的书房,我寻找逝去的蝉声。那风雨寒蝉、衰柳寒蝉、薄暮寒蝉,给我心灵最大的触动。
寒蝉鸣叫的时候,往往是薄暮,是斜阳,是长亭晚,有时是潇潇雨后,那种诗人身上感到的既是自然界的寒凉,又有着内心的悲抑、哀凉和痛苦。那斜阳和长亭,给诗人提供了一种抒情的参照与空间。“病叶惊秋色,残蝉怕夕阳”,在他乡,在日落时分,身世飘零,家园何处?最不忍的是“蝉声未足秋风起,木叶俱鸣夜雨来”,这不是暮蝉,而是夜里引带风雨的蝉。
薄暮黄昏,在古人的时间意识里,那是生命迫近终了的时候。我们知道,生与死是一切艺术和哲学的思考的出发点。那个时候,人最易发出“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追问。“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从蓬勃升起的朝阳,到落日熔金的余晖,这是生命从壮美走向寂灭,从新生走向衰暮,如果这时,再配上蝉的“知了,知了”的声音,好像它已经预知了命运。
我以为,蝉鸣发出的“知了”一音,颇有禅宗的味道。“知了”是由“知”走向“了”,明白了世间的一切,走向解脱和放下。
这就有《红楼梦》中《好了歌》的味道了,跛足道人在《好了歌》中说出了权力地位、财富利益、美色欲望、后嗣延续这四个令世人执迷不悟的事,但最后呢?用草没了、眼闭了、人去了、谁见了来作答。跛足道人就是一只在《红楼梦》里的“知了”,他说:“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我这歌儿,便名《好了歌》。”
我喜欢松尾芭蕉的俳句《蝉鸣》,这是“知了”悟道后的力,直穿岩石。
遍布的寂静
蝉的叫声
穿透了石头
什么力在寂静后能穿透石头?是知了“知了”的力。大彻大悟,蝉鸣里,知晓了利禄、名誉、生死,然后抛弃,无欲则刚,那是穿透一切的利箭,即使是石头。
其实,古今对蝉最了解的,我以为非杨万里莫属,他的《听蝉八绝句》,是以使他高居“蝉的第一解人”。杨万里的绝句,第一首写在官家的忙碌事中,他偷得浮生半日的罅隙,在绿杨阴里听蝉,写下“道是江东官事冗,绿杨阴里听蝉声”。但这样的生活,不是王维的辋川别业,而是公干之余,一种偷来的快乐。
“一只初来报早秋,又添一只说新愁。两蝉对语双垂柳,知斗先休斗后休。”杨万里别具只眼的是他写了蝉的斗,在鸣叫中一争高低。“说露谈风有典章,咏秋吟复人宫商。蝉声无一些烦恼,自是愁人枉断肠。”蝉鸣是有规矩的,有音调的,可入宫商角徵羽。蝉是没有烦恼的,一些人觉得蝉声聒噪,那是因为心中的愁绪,“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觉得杨万里的这首绝句,就是一首咏蝉的禅诗。
在蝉的嘶鸣中,“罪过渠侬商略秋,从朝至暮不曾休”,这执着的蝉,朝朝暮暮“叫来叫去浑无事,叫到诗人白发生”。诗人在蝉声中老了,鬓边的白发是蝉一声一声唤来的,杨万里的这首诗有意思。“望帝啼春夜更多,不知蝉意却如何。还来入夜便无语,明日将诗理会他。”杨万里说蝉和杜鹃不一样,夜里是不啼鸣的。夜里等蝉鸣不得,“明日将诗理会他”。但蝉是会在夜里呜叫的,这在辛弃疾的笔下“清风半夜鸣蝉”和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里都有明证。
人往往是在孤独时遇到蝉的,人生的孤独一方面来源于人的忧患意识,另一方面则来源于世界的苦痛与人生的虚无。“人受意志的支配与奴役,他每时每刻地忙忙碌碌地试图寻找些什么,每一次寻找的结果,无不发现自己原是与空无同在,最终不能不承认这个世界的存在原是一个大悲剧,而世界的内容却全是痛苦。”面对着“知了,知了”的蝉鸣,人会想到什么?孤独的人生既然存在,它就不得不在世上存在,既然活着,他就不得在世上活着,人生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而评判人生幸福的指数,从来不是看欢愉的多少,而得从挣脱苦痛的程度来看。有人沉迷于山水,采菊东篱,白衣送酒,用醪糟来洗去胸中的淤积与块垒;但悲喜与胜负,都不过是人生的修饰,是人生短暂瞬息的呈现,随着时间的流逝,彩云易散琉璃脆,这一切都不坚牢,都终将归零,回归人生的常态孤独。
也许,好就是了,或者参透知了,会获得一种自我拯救的力量和启示。但这个结论,最终于我也是十分怀疑的。蝉呢,是一道无解的方程。
在中国的蝉声里,我还是能时时触碰到另一种蝉,这种蝉有着古代知识分子的高洁,不同流俗,但又命运不济,常常遭遇“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曹植在《蝉赋》说:“苦黄雀之作害兮,患螳螂之劲斧。冀飘翔而远托兮,毒蜘蛛之网罟。欲降身以卑窜兮,惧草虫之袭予。免众难而弗获兮,遥迁集乎宫宇。”蝉的处境十分凄惨,不仅有黄雀、螳螂,还有毒蜘蛛、草虫等众多的敌人,还有人的各种器具的捕捉、火烧、油炸,曹植笔下的蝉最后都避难避祸去了。但总有那种不识趣的蝉,一种呆蝉,一种如飞蛾扑火的蝉,一种悲壮的蝉,他们嘶叫着,说出自己的意见,有一种撞南墙的执着。
这种蝉在黑暗中走来,历经灾祸,遍体鳞伤,从身体到心灵。他们的境遇,也是危险的,在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链条里,他们时时是被伤害被侮辱的一群,他们以叫为武器,把看到的经历的表达出来,不发声,毋宁死,如果连叫都没有了,他们存世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蝉作为一种图腾,出现在我们的第一个朝代,那时我们的民族早早有了治水的大禹,有了城池,有了青铜,有了文明的炊烟,也有了玉佩的蝉给我们以神灵庇护。蝉嘶鸣着从《诗经》走到了唐诗宋词,走到了心上,和雷声、蛙声、鸟鸣一样,给我们以天籁,给我们以季节的提醒。
我在这些历史和典籍里涵养,渐渐也培养起了敏感的耳朵,我出生在中原腹地的农村,自小就侧身蝉的呜叫里,只是到了大学毕业,工作之后,才有了听蝉的兴致。
早晨的蝉鸣,有了一夜露水的滋养,从黑暗中醒来,是一种新生,在太阳的鼓舞下,那是一种欣兴的心态吧。
午后的蝉,是热烈的,如人之壮年。黄昏再听蝉,便有了伤感,也有了清静。若是夜半醒来,还有蝉的陪伴,那就是天籁了。
四
“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
在中国的蝉声里,这两句诗,是最出名的,曾经在一个夏日,我和朋友去一个叫皇庵的小镇的河堤游玩,那是正午,我们走上大堤白杨林的时候,突然蝉都屏住了呼吸,没有一丝声响,陷入巨大的寂静。
正是三伏天,通向大堤的小路,好像被热烫得有了弯曲、回旋的线条,干热的空气灼身,脑袋和眼睛都有了幻觉,原野是着火的,小路上的泥块是烫的,青草都像蒸了八成熟。
我们选了一个树荫坐下的一刹,不知哪个心急的蝉憋不住气,开始试唱,一下子引爆了那千蝉万蝉的齐鸣,蝉声鼎沸,这突如其来的蝉声袭击,吓了我们一跳。接着那河的两岸,那大堤上,那白杨林里,响彻着更多更大的蝉声。
这是在文学课堂上才有的蝉声,“蝉噪林逾静”,那些课室里的男女的窃窃私语没有了,咳嗽声没有了,书写声没有了,大家好像一下被文学洗了耳朵,唤醒了心灵,好像是第一次听到蝉声。
这个时候,大地的蝉鸣,才让我实实在在感到夏天来了,不只是热的空气,而是这蝉声,我真不知,夏天来了,是这个样子。那空调房里、电风扇下的夏,都是打折的不真实的夏。
我想到了我的童年,我们用长长的高粱秆去捉知了,顶端有一个如羽毛球状的空心的张着口的秫秸笼。我们故乡把蝉叫“爬叉”,它们脱壳后,我们叫“嘟了”。而知了是我们到了学堂后才知道的。
你能想到吗,放学后,那是正午,太阳越热,知了叫得越响。几个伙伴从坑塘钻出,也顾不得回家吃饭,把书包随意一扔,就去捉知了。有时在树下,有时爬到树上,把高粱秆举起,往树杈的叫声(扌+享)去。“逮住了,逮住了!”有人呼喊,然后从那个秫秸笼里,把知了拿出,装到火柴盒里。
到了下午,那装在火柴盒里的知了被带到教室,有时在老师讲课的时候,有时在朗读的时候,几乎每个桌子底下的火柴盒里的知了,都会一下子冒出声,那知了的叫就是教室里的弦歌,是书声。老师说过,古代真有个书生,变成了知了,在大树上朗读《诗经》《楚辞》。
我却觉得,那有着轻纱般的薄翼的知了,一定是从闺房小姐那里走出的,那薄翼多像小姐的裙子。我对老师说,那知了,也可能是祝英台那样的女生变的。
和朋友坐在河堤上,我说有祝英台那样的蝉,她笑了,那你是梁山伯吧,是个闷葫芦的蝉,必须是在大家的鼓励甚至逼迫下,才可以发出鸣声吧。
蝉的叫声,是有区别的,叫声频谱不同,它们的叫声在100到130分贝。就如人种有黑的白的黄的,知了也有很多种类,但都被简称为知了;它们的叫,也有普通鸣叫、求偶的叫、交配的叫、竞争的叫、召集的叫和哀鸣等许多种。我们在河堤上,就听到了一场露天的蝉鸣的交响乐。
啊,一条蛇!朋友抓住我的手,这突如其来的惊叫,把蛇吓走,也把知了的叫,吓住了。就如我们刚踏入河堤的时候一样,那时我们惊扰了蝉鸣的世界,那是脚步,这是惊叫。但这些蝉是不甘的,它们觉得我们是闯入者,是异类,我觉出来它们的愤怒与叫喊,先是“出去,请出去”,接着看我们没有动静,就大呼大叫,是集体主义的抗议。多年后,我读到诗人雷平阳的《集体主义的虫叫》,一下子遇到了知音,他写了一个事件,是一次旅居偶遇虫声的事件,他写的是对自然的礼赞,是描绘一场大自然里的虫声的宏大与稠密。
那些虫子潜伏在无限辽阔的四周,全部“努力张大的嘴,眼睛圆睁,胸怀起伏”,多形象啊,胸怀起伏,那是愤怒,眼睛圆睁,是更大愤怒的表现。“叫,是大叫,恶狠狠地叫,叫声里/翻飞着带出的心肝和肺。”透过这些诗句,我们可以想象那些虫子的嘶吼和呐喊,不吼出“心肝与肺”不足以表达它们对自由与生命的向往。雷平阳忍不住走出门外去寻找声源,“黑黝黝的森林、夜幕/都由叫声组成”,最后雷平阳悟出:虫子们之所以叫,是因为“森林/太大,太黑”;它们叫,是为了“明确自己的身份”“传达自己所在位置”。
是啊,要想在众声喧哗中找到自己,那你就必须声嘶力竭、不遗余力地表达,争先恐后、竭尽所能地争取。
在河堤上听到这些集体主义的蝉鸣,我可以想象它们,那些荷尔蒙过剩的雄蝉敛翅站在树端,好像置身追光灯下,它们必须拿出自己最光彩的嗓音,把美声的唱法、民族的唱法、民谣的唱法,摇滚的、布鲁斯的,一切能引起雌蝉青睐的,都一一摆上舞台,它们说的是知心话,是爱慕语,是开窍的梁山伯对祝英台的告白,是独唱。它们循着自然的旋律,听从内心的召唤。我想,如果到了夜间呢,这些雄性的哥们儿,应该来些小夜曲,从金戈铁马转换到小桥流水、深巷杏花。但不管怎样,来自生命的歌谣,是令人尊重的。
宋人陶谷在《清异录》中记载:“唐世京城游手,夏月采蝉货之。唱曰:‘只卖青林乐。’妇妾小儿争买,以笼悬窗户间,亦有验其声长短为胜负者,谓之‘仙虫社’。”
唐代的人多么诗意,多么向往天籁,就如现在中原腹地我老家,夏天人们会挑着很多的装在笼子里的蝈蝈,那也是夏秋的虫子,挂在家里,一直可以听到初冬。
唐代的青林乐,就是人们捉到的蝉,如我童年时候,放在火柴盒里,带到教室里的知了。
蝉从远古到我这次再没听到蝉声的时段里,一直温暖着我们的历史,它们说着“知道了知道了”,是告诉人们,人所做的一切它们都知道了,它们看到了人间的苦难,它们的鸣叫里有悲悯。它们说“知道了”,是在安慰我们吗?
如今中原腹地,再也没有了蝉声,这个失落给我一种担忧:这是一种文化的消失,还是文化的重建与修复,等待着另一种涅槃呢?
我不知该怎样表达这蝉声的落幕,这是捕捉和杀戮吗?它们已难觅踪迹,它们连挽歌也没有留下,它们只是收敛在一册册的典籍里。我们是应该向历史鞠躬道歉呢,还是向这些曾鸣叫的虫子说声对不起呢?我们向哪个方向鞠躬呢?
向着杀戮吗?向着那些饕餮之徒吗?
无边的灼热的夏。无边的萧瑟的秋。没有了蝉声陪伴的历史,我们只能默默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