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骚扰电话装上“永动机”
2024-12-04张宏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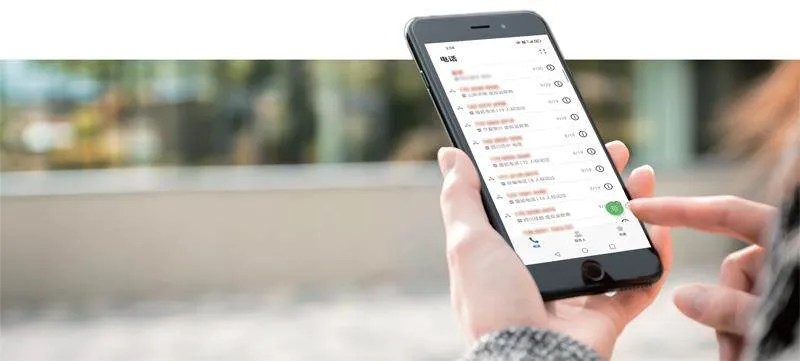
“你怎么才接电话啊?!我是XX公司的客服顾问,您有一张优惠券再不用就要过期啦!”
电话那一头,对方正用“AI(人工智能)外呼电推”一顿“输出”——全天候不间断呼叫系统、防拉黑的技术加持、对你的情绪无动于衷——你已经对“狂轰滥炸”式的营销忍无可忍,电话这一头尽是憋屈和无奈……
最近一段时间,多名读者向记者反映,骚扰电话的侵袭愈发频繁,其“阴霾”在日常生活中依旧存在。事关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的“攻防战”进入新一个阶段,骚扰电话就像被装上了一台“永动机”,这与电话销售行业“AI利器”的异军突起不无关系。在此暂且将对技术持何种态度的讨论搁置一旁,我们应当看到,“技术中性论”的某些观点或许可以延伸出更多对操纵者意图和行为、营销乱象深层次原因的思考。
降本增效的“新宠”
高效率、低成本的AI语音应用,成为电话销售行业的“新宠”。
记者了解到,就在2024年8月,海外专注于企业级AI电话服务的“Bland AI”宣布完成1600万美元的A轮融资。
新加坡某投资机构副总裁陈沛告诉记者,目前“AI外呼电推”在海外是较受关注的领域。其实,不能将电话推销和电话骚扰等同起来。值得一提的是,“Bland AI”是将AI语音应用和企业知识库结合的智能电话平台,主要是面向已经登记联系方式的、对相关内容感兴趣的客户开展电话销售。AI的对话反应或将逐步与人类的自然对话反应接近,也能按要求提供企业相关的知识解答。
AI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电话销售行业也不例外。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管理学院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企业导师支培元向记者表示,自动化、规模化实现了成本控制与效率提升的双重突破。“AI外呼电推”在处理大批量标准化任务、基础事务方面表现出色。同时,其在个性化交互设计、即时响应能力及大数据分析的支持等方面,展现出巨大的潜能。
技术的应用难以避免地伴随着一定的局限性。在不少领域内的专家看来,现阶段“AI外呼电推”缺乏人类的情感理解和判断能力,过度机械化带来的疏离感较为明显,在模拟人性化交流方面可能无法处理复杂的情感问题,缺乏对用户体验的深切关注,难以达到传统人工客服的细腻与灵活。在采访中,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副秘书长袁帅则提出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方面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问题,这同样值得关注。
交谈间,人工智能专家郭涛对过度依赖AI进行营销流露出些许担忧,“这将会对企业的营销策略和客户关系管理产生影响,或使企业过于注重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的品牌声誉建设、客户关系的建立与维护”。此种担忧不无道理,或说已经有所验证——回到文章的开头,便是新兴业务模式背后的骚扰电话问题。个别企业为了快速获得市场反应,不惜采取激进甚至非法手段。
外呼电推频繁侵扰
据国内多家媒体报道,2024年下半年,上海有部分市民接到播放AI语音的种植牙骚扰电话。据投诉人反映,种植牙口腔诊所的骚扰电话大约以两三天一个的频率打来,但也有些市民称,他们每天都能收到。需要重视的是,不管是明确表示没有需求,还是利用手机系统拉黑阻拦,都挡不住骚扰电话不断打来。该地市民姜先生称,骚扰电话所用的号码,大部分是“021”开头的座机号,偶尔也会出现“165”等开头的虚拟运营商手机号。每次都不一样,拦截难度较大。
有媒体根据对多家口腔诊所的走访,顺藤摸瓜找到第三方“互联网营销”公司。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此类服务在行业内被称为“前置AI”,即由电脑系统自动外拨电话,拨通后先播放一段AI语音,若检测到人声应答,则会由人工客服跟进。一旦“挖掘”出有需求的市民,上述信息会以“每条100元”的价格出售给合作的口腔诊所。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频繁且未经授权的“AI外呼电推”不仅侵犯了个人的生活宁静,严重的还可能触及隐私保护的红线。天津美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丁鹏曾撰文称,包括电话号码在内的个人信息是有其法律意义并受法律调整和保护的;我国法律规定了个人信息的使用规则,即应该如何使用和不能如何使用。《民法典》第1035条规定,“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并规定“处理个人信息的,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不得过度处理”。相应地,个人信息的所有者享有其个人信息被合法使用的权利。同时,《民法典》第1033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属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
记者梳理发现,除《民法典》外,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电信条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等也有着相关规定。不过,面对新型骚扰电话形式,技术发展的速度可能会超越现行法律的适应能力,保持法律规制与科技创新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同时在规制手段、监管力度等方面仍然有待完善和加大。
此外,对于“AI外呼电推”引发的相关营销乱象,支培元认为,除了反映了个别企业对短期业绩效益的盲目追求之外,还暴露出行业内缺乏有效自律机制与统一伦理标准的问题,导致技术的更新迭代未能与科技伦理的要求同步前行。
显然,在“AI外呼电推”所带来的经济激励面前,企业面临着如何在追求商业成功与遵守法律法规、遵循科技伦理、承担社会责任等之间寻得恰当平衡的关键课题。财经作家、营销咨询行业人士高承远认为,在利用“AI外呼电推”追求效益的同时,也宜适当控制呼叫频率、精准定位目标客户、提供明确健全的退出(退订)机制等,以减少对消费者的骚扰。高泽龙则建议,相关企业宜设立明确的道德准则,并持续监控和评估AI系统的表现,确保系统符合相应的服务质量标准,并通过动态调整减少负面影响。
个人信息保护的追问
再进一步溯源,骚扰电话的产生与个人信息的泄露密切相关。那么,个人信息是怎么被泄露出去的?信息泄露的发生率非常高、渠道非常复杂。据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研究员王永建的归纳总结,移动应用程序的权限滥用、不安全的网络连接、社交媒体的不当使用、网络钓鱼和欺诈等,都可能给不法分子窃取个人信息留下可乘之隙。
除了日常防范、行业自律、政府监管等,筑牢个人信息的“安全堤”,离不开更为有力的司法保护。以作为法治的重要组织部分的检察机关为例,2024年2月至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检察机关部署开展“检护民生”专项行动,相关实施方案明确“加大对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司法保护力度”的要求。
要知道,房产、快递、电信、保险、医疗、教育、金融、互联网等行业,属于处理大规模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业,这些行业一旦出现“内鬼”,也会使大量公民个人信息遭到泄露。在记者所在的上海市,当地检察机关依法严惩相关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并加强综合履职,通过民事公益诉讼维护公共利益,还积极融入社会治理,制发检察建议推动行业治理。
此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在办理诈骗案件时,发现有“高利贷中介”团伙在犯罪链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第一时间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并敏锐察觉到该案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可能存在侵害公共利益的情况,及时通过“四大检察”融合发展工作办公室将线索移送该院公益检察部门同步审查。经刑事检察与公益检察融合办案,检察机关以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为由对百余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最终促成“赔偿+罚款+判刑”。
记者还注意到,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诉H科技有限公司、韩某某等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曾入选最高检“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这一案例的特别之处在于,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用户利用互联网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网络运营者未依法履行其社会管理职责的情形,检察机关在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时,并未囿于刑事被告人范围,也可以依法追加其为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同时,在该案中,针对网络侵害的跨地域性等特点,检察机关协同相关行政机关治理侵害个人信息行为,有利于互联网领域损害公益问题的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彰显出公益诉讼的独特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