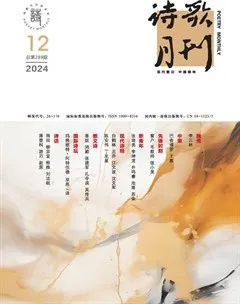我的 《诗歌报》 编年小史
2024-12-03游刃
《诗歌月刊》编辑辗转联系上我,约我写一点回忆自己与《诗歌报》之旧事的文字。印象中塞巴德《奥斯特里茨》里的主人公,为了找到一个族人给一段历史作证,也是一环接一环地找到他所要找的人的。我和《奥斯特里茨》里的那个族人一样,都是庸常而湮于尘埃的人,历史场景里雷霆海啸、飓风烈日演变不息,而我们都不过是倏忽而过的蜉蝣与一粟。
上了年纪的人都爱回忆往事,偏偏记忆力大大衰退,这真是乖谬尴尬。
我最早接触《诗歌报》是在大学时。1986年,它与《深圳青年报》联办的“86大展”轰动一时,但我也只是从隔壁宿舍喜欢诗歌的同学那里看到过它。不过,那时我多猫在图书馆里嗜读文学名著,对报纸杂志了无兴趣,况且大学时,我的诗作主要发表在《星星》《福建文学》上,所以对《诗歌报》所知甚少。
1987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老家县城的柘荣县第一中学任教。次年,我才订阅了《诗歌报》。从保存至今的那张获奖证书来看,1988年6月,我的一首题为《过去》的诗,获得《诗歌报》举办的首届爱情诗大奖赛三等奖,并被收入获奖作品集《禁果》一书。其时,我并没有真正谈过什么恋爱,对那首爱情诗是怎么生成的已经没什么印象,那完全是人生诸多碰运气中碰到的一次好运罢了。这是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诗歌报》上。
刚到学校工作,教学任务重,住宿条件差,我几乎没写什么诗。过了两年,学校分给我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课余终于能在自己的天地里胡思乱想,写的诗也多些。
1990年,《饮风的人》(二首)发表于《诗歌报月刊》第9期的“花朵的力量”短诗专辑上。这个专辑的诗歌,编辑都会署上作者所属的工作单位名称。我记得在“游刃”的笔名前,署的是“福建柘荣一中”。在那个如今看来通讯相对落后、只能从杂志报纸上获取时人信息的年代,我后来听说,福建省内的一些诗人,看到我这个单位名称后,都有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文学兴奋感,似乎这么一个偏僻的小小山区县份,竟然还有个叫游刃的同道,诗的神光照进每个角落,真实不虚。
刘克庄说:“暮年字字费冥搜,少作如山弃不收。”我的少作很少,亦无甚价值,便多废弃。感谢《诗歌月刊》编辑不辞辛劳,从《诗歌报》的资料库里将我发表的那些陈年旧作拍照发给我。发表在《诗歌报月刊》上的这两首诗,除了这首《饮风的人》外,另一首是《怀人》。即便年湮月远,我还能记得《饮风的人》里“饮风的人,烟波上的瓷砵/在斜阳里换了衣裳”这样半文半白、半通不通的造作之句,可见这次发表对我影响之深。
我也因这两首署了我工作单位的诗作在《诗歌报月刊》上发表,而结识了省内外的一些诗人。所谓结识,不过是通信而已。那时,诗人间的联系大多都靠写信。我们学校的门卫起初不知道那些地址上写着“柘荣一中”、收信人叫“游刃”的人的信件是写给谁的,后来传开了,知道是我,有些同事便不叫我本名,而以游刃称呼我,最后直呼我“诗人”以代本名。
我和外地诗人之间的通信,基本上以互寄诗作为主,信件你来我往,也只聊诗,多避俗事。大约就是在那时,闽东、福州、莆田等地的青年诗人们,也因《诗歌报月刊》上那两首诗,与我建立了通信联系。闽东诗人汤养宗我也是在那时认识的,他年长于我,写诗更是早于我,对我颇为关注,书信往来亦颇频繁。读高中时,在父亲工作的公社办公楼里,我得到一期宁德地区文化局主办的刊物《采贝》,我在那期《采贝》上读到汤养宗在海军服役时写的一组海洋题材的诗,感觉很新鲜。虽然当时我一点也没有写诗的意愿,读过后内心仍受震动。几十年白驹过隙,记忆里至今犹残存着这组诗中的两句:“母亲带血的嘱咐是我胸前的扣子,我航过的□□(这两字我想不起来)吐了又断。”
《诗歌报月刊》1991年第4期,发表了我的两首诗,一首题为《枫桥:对一个地方的想望》,另一首是《为苏小小而作》。这次,我的工作单位名称没有失误,由之前的“拓荣”改正为“柘荣”。这两首诗作分别是对张继和李贺的经典之作的现代改写。韦庄诗云:“长年方悟少年非,人道新诗胜旧诗。”这些旧作,多不堪细读,只有在如黑白默片、怀旧老照片那样带着被时光耗尽的枯涩凝视里,才恍然现出与诗中的抒情意味暗合的如梦光影。
这一年的《诗歌报月刊》第9期,我的诗歌评论作品《玻璃工厂:纯粹的语言平面世界》在“创世纪:青年诗人谈诗”栏目上发表。我记得那一期的《诗歌报月刊》发有三篇评论文章,第一篇是陈仲义的,我的居中,末篇是四川诗人杨远宏的。这是我第一次发表诗评,在这篇谈到诗歌语言问题的所谓评论里,曾大段引用了高月明、陈先发等诸安徽诗人当年在《诗歌报》上发表过的诗句。此文特以安徽诗人的诗作为例,自有感激之情在,亦不乏讨好《诗歌报》的稚拙的世故。
1992年春,由蔡其矫老师推荐,我到鲁迅文学院脱产学习了半年。1992年到1993年,我与东吾合作,先后在《诗歌报月刊》1992年第2期封三发表《位置》、第4期封三发表《飞翔》,1993年第11期发表《显现》、第12期封三发表《侧影》等一些“诗画配”的作品。
“诗画配”这种形式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印象中,还是在《诗歌报》时,就有曲光辉的画作与一些诗作的配合,不时出现。1991年底,我收到东吾的黑白画作,他让我配诗,投给《诗歌报月刊》。东吾曾是福建侨兴轻工学校的学生,之前,我的同学、好友林俞男毕业后到那所学校任教,我去过那所学校几次,东吾也写诗,就此结识。东吾毕业后留校任教,国画、书法笔耕勤奋,不时寄些黑白抽象画作来给我。我兴致来时就写几行,一并寄给《诗歌报月刊》。可能我们合作发表的作品,多在封三这个显眼位置,所以,直到前两年遇到一位北漂的诗人时,她还提及我和东吾当年的“诗画配”。不过,那时,就有朋友直言劝我少做这种“配合”。
1993年《诗歌报月刊》第1期,发表了我的《星光下的马车》(二首)。《星光下的马车》是我现在读来还有点喜欢的作品,诗里那个穿过星图颠倒的夜晚的身影,虽然摇晃歪斜、单薄扁平,我还是敝帚自珍。
1994年,女儿游忆出生。《枫桥:对一个地方的想往》一诗被收入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诗歌报〉十年精华》一书。这年的《诗歌报月刊》第7期,我还发表了一次“诗画配”,题为《月光》,诗是我写的,但画的作者署名为陈晓燕。我不记得这个陈晓燕是不是东吾的某个学生。在这首《月光》的开头,我写道:“从前走失的已经回来,漫游过的地方汇往海上/那些道路不过是流水一脉,没有中心的花园/依靠了优美得以持续,不管手握了纸张一样的身子。”这几行诗句,写的仿佛就是现在正在回忆《诗歌报》往事的自己。
1997年,我的《木偶戏》(三首)、《工匠》分别在《诗歌报月刊》第8期、第10期发表。这首《工匠》原刊于北漂的山东莒县诗人于贞志办的民刊《转折》上,第10期的“民间社团辑”转载。比我年轻许多的诗人于贞志已经不在人世多年,我们通过《诗歌报》相识的那段友情不会消亡,他在诗中永生。
1998年,《小县城的美人》《泥瓦匠》分别在《诗歌报月刊》第8期、第10期发表。
在《诗歌报月刊》发表作品的那些年,我完全靠信件维系着与《诗歌报月刊》之间最为单纯的关系:我投出稿件,发表后编辑部寄来样刊和稿费单。我和那些发表过我诗作的编辑们,没有任何非业务上的交流。但我记得刊物上在每件作品后面所署的一些名字:雪鹤、黎阳、城父、蓝角……我至今仍不知道这些神秘莫测的名字是与刊物编辑部工作人员名单上的哪个名字相对应。这些被时空、文字与纸页遮蔽住的《诗歌报》编辑们,有着另一个遥远星系所共有的波频,时隔数十年之后,我还能感受到那超越肉身所限、晦暗不明却又永续无断的存在。
直到《诗歌报月刊》已经更名为《诗歌月刊》的2000年后,偶尔还有编辑从民刊中选一两首我的诗发在“民刊专号”上。那是一种自己不过是路过某个村子借宿一晚,过了很多年后,村里还有人念及自己名字的感觉。
查尔斯·西米奇在一首题为《秘密历史》的诗中写到:作为诗人,自己是墙上的蜘蛛、照进屋内的灯光、放在床边的鞋子等等这些物什卑微的记录者;也正因为自己是它们的卑微记录者,那些遗落的珍珠耳环、无声飘落的雪花、消逝的夜晚,还会回返。我并未真切体会过西米奇所说的诗歌的这种神秘力量,在诗歌历史的泥炭层里,作为一个卑微得不值一提的记录者以及那些卑微得不值一提的诗,竟还能和《诗歌报》这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真是非常幸运。倚赖着《诗歌报》天女散花、仙佛罗汉般展列的四十年灿烂历史,我试着构建自己在《诗歌报》发表作品的个人编年史。这是我一个人的诗歌秘密历史,承载着一小片属于我内心幽微隽永、不轻易外道的历史秘密。
游刃,1965年生,现居福州。著有随笔集《一间无尽的舞厅》、诗集《一直生活在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