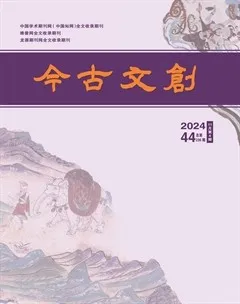荆楚民族流变研究
2024-11-22王琴周亚琪马安澜
【摘要】荆楚民族是由楚公族、三苗、越人构成的多元民族共同体。最初各民族以自己的方式独立发展,后在国家扩张、地域迁移等因素影响下,各民族开始交往融合,荆楚民族一体化也就此开始。荆楚民族一体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三个民族内部发展演变与民族间的交流融合并行不悖。楚公族可确认的先祖追溯到祝融部落;三苗的发展、演变形态在与中原地区的交战中被塑造;越人的族群分为勾吴、于越。楚公族、三苗、越人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以战争、迁徙、人才往来等方式交流融合,并与中原关联密切。楚公族的尊火崇凤理念建构了楚文化的主要形态;三苗的信巫好祀让楚文化染上了神秘瑰丽的色彩;越人的断发文身给楚文化带来了野性质朴元素。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各民族的往来中交融,共同决定着楚文化的面貌。
【关键词】荆楚民族;楚公族;越人;三苗;楚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4-0072-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4.018
对于楚人的渊源,学界有北来说、东来说、西来说、土著说等说法[1]。不同的学说对楚人的先祖、迁徙路线、民族构成有不同的认定。因为文献繁多,缺乏充分的出土文物,问题的答案莫衷一是。目前学界的楚文化研究集中在对楚文化的渊源、内容、特质、应用的研究;对楚族源的探究;对楚民族形成的研究;对出土文物的研究等方面。其中,对于楚族源以及楚民族构成的研究学界持不同的说法,但多各自关注楚王室、越人、三苗这几个民族的内部发展演变状况,缺少对楚民族的构成的宏观把握。且大多数研究对先秦时期楚国的民族构成与流变未充分重视。人是文化创造的主体,对荆楚民族流变的研究有助于回到人本身,深化对楚文化创造主体的认知,从而更好地理解楚文化特质。
一、荆楚民族结构
荆楚民族是先秦时期聚居生活在南方地区的主要民族,该民族的文化特质与个性既独立不凡又与中原文化联系密切。针对先秦时期的南方民族而言,本文的“荆楚民族”是一个总结性的概念,又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内部经历了多个民族的流变融合。
楚国是先秦时期南方的大国,以楚国疆域为网可以基本确定荆楚民族的活动范围。楚国立国时期以丹阳为活动据点,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相继灭陈、蔡,后来又灭越,国力极为鼎盛。《战国策·楚策一》记载:“楚,天下之强国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2]在地理格局上本文以此地域为本展开对荆楚民族的研究梳理。
楚民族由三部分构成:楚公族、越人与三苗。其中,楚公族是楚国的主体民族。
《史记·楚世家》详尽记述了楚人的世系:“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祖曰昆吾……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3]按照《史记》的记载,楚世系如下:黄帝→昌意→高阳→称→卷章→重黎(祝融)→吴回→陆终→季连→附沮→穴熊→鬻熊→熊丽。
实际上,黄帝、昌意、高阳是楚人的附会,非其先祖。清华简《楚居》所载楚人先祖中并未提及黄帝、昌意。安大简楚史类简中有关楚国世系的记载最早追溯到颛顼,同样没有提及黄帝、昌意。在《大戴礼记·帝系》《五帝本纪》所载的帝王世系中,帝喾、颛顼等都为黄帝子孙。民国以来,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学者对这些帝王传说及有关文献进行了大量的考辨和推翻工作,他们认为《帝繋》《史记》所载黄帝一元、三代同源的“一统的世系”的构建,是战国以来民族趋于一统的产物[4]。故而以此世系为依据言黄帝、昌意为楚人先祖并不可靠。此说是楚人在为自己统治的扩张寻找依据,事实上他们并非是楚人传说中的固有先祖。
高阳、颛顼并非同一人。“高阳”最早见于《左传·文公十八年》:“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颛顼氏有不才子……”[7]《左传》作者将高阳与颛顼分述,他们是形象、族类不同的两位古帝。屈原在《离骚》中自叙身世时也并未明确说高阳即颛顼。张正明先生考证后认为:“高阳为夏人所尊崇,是炎帝的古称。”[34]炎帝作为传说中的太阳神,符合楚人对红色、太阳的崇尚,因此被楚人视为始祖。颛顼因对原始社会的巨大贡献而被推崇,地位甚高[8]。战国时代社会统一局势日显,在华夏正统观念支配下华夏部落联盟的重要首领都被说成是黄帝后裔,颛顼被说成是黄帝之孙,祝融也被说成是颛顼后裔。《大戴礼记·帝系》云:“颛顼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谓之女禄,氏产老童。”[10]《山海经·大荒西经》载:“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13]说颛顼是楚人的血亲始祖是一种附会。故高阳、颛顼都是楚人追认的始祖,与楚人无血缘关联。
楚公族可追溯的确认的具有血缘关系的始祖是祝融。这点从文献和考古发现都可佐证。《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记载,夔子因为不祭祀祝融而受到楚人的非难[7]。可见在楚人认知中,祝融为楚国的先祖。根据《国语·郑语》中的记载可推出楚公族为祝融的后裔。《史记·楚世家》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个说法。包山楚简的卜辞记载:“举祷楚先老僮、祝融、鬻熊各一牂”[14],也可印证。
吴回第六子季连是楚人的直接祖先。祝融部落在吴回之后发生了裂变,《大戴礼记·帝系》曰:“老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谓之高蜗氏,产重黎及吴回。吴回氏产陆,谓之女娘终。陆终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氏,产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启其左胁,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为昆吾,其二曰惠连……是为曹姓,其六曰季连……季连者,楚氏也。”[10]这是关于“陆终六子”的记载,此记载与《史记·楚世家》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可见,季连为楚公族的直接祖先。
《诗经·商颂·长发》曰:“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11]商攻夏,中原地区斗争激烈,商的威慑日益增加,季连后裔南迁。后来鬻熊归顺周文王,《史记·楚世家》载:“鬻熊,文王之师也……”[3]张正明先生辩证说此处的“师”为“火师”[12]。鬻熊的后代熊绎成为楚国的开国君主[3]。据《史记·楚世家》记载,熊绎被周成王封于楚蛮,给予子男之田的爵位,定都在丹阳[3]。熊绎是周初重要的异姓诸侯,与周之同姓诸侯共事周成王。自鬻熊以后,楚君位已由熊氏所把持,出现了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
越人素有“百越”之称,“百越”是中原对南方族群部落的泛称。越人野性质朴,古越族的风俗习尚中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断发文身,裸以为饰”[7]。荆楚大地上拥有独立政权的越人族群可分为两支:太伯建立的“勾吴”,即后来周章所立的吴国;部落“于越”,即后来的越国。
《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3]出身周王室的太伯仲雍奔荆,入乡随俗并获得当地认可,与当地人共居并建立族群“勾吴”。勾吴族有两大构成部分:一是由中原周王室太伯、仲雍及其后代构成的勾吴族王室;二是由原本定居在荆地的越人土著。越人土著的文化生命力影响了由中原而来的勾吴族王室,吴太伯选择“断发文身”融入当地,王室的习俗也在当地土著影响下同化。周章时期周王正式封吴,“勾吴越人”组建统一国家,寿梦时期吴国益强,开始称王。
“于越越人”是另一支生活在长江下游地区的族群。《公羊传·定公五年》称:“于越入吴。于越者何?越者何?于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16]于越居于长江口东南,所立之国为越国。根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越人在身体上纹上花纹,将头发剪断,开辟荒地建立城邑。[3]越国“文身断发”的习俗可印证其族群归属为越族。
于越一族的发展谱系较勾吴相比更为模糊,所存史料主要见于《越绝书》与《吴越春秋》,史料对于越越人早期发展传承状况记载不详,但能明确直到允常、勾践在位时期,越国才开始强大称王。
勾吴越人和于越越人虽都成立了各自独立的政权,也是多年宿敌,但两支越人的生存环境极度相似。《越绝书·越绝外传记》云:“吴越二邦,同气共俗。”[17]吴越自然条件相似又相邻,交往便利,因而孕育出相近的风俗文化。
“昔,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溪之阳,卢、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2]对三苗地望的记载以《战国策·魏策》最为翔实。三苗所居的大致方位,应为今湖北、湖南、江西西部的江汉平原区域。《礼记·王制》对南方民族的称呼有所记载,后以此演变,对南方民族的称呼中带有贬义色彩[25]。后来也称南方民族为“苗”“苗民”,亦称“三苗国”。三苗的发展流变与其迁徙密不可分。
第一个阶段是黄帝至颛顼时期,时间跨度长达千年。黄帝取得阪泉之战的胜利后,与九黎集团展开了涿鹿之战[23]。生活于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之间的平原地带的九黎集团,在蚩尤带领与东下的炎黄部落对抗后惨败,离开东部平原向西南迁入长江中游一带。
第二个阶段是尧舜禹时期。九黎部族的一部分迁移至长江中下游,同原住民一同建立“三苗国”[27]。在此时期“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23],舜派禹出征三苗,迫使“有苗氏来朝”[33],但有苗氏休养后继续与华夏族团对峙,舜“南巡狩”[3],亲征三苗族团。苗族先民再次被迫迁徙,史称“窜三苗于三危”“放驩兜于崇山”[3],即一部分被赶到甘肃、青海积石山一带,一部分被赶到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的崇山峻岭之中,一部分留在“三苗”故地。在夏人与三苗发生冲突时,祝融部落,也即楚人,处于夏人与三苗之间,起到了文化交流的媒介作用。
第三阶段是华夏族团与三苗族团冲突的结束。华夏族团对三苗族团的征讨活动从未间断,并在夏商时期对该地区进行了占领和直接统治,这标志着三苗势力的消逝。在夏朝以后,三苗游走于楚人周围,并与楚公族在大大小小的战争中相互影响,最终三苗成为楚族的一部分。
一言以蔽之,荆楚民族由三大民族构成,其中楚公族为主体民族,在荆楚民族和荆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了最深刻的烙印;而三苗与越族则为荆楚民族的次要民族,他们的文化同样璀璨,但由于他们所领导政权的消亡,其族人与文化最终只能融于楚公族领导的楚国。而楚人、越人、三苗三个民族共同熔铸成荆楚民族,则是民族一体化的结果。
二、荆楚民族一体化
严庆先生在《解读“整合”与“民族整合”》中认为:“民族一体化是指不同民族之间通过战争、通婚、人才往来、迁徙等方式进行交流、融合最终实现多民族统一的过程和结果。”[28]荆楚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一体化进程值得仔细研究,下面主要对荆楚民族一体化历程中的相关问题进行探究。
楚人与三苗的一体化进程与地域密切相关。林惠祥在《中国民族史》中,根据三苗和楚人称呼、所处地域的关联性得出“三苗必为楚先祖”的结论[29],三苗与楚人确有地域方面的密切关联。地域的迁移、承继是楚公族与三苗一体化的重要实现方式。
历史上三苗经历了三次迁徙,在迁移过程中完成了与楚人的融合。涿鹿之战中苗族先民(即九黎集团)战败,向西南迁入长江中游地带形成了新的“三苗”部落集团[23]。尧舜禹时期,九黎部族的一部分来到长江中下游,建立“三苗国”。但禹征三苗,季连部落追随禹南征三苗,驻留荆州江汉。《路史·后记》载:“伯禹定荆州,季芈实居其地。”[24]留存江汉地区的季连部落与苗民处于交融状态,这是可准确追溯的楚人、苗人一体化进程。第三阶段发生于商末,鬻熊投奔周文王。周成王分封熊绎,《史记·楚世家》中有清晰的记载:“封熊绎于楚蛮……居丹阳。”[3]楚国正式立国,熊绎的封地大致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位于同一地域的楚人与三苗自然融合。由此三苗文化融入楚文化中,极大地塑造着楚文化的形态。至此,楚人与三苗的民族一体化进程基本完成。
春秋战国时期,越人与楚人通过国家战争、人才流动、族群通婚等形式进行着民族一体化。国家间的人才流动是民族一体化的重要环节。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楚国逃亡在外的大夫申公巫臣指导吴国的军事活动,吴王寿梦便“令其子为吴行人”[3]。吴王阖闾实行社会改革,重用楚人伍子胥、伯嚭发展本国,“举伍子胥为行人”,任用伯嚭为大夫[3]。
族群间的通婚也是民族一体化的重要途径。《史记·楚世家》记载:“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3]楚王室与越人通婚,越人的礼仪文化、生产方式等被带到楚国,促成了两族文化礼仪的交流和生产行业的沟通。春秋后期国家间的战争日益频繁,战争成为越人与楚人融合的重要手段。越灭吴,楚灭越,频繁激烈的战争推动三国最终融合。公元前306年(楚怀王二十三年)或稍前[21],楚灭越,楚国囊括吸收了越国[3],楚越一体化最终完成。楚人首先完成与三苗的融合,后又通过战争完成了与越人的融合,至此荆楚民族内部一体化进程完成。
荆楚民族一体化伴随着民族文化融合。楚人立国,楚公族同以三苗后裔为主体的荆人结合[22],塑造着当时楚国的民族文化形态。《汉书·地理志》记载“(楚)信巫鬼,重淫祀”[15],《淮南子·人间训》也称“荆人鬼”[32],楚国淫祀奉巫的传统正是从三苗文化中继承而来,三苗的信巫好祀使楚文化染上了神秘瑰丽的色彩。
越人的民族性格野性质朴,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该民族突出的习俗是断发文身,吴太伯奔荆后“文身断发”[3],越国政权传至勾践一代仍维持着“文身断发”的习俗,这是越人族群内长期流行的习俗。《墨子·鲁问》记载,楚国的南方有一个吃人的国家“桥”,这个国家中长子出生了就要被杀死吃掉。[18]《列子·汤问》也记载:“越之东有辄沐之国,其长子生,则鲜而食之……”[19]越人有食人的传统,文化特质野性血腥。楚越融合使得越人文化给楚文化带来了野性质朴的元素。
楚人尊火崇凤,因为对祝融的重视与尊崇,楚人形成了特殊的“尚赤”“尚东”的风尚。楚人的衣服、器物多见赤色,漆器大部分是黑底朱彩[34],很少有例外。楚人的座次以东向为尊,楚公族的墓葬头向从东,这些都与火神居于东方密切关联[34]。楚公族的尊火崇凤理念主导建构了楚文化的主要形态,是维持楚文化活力的主要动因。这种源自先民祝融部落集团的文化左右着楚文化的发展方向,是楚文化一以贯之的重要原因,也决定了荆楚民族的民族本色。
荆楚民族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融合还同中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与荆楚民族和中原的往来是密切相关的。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荆楚民族精神愈加理性和规范。
楚人从中原迁徙到江汉,受到了中原文化的浸润。楚族首领最初接受周成王的分封而立国即为楚人接受汉人分封制度影响的明证。楚文化中融合入汉文化,汉文化中的礼乐文化、典籍制度等对楚文化的面貌产生重要影响,楚庄王早年行“问鼎中原”[3]的鲁莽之举,但后期讨陈“以义伐之而贪其县”[3],学习中原之礼。越人在发展的过程中与中原交流,发生了汉化,面对中原文化的心态也发生了明确转变。从吴太伯自中原奔荆“断发文身”[3]融于当地土著到吴王寿梦问礼后慨叹“岂有斯之服哉”[3],这一变化折射出越人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与折服。
由上,荆楚民族的构成是多元的,它的形成过程是动态的。楚人立足本民族发展现状,与三苗、越人交往。荆楚民族一体化进程以楚国为主导,楚国包容了失去独立政权的三苗、越人;一体化的阶段性特征突出,楚公族首先与三苗融合而后与越人融合,最终实现荆楚民族一体化;一体化途径多元,不同民族之间以通婚、战争、迁徙、人才流动等方式交流、融合,逐渐形成了荆楚民族。荆楚民族一体化的进程伴随着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三个民族以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共同塑造了楚文化的形态。
三、结语
本文梳理了荆楚民族的流变发展过程,其中主要民族楚公族与次要民族三苗、越人通过迁徙、战争、人才任用、通婚等方式相互碰撞、融合,最终完成了民族一体化,形成了荆楚民族。不同民族的性格、风俗、文化在一体化的过程中交融,共同塑造了灿烂瑰丽的楚文化。
参考文献:
[1]舒之梅.五十年来楚族源研究综述[J].江汉论坛, 1983,(03):65-67.
[2]刘向.战国策[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3](汉)司马迁撰.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20.
[4]蒋伟男.《楚世家》文献辑证及相关问题研究[D].安徽大学,2019.
[5]王逸,洪兴祖,朱熹.楚辞章句补注·楚辞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2013.
[6]左丘明.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7]左丘明.左传[M].长沙:岳麓书社,1988.
[8]蔡靖泉.炎帝·颛顼·祝融——楚人始祖论[J].江汉论坛,2014,(12):77-81.
[9]刘玉堂.楚国宗法制度与等级构成——兼析楚国的社会性质[J].荆州师专学报,1994,(01):63-68.
[10]方向东.大戴礼记[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
[11]孔丘.诗经[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
[12]张正明.《“鬻熊为文王之师”解》辨误[J].江汉论坛,1983,(09):67-68.
[13]周明初.山海经[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1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15]班固.汉书[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
[16]梅桐生.春秋公羊传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17]袁唐,吴平.越绝书[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3.
[18]墨翟.墨子[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
[19]列御寇.列子[M].北京:中华书局,2022.
[20]田春锋.中国古史传说时代“征三苗”问题新探[D].陕西师范大学,2008.
[21]杨宽.战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22]刘玉堂.楚公族先祖的居地及其南迁[J].荆州师专学报,2000,(06):84-88.
[23]闫德亮.从九黎到三苗再到苗族——兼论蚩尤神话与文化[J].贵州社会科学,2015,(05).
[24]罗泌.路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
[25]卢静.礼记[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22.
[26]赵晔.吴越春秋译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27]李廷贵.再论苗族的迁徙[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4):11-12.
[28]严庆.解读“整合”与“民族整合”[J].民族研究, 2006,(04):20-29+107-108.
[29]林惠祥.中国民族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8.
[30]张云辉,唐靖,李明秀.关于蚩尤与苗族族源及迁徙问题研究综述[J].民族论坛,2009,(04):46-47.
[31]赵炳清.楚人先民溯源略论[J].民族研究,2005, (01):80-87+109.
[32]刘安.淮南子[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33]方诗铭.古本竹书纪年辑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4]张正明.楚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35]杨梓.抗拒与接纳——从《左传》看楚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的张力[J].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21,42(09):57-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