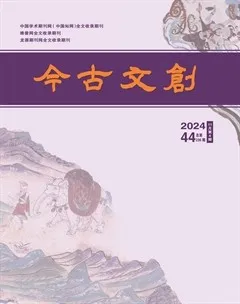被生产的主体——福柯主体观探析
2024-11-22陈瑞霞
【摘要】主体问题一直是福柯关注的核心问题,对主体的分析贯穿福柯思想研究的始终,他的分析涉及知识、权力、性和自我认知等多个方面。福柯阐述了三种将人转变为主体的对象化模式,并揭示了“人”这一主体是如何在不同的真理游戏中被建构的。在福柯看来主体并不是静态的、固定的实体,而是与各种权力关系交织而成的产物,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性的社会构造。
【关键词】福柯;主体;权力;知识
【中图分类号】B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4-0060-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4.015
西方哲学一直将主体问题置于显著地位。在米歇尔·福柯的哲学体系中,对主体问题的探讨更是占据了核心位置。他本人也曾提道:“我的目的是要创立一种据以在我们的文化中把人变为主体的各种方式的历史。” ①简而言之,福柯致力于揭示人是如何被主体化的,并深入解构这一主体化过程。不同于传统哲学的研究方法,福柯特别关注那些在传统哲学中被边缘化的群体,如疯人、囚犯和性倒错者等,他运用谱系学的研究方法深入探究了这些特殊主体的生产过程,试图揭示它们背后的复杂机制,从根本上把主体被生产的真相揭露出来。福柯明确指出,主体实际上是在知识和权力相互作用的场域中被“定制”与生产出来的,是一个动态、多元且不断变化的过程,而非静态、单一且永恒不变的实体。
在《主体与权力》这篇文章中福柯讨论了三种生产主体的客体化模式:“第一种力图给予自身以科学地位的探讨方式,例如,在普通语法、语文学和语言学中对讲话主体的客体化。再比如说,在这一种方式中对生产性主体,即劳动主体在财富和经济学分析中的客体化。” ②第二种是“分离实践中的主体的客体化” ③,即将主体自身内在地或与他人分割开来的过程,这种分离通常借助于权力的力量。比如通过权力/知识对疯子和正常人、罪犯和好人、性倒错者和性正常者进行区分。第三种是自我教育,即个体是如何教育自己把自己转变为主体的方式,例如在性领域内,人们如何学会将自己识别为一个“性”主体。福柯认为,“人”是通过这三种客体化的方式被生产出来的,它们互相整合,并相互促进。
一、作为主体的“人”的诞生
第一种主体化的方式即个体或群体试图通过将自己与科学知识联系起来,赋予自己一种科学的、权威的地位,这一主体化方式是在《词与物》中探讨的主体问题。在《词与物》这本书中,福柯通过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对文艺复兴以来直至20世纪西方的知识型做出划分,并梳理出三种不同时期的知识型,即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型、古典时期知识型和现代知识型。在对知识型进行考古学研究的过程中,福柯特别关注了人文科学,对“人的诞生”做出详细的阐述。在他看来,“人”是现代知识型的产物,主体是通过现代知识型被建构的。
三种知识型中,最早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型,以“相似性”为基本特征,其中语言也被理解为这个相似网络中的元素,因此词能够直接表达物,并且词与物两者处于一个互相交叉、融合的模糊空间内部。这种知识型并不需要将人作为认识的中心或主体,人的主体性在这一时期也并未被凸显。到了古典时期,知识型以同一性与差异性为原则,事物由直接存在于相似性网络中的元素变为存在于秩序图表中需要被表象的间接的对象,表象成为这一时期知识的最本质特征。在这一时期的知识型中,词不再与物同为世界自然存在的一部分,词的功能在于表象事物。“词能毫无遮挡地表征物,词和物快速而透明地达成了一致而人则消失在这种表征和表格的秩序中” ④,人在这种认知形式中只是一个过渡或者说是工具,人只是表象的承担者,对人自身的反思认识并没有出现,此时还未出现“人”。
到18世纪,知识型则演变为现代知识型,在这种知识型中“人”成了核心,成了知识普遍性的基础。不同于古典知识型围绕着表象与物的关系展开,现代知识型则转向了表象与物之关系如何可能。这时f264b715a7c5a1f2df1d2c98d3334559,表象的主体即“人”就被置入这一关系之中。经济学、生物学和语言学这些学科取代了古典时期的自然史、普通语法和财富分析,且这些学科都围绕着“人”得到解释。在经济学领域,人的劳动成为衡量财富的尺度;在生物学领域,由人这一生命体的结构和功能的联系决定着自然界生物规律;在语言学领域,人这一言说者站到了语言学的中心位置。这三门学科把“人”当作研究的对象和知识的课题,“人”便在现代知识型中诞生了。
经过对不同时期知识型的深入分析,我们观察到,虽然人始终存在,但在文艺复兴和古典知识型时期,作为主体的“人”还没有诞生。在古典时期,知识的焦点凝聚于表象之上,个人与其内在表象及外界被表象之物,通过古典语言的桥梁实现了直接的沟通与连接。这一过程无须依赖于对人性本身的深入探索来构建以表象为中心的知识体系,人在这一体系中更多扮演着展现与传达表象的工具性角色。此时期,所有的知识体系与语言表述均围绕着表象及其内在的逻辑秩序展开,而非聚焦于人类本身。因此,人并未能占据知识的核心位置成为主体,关于人的科学研究也尚未被视为必要或迫切的需求。
随着现代知识型的兴起,作为主体的“人”才逐渐显现。到18世纪,只能建立起同一与差异的区分的古典知识型,显得愈发力不从心,它难以有效整合并阐释新时代的劳动形态、生命现象以及语言的复杂性。这些新兴领域的内容,其起源、特殊个体的多样性以及潜在的秩序结构,远远超出了古典知识型所能提供的框架与解释范畴。古典知识型崩溃,现代知识型确立。现代知识型试图反思并穿透表象去找到一个超出表象的知识中心或基础来应对科学知识的需要。在福柯看来,“康德哲学建构了这样一个表象者。同时,康德哲学又使这个表象者有成为知识对象的可能,于是,主体便出现了,并且成了现代知识型和现代知识的基础和中心。” ⑤这就是第一种生产主体的方式,即在科学知识的需求下,给予人科学并权威的地位,把人放置到知识的中心位置,将知识构建在“人类学”的框架内,并发展出人文科学,使得“人”既是认知的主体也是客体,“人”由此而诞生。
二、分离实践
第二种主体化方式,是分离实践,指用权力/知识对人进行分类,其中最著名的是对疯人、不正常人的区分。在这一区分过程中,权力/知识发挥着关键作用。权力生产知识,并将这些知识作为真理标准使个体反思自身(自身内在的分离)并对人进行区分(与他人分离),从这种区分中寻找出诸如疯人、性不正常者、畸形人等不合乎“标准”的人。这种分离实践不是简单地将人分为不同类别,而是通过权力/知识机制的运作,去参与个体身份和自我认知即主体的形成过程。
(一)疯人
首先是对疯人的区分,这种区分在《疯癫与文明》中有详细的阐述。福柯在这本书中对疯癫进行了考古学的探究,并指出在不同时期疯癫的地位是不同的。福柯对疯癫史的研究最早追溯到了中世纪,当时伴随着麻风病人的消失,对待麻风病人的严格分离的形式被流传下来对待“精神错乱者”,在这个时期疯癫还只是一种一般的现象,一种很平庸的经验。到文艺复兴时期,“疯癫才变得夺目” ⑥,它甚至代表着一种知识、一种预示。在这时虽然疯子开始受到社会的排斥,但此时疯癫仍是与世界相容的,并未站在理性的对立面,“这个世界在17世纪初对疯癫是特别友善的” ⑦。
到17世纪中期,随着古典时代大禁闭场所的到来,疯癫者不再被友善地对待,“疯癫就同这个禁闭的国度联系了起来” ⑧。此时疯人与失业者、穷人、流浪汉通过“治安”的手段以一种“懒惰”的形象被禁闭起来,他们被隔离、被排斥。而在这种禁闭场所中,疯癫再次与失业者、流浪汉等进行区分并被划分成为“奇特的物种”,甚至被当成野兽来展示以供观赏。疯癫在这一时期被彻底地排斥,理性对其进行着绝对统治。
到18世纪,医学开始介入疯癫,精神病人正式出现,人们开始用更加“科学化”的方式对疯癫进行治疗。疯癫作为精神疾病被细致地划分出不同的种类,并伴随着不同的治疗方法。到19世纪,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现代精神病院诞生了,疯人被收治入院,在精神病院中接受医生的监视和审判,在这里医生的话语代表绝对的权威,此时疯癫被完全地统治。
通过对疯癫史的考察,福柯认为,疯癫发展至此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它是被创造出来的。疯癫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定义,预言者、反劳作的人、野兽、精神病,但这些对他的定义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社会和文化通过特定的排斥和隔离实践所创造和维持的概念,没有这种特定排斥和隔离实践,疯子便不会成为疯子。
(二)不正常的人
在《不正常的人》中,福柯对“不正常的人”的三个源头,畸形人(monstre)、需要改造的人(individu à corriger)和手淫的儿童(enfant masturbateur)做出谱系学的考察研究,清晰地阐明了这三种群体是如何在知识权力的引领下被区分并被合流成为“不正常的人”。
福柯所指的畸形人是在法律范畴中的畸形人,比如双体人、双性人,之所以对这类人进行区分,是因为这些人会因生理异常而引起法律的混乱。当这类群体面临法律的制裁时,司法系统往往难以做出公正有力的判决。双性人或双体人模糊了法律的界限,给法律的执行带来了挑战。于是,精神病学开始介入到这种法律无法解决的领域,用精神医学的概念对这类人加以分析和区分。
18世纪中期,在权力机制对性领域的愈发渗透中,伴随着一本名为《手淫》的书的出版,对儿童手淫问题的关注被放置在了社会讨论的中心。当时社会是把手淫当作一个生理学和医学问题来进行研究的,从医学观点出发认为多种病症都是由手淫所引发,儿童手淫会给身体带来多种不利的影响,由此手淫被病理化,并被认为是一种不可治愈的疾病。针对这一问题,精神病学开始介入,并发展出“性本能”这一概念对手淫问题做出分析和阐述。
当17世纪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时候,生产率的提高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目的。为了满足资本社会的需求,权力机制开始对人的肉体进行规训。在这一过程中不但可以规训出符合社会需求的“标准人”,并且还会筛选出那些拒绝规训的人,那些抗拒由纪律对身体进行压制和改造的人。这些“反抗者”因无法满足资本社会的期望,便被排除在社会的边缘,被界定成“不可改造的人”。
到19世纪,随着精神病学对各种领域的渗透以及扩张,那些对社会秩序有所偏离或不符合社会标准的个体如“畸形人”“手淫的儿童”和“需要改造的人”一起被精神病化,被规入“不正常的人”的范围中。
通过对疯人、不正常人的追根溯源的探究,福柯表明疯人、不正常的人并不是一种病理现象,对他们的区分,也不是一种自然的区分,这种将是否偏离社会秩序当作划分正常与不正常人的标准,是权力/知识运作的结果。权力知识生产出所谓正常人“标准”,并对不符合“标准”的人进行区分。首先,这种“标准”和区分过程能够让人们有意识地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是否与之相一致,在这种自我检验中,个体努力按照社会标准来改造自身,创建出符合社会规范和期望的主体,这种自我认知对主体的生产有着直接的影响。其次,区分不但能够生产“标准”的人,而且其主要目的是能够找寻出那些不符合“标准”的“不正常的人”,并对其进行隔离、规训,从而能够更好地维护资本主义现代秩序的正常运行。简而言之,这一主体的生成方式即对人进行区分,要进行区分,就必然要确立区分标准,人们便是根据这一区分过程及“标准”去参与个体身份和自我认知也就是主体的生成过程。
三、自我教育
第三种主体化方式,是自我教育,即个体如何将自己转变为主体的方式。这种主体化的方式,“实际就是主体标准支配现代个体自我意识的过程” ⑨。比如在性领域中,个体是如何通过话语实践,构建出自己的性身份和主体的。
在《性史第一卷:认知意志》中福柯考察了近三个世纪关于对性的管理。在维多利亚时代,性是不能公开谈论的,它被看成是禁令、戒律,只能被夫妻所垄断。但是在18世纪大家普遍认为性被压抑的时代中,围绕着性,发生一次“话语爆炸”,“权力机构煽动人们去谈性,并且谈的越多越好” ⑩。坦白在这时成为一种重要的捕捉性话语的形式,并经过长期的发展不断地扩大其范围,延伸到病人与心理医生、教师与学生、犯人与专家等等。随着教育学、医学、经济学的介入,产生了性科学,并随之产生出各种各样的性知识,制定了各式各样的性规范。夫妻的性生活被确定成一种规范,而关于那些与其相反甚至是存在错位的各种性经验,则被画上了具有“反自然”倾向的性倒错者的标记。
人们的性行为有了一些规范性的准则,人们开始以一些不正常的性生理和性心理人物比照自身,辨别自己是否是有着正常性欲的人,自己的欲望对象是否正确,自己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这一过程中,权力巧妙地渗透至每个人的内心,将性欲的起点深深嵌入道德与理性的框架之中。进一步地,人们不仅被动接受这种规训,还主动成为权力的执行者,协助监督、鉴别那些被权力体系划分为性倒错、性变态、性反常的个体。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些被归类者试图反抗时,他们往往不自觉地采用权力所设定的分类体系进行辩驳,这实际上是在无形中承认了这种分类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如此,权力不仅塑造了人们的性观念与行为,还悄然构建了自我审视与相互评判的社会机制。这就意味着他们默认了这种区分,承认了这种通过规范化道德构建的自我。人们把各种“性标准”和“性观念”内化到自我意识中,使主体化的过程成为一种个体自觉自愿的行动,这样看不出任何被改造的痕迹,因此也感受不到权力知识体系对主体的干涉和控制。
主体陷入到了一种“自愿服从”的陷阱中,以“自我塑造”的姿态显现,使得现代个体将主体化认为是自我教育的过程。于是,个体自觉自愿地依照标准去改造自己,改造为标准的现代人。这样,现代个体浑然不知地陷入受知识——权力机制奴役的陷阱之中。
这一生产主体的方式,福柯认为,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早已盛行。在古代,虽无烦琐精细的法律与制度强制约束性行为,却恰恰彰显了人们对快感的自主驾驭能力。在没有硬性规则的框架内,人们并未放任自流,反而展现了一种自律精神。对于古希腊人而言,这种自我约束的驱动力源自对美德声誉的追求及对个人美学风格的塑造,它体现出一种生存美学。另一方面,在罗马时期,所有人都关注自己。各种各样的关注自我的技术,都旨在通过对过去经验的回忆和辨识,让既定的真理进入主体之中,被主体消化和吸收,使之为再次进入现实做好准备,去改造和优化主体。
福柯认为,现代社会中这种主体“自我塑造”的方式,正是吸收了古希腊时期的自我技术、关注自我的实践。古代世界将个体塑造成为有能力治理他们自我的主体,这种方式被现代社会借用改造,使人的主体领域成为权力控制肆虐的场所,这就是现代社会个体化的过程,其中权力的运作极为重要。从伦理主体到现代主体的转变,也就是从“以伦理为导向的道德”向“以规范为导向的道德”的转变。
四、结语
通过对三种主体生成方式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福柯看来主体的产生是这样一个过程,人在科学知识的探讨中诞生,在全景敞视社会中被规训成为符合社会标准的“正常人”,在政治化的“自我技术”下将“正常人标准”内化到自身之中,按照知识权力无形中给予自身的社会标准生产自我,并由此认为“我”这个主体是自主建构而成的。福柯认为,这一主体化过程是被一只无形的“权力之手”所掌控的,并不是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在自由地构建自我。
在福柯看来,主体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种构形,即主体是被制作出来的,一种被赋予形式的东西,是具有历史性的。主体化过程中会受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权力关系的影响,导致主体的构成和表现具有多样性和变化性。那也就是说,个体一旦成为“人”,那么他肯定会不同程度地被他所处时代的知识(真理)所影响,而知识又是被权力生产出来的。由此看来,主体深陷权力的漩涡之中。但是,“尽管我们无法从权力关系中解脱出来,我们也并非简单地由这些权力关系所决定:我们并非注定要不加批判地再生产出我们社会中主流的规范和价值观。” ⑪福柯强调要对现代主体进行反思。他认为,通过自我反思和批判,个体可以意识到自己是如何被知识、权力和社会构造所塑造的。人们应通过不断地自我审视和自我改造,超越社会给予的身份限制,实现自我解放。
福柯对主体问题的分析对后来的哲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对主体问题的分析是多维度的,涉及历史、权力和自我认知等多个方面。他的理论挑战了传统的主体观念,强调了主体的历史性、社会性和建构性。福柯的主体观念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中的个体身份和自由提供了深刻的洞察力,对当代哲学和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注释:
①(美)L·德赖弗斯、保罗·拉比诺著,张建超、张静译:《福柯的附语:主体与权力》,载《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
②(美)L·德赖弗斯、保罗·拉比诺著,张建超、张静译:《福柯的附语:主体与权力》,载《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
③(美)L·德赖弗斯、保罗·拉比诺著,张建超、张静译:《福柯的附语:主体与权力》,载《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
④汪民安:《论福柯的人之死》,《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5期。
⑤刘永谋:《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从知识考古学到“人之死”》,中国人民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
⑥汪民安:《福柯的界限》,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⑦(法)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疯癫与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
⑧(法)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疯癫与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
⑨刘永谋:《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从知识考古学到“人之死”》,中国人民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
⑩(法)福柯著,佘碧平译:《性经验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⑪(美)狄安娜·泰勒著,庞宏译:《关键概念》,重庆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参考文献:
[1](法)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2](法)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3](法)福柯.词与物[M].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
[4](法)福柯.性经验史[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5](法)福柯.不正常的人[M].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6](美)L·德赖弗斯,保罗·拉比诺.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M].张建超,张静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
[7](美)狄安娜·泰勒.关键概念[M].庞宏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9.
[8]汪民安.福柯的界限[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3.
[9]莫伟民.主体的真相——福柯与主体哲学[J].中国社会科学,2010,(03).
[10]汪民安.论福柯的“人之死”[J].天津社会科学,2003,(05).
[11]刘永谋,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从知识考古学到“人之死”[D].中国人民大学,2005.
[12]Cremonesi,L.,Irrera,O.,Lorenzini,D.,and Tazzioli,M.Foucault and the Making of Subjects[M]. London:Rowman & Littlefield,2016.
[13]Portschy Jurgen.Times of power,knowledge and critique in the work of Foucault[J].The Social Life of Time,2020,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