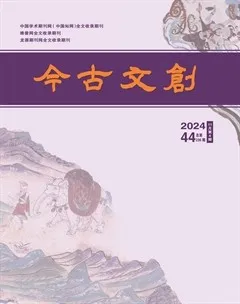从陆游饮食诗中管窥宋人的素食养生饮食观念
2024-11-22郭朝安
【摘要】陆游饮食诗中关于素食、养生的诗句颇多,其自身饮食观倾向于素食养生。两宋素食发展迅速,从而素食成为大众主动性饮食选择。从陆游蔬食饮食中细察,儒释道三家于饮食方面的思想大大影响了陆游的饮食观,广大民众素食养生的思想也来自儒释道三家的饮食观念。
【关键词】陆游;素食;养生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4-0056-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4.014
两宋作为中华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峰,陈寅恪先生曾提及:“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245两宋之际所遗留的文化著述极多,包括大量的文章、杂记、史料、诗词等等,这些著作中所包含的饮食方面的记载极多并且也较为繁杂。无有争议,中国饮食的一大转折点就在于两宋之际,现如今主要的烹饪方式大多都是肇始于两宋时期,素食作为一种饮食观念已早有渊流,不过成为体系性、社会性的饮食观念是在两宋之时,素食在此时期内迅速发展并渐而小成。一饮一食入诗这在唐时是不多为见的,在唐时,诗词的气质要求是高宏而深远、壮美而大气,所以以饮食这种日常生活的枝梢部分入诗,很难在唐人诗集中所逢见,但宋人重视现实生活中的枝梢微节,格物而致知。如果说唐时,诗者往往是“至广大”,那么到了宋时,诗者则开始“近精微”了,宋代文哲很擅长以一朵花或者一枚雪片的姿态去体会宇宙自然,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这样一来,饮食作为日常生活中最易接触的事情,那么饮食入诗也就不足为怪。陆游作为南宋诗坛的重要人物,其《剑南诗稿》有9300余首诗,其中关于饮食的诗为3622首。如此洪量的饮食诗中包含的食材、制作方法众多,其中关于素食养生的部分是陆游饮食诗中的一大特色,以此作为研究切入点,对素食养生为何在两宋之际发展如此迅速并成为体系,也就能够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素食起源早在三代夏商周时期,此时素食群体被称为“藿食者”[2]447,不过这一群体是被动性素食,与此对应的乃是曹刿口中的“肉食者”,多指贵族、士大夫群体。居孝时期的斋戒也视为素食性活动,先秦道家方士的“长生食素”饮食行为,对先秦上层贵族的饮食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450。素食真正在全社会层面普及应是以南朝萧衍所著的《断酒肉文》为转折,他要“全天下的僧俗无一例外地实行严格的素食”[2]451,随着唐时佛教的鼎盛,人们对于素食的接受从被动逐渐转化为主动,到了陆游所生活的南宋,素食更成为“读书人”生命品质的体现,并且是素食思想中,能够促进养生概念的实践方式。陆游饮食诗中关于素食研究不是很多,本文专注于其素食思想,探讨陆游的素食观,并由他的饮食诗做切入深究两宋素食观念的发展。
一、素食发展渊流下的主动饮食选择
素食思想来源的途径是复杂的,按照赵荣光先生《中国饮食文化史》中所述,素食应该分为:“准素食者群、方士道家的冀长生食观、佛教戒律的素食思想、其他行为素食者群。”[2]447而陆游的素食思想是经过唐宋几百年间的素食思想的发展演变,从而逐渐形成的特色素食理念。邱庞同先生在其《饮食杂俎——中国饮食烹饪研究》一书中认为:“素菜在宋代发展较快……素菜的象形菜做得也很逼真……在汴京、临安的市场上,出现素菜馆,专卖素菜。”[3]40两宋之际,素食在餐饮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素食思想和素食实践在社会上被接受的程度,陆游的素食行为也是受当时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人(今浙江省绍兴市人),其一生命途多舛、仕途不顺,著诗极丰。陆游所著《剑南诗稿》是其一生诗作所编著,其中陆游饮食诗所提及的饮食大多是闽浙、吴赣、巴蜀等地区的饮食,而其中又以其家乡浙江山阴地区为多。素食在陆游饮食诗中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在两宋,许多诗人学者都推崇素食,苏轼、刘夔、陈著、张耒、钱时等都对素食褒赞有加,陆游更是一位切实的素食实践者。而对于陆游来说,切身实践素食饮食,不只是一个文人对于自己生命品质的体现,更多的是出于对自身身体的考虑,而由素食进而产生的养生观,便是陆游饮食诗中素食的根本原因所在了。陆游曾言:“我少本多疾,屡亦频危殆。皇天实相之,警告意有在。”[4]4181可见陆游饮食诗中的素食特色与他自身有很大的关系,但这素食为何在两宋之际受人追崇,其多来源于自唐宋之际愈来愈突出的素食理念。
如孟元老描写北宋汴京的著述《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及有素分茶,如寺院斋食也。又有菜面、胡蝶齏、疙瘩,及卖随饭、荷包白饭、旋切细料馉饳儿、瓜齏、萝卜之类。”[5]29“分茶”在东京城中是大饭店,售卖各种主食和荤素菜肴,所故,“素分茶”应是专卖素食的饭店,餐饮业中出现这种情况,说明社会中素食之风必是人所共推,有一定的受众群体且数量也小有占比。这样的情况在南宋成书的《梦粱录》中也有相似记载:“又有专卖素食分茶,不误斋戒,如头羹、双峰、三峰、四峰……”[6]136至陆游生活的南宋时期,京城临安(今杭州市)沿袭汴京风气,素食分茶店的数量尤胜以前。素食能够在繁盛的政治与经济中心临安城风靡,可见素食观念已在社会各个方面深入,《山家清供》《本心斋蔬食谱》《茹草记事》等素食著述刊行亦是水到渠成,这些由最初级素食观念产生,再到社会实际行为演化,最终到素食著述共经历三级转化,此时素食著述的出现表明素食已不单单是一项简单的饮食行为,更是一种由饮食实践而升华的一种文化理念。
陆游饮食诗大量的蔬食性选择是其饮食方面的一大重要特色,这与他自身内在和社会外在因素相关,两宋社会渐渐风靡起来的素食之风、士大夫群体推崇素食,以及越来越丰富的物产和烹饪技术的发展等,这些作为外部映射对陆游的饮食有很大的影响。宋文人的精神状态渐次由唐时的恢宏气象转变为微致清雅,对于个人生命品格有极严的要求,以致宋仕宦大夫从肉食转而追求素食,苏轼《撷菜》:“秋来霜露满东园,芦菔生儿芥有孙。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7]2202苏轼也很推崇素食,认为素食大有比鸡豚更美妙的滋味,素食在宋文人当中已发展成为更玄妙的一种人生追求,陆游作为两宋时期的一位文人士大夫也概莫能外,渐而被影响。陆游对于蔬食的选择,并不是被动性的,这与僧徒被动性食素、下层贫苦百姓被动性食素是存在根本性的区别,在《蔬食》中:“墙阴春荠老,笋蕨正登盘。野馌元无妇,村醅不属官。何由取熊掌,幸免买猪肝。犹胜烦秦相,绨袍闵一寒。”[4]3519对于此时的陆游来讲,“熊掌”与“猪肝”都是免于口腹,“春荠”与“笋蕨”都是正可口的登盘之食,于外在条件映射下,从而主动性地选择素食,这也是两宋之前世人所不具有的。
二、陆游饮食诗中素食养生现象
纵观陆游一生饮食诗书写,少年与青年时代所留诗作寥寥,直至出仕之后饮食诗所录渐多。他的素食方面饮食诗书写并非起始青年时代,这与其他一生笃奉素食之人亦不相同,北宋晏殊曾有:“公风骨清羸,不喜肉食,尤嫌肥羶”[8]47,晏殊自年少时即是尚好素食,但陆游的素食观念却是随年龄的增长慢慢被他越来越重视,他在三十几岁后外出为官时亦常有:“牛尾膏美如凝酥,猫头轮囷欲专车。”[9]6这种肉食盛宴情况也是时时出现在日常生活中。陆游雅好蔬菜,在他五十岁之后素食所占饮食比例渐渐为多,像《食荠》中所言:“采采珍蔬不待畦,中原正味压莼丝。”[9]64路边繁盛随处可见的野荠菜也是他喜爱的蔬食,尽管生长于路边荒野,但在此时也味美胜于精心种植的莼菜了。陆游的素食并不只是为了吃素而素,其是接受良好幼年、少年以及青年教育的“读书人”,两宋之际文教兴盛,承平既久的世事,和对待文人士大夫比之前代尤胜的朝廷,致使社会涌现了更多的读书人,儒学在此刻得到了积百载而一勃发的演进。陆游作为儒学的后学者,往往在其饮食中尚清雅、素洁、质朴、平淡的食物观念,如在《苦笋》中云:“藜藿盘中忽眼明,骈头脱襁白玉婴。”[9]43藜菜和藿菜本就是寻常可见的杂蔬,可是陆游目光所及的藜藿能够清然使得精神“忽眼明”,连脱壳的苦笋在洁白如玉的状态下也使得人口腹大开。此素食贵清雅的想法也是在陆游潜意识的素食观念中,再如《野饭》中说:“山深少盐酪,淡薄至味足……是家吾所慕,食菜如食肉。”[9]45这种由淡薄滋味阐发所产生的精神享受,并且用饮食的方式来承载,深深契合他内心深处的素食饮食观。
在陆游出仕为官的几十年中,我们可以在他的饮食诗中常见酒、茶这类的出现,但出现次数最多的几类食物便有“羹”“芋”,两宋政府对于官员的薪俸是非常慷慨的,《宋史·职官志》记载宋太宗言:“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10]4115在如此高俸禄下的为官时日,陆游饮食日常仍尚菜、羹,如在《晨起偶题》中言:“风炉歙钵生涯在,且试新寒芋糁羹。”[9]3其年陆游三十六岁,陆游喜爱芋、羹的饮食习惯在青年业已深种,如在《秋夜读书每以二鼓尽为节》中言:“秋夜渐长饥作祟,一杯山药进琼糜。”[9]4山药羹是陆游常用之羹,由于少时体弱多病,其自身久病成医从而多读医书,也有一定的医学常识,这时陆游已渐渐步入中年,以素食方式养生对他饮食影响变大,这在其辞官归山阴之后所书写的诗词中常有体现。其后《归云门》:“甑炊饱雨湖菱紫,蔑络迎霜野柿红”[9]78,《幽居》:“芋魁加糁香出屋,菰首芼羹甘若饴”[9]90,由于地利,陆游辞官归乡之后,饮食其更加倾向于素食。山阴家乡的风物奇多,尤其瓜果蔬菜更是不缺,湖菱、野柿、芋、菰首、芼等等都是陆游饮食的第一倾向性食物。
陆游的养生观念是在年少时发端,他在人生的前三十几年多在家乡山阴求学读书,而陆游的高祖陆轸对于道学颇有建树,陆游家族是为山阴地区的藏书世家,陆轸于道学所著《修心鉴》更是后世子孙必读之物,道学视为陆游家族内“家学”不足为过。在《道室试笔》中说:“吾家学道今四世,世佩旌真《三住铭》”[4]3446,陆游对于道学的接受也与年少时家学启蒙有关,他曾在《古风》中言:“少年慕黄老,雅志在山林。”[4]1140道家又切实为素食养生源流之一,在陆游中年之后素食用以养生越来越受到他的重视,并且之后逐渐切身奉行。他在《饭罢戏作》中言:“杜老死牛炙,千古惩祸败。闭门饵朝霞,无病亦无债。”[9]72陆游此时50岁,可见他内心对于食肉所带来的严重不利后果深信亦然,所以他在个人饮食观念中,深信道家素食对于养生的积极作用。陆游常常游历拜访各地道观,与道士交往中不免受他们饮食习惯的影响,如《小憩长生观饭已遂行》中言:“道士青精饭,先生乌角巾。”[9]70青精饭是用南烛枝叶捣汁浸饭,再把米蒸熟为饭,呈青色,故称青精饭,这种用植物的汁液融合稻米的方法,正是道家素食养生观念于饮食方面的体现之一,陆游对此喜爱,是由于内心对于养生理念的追求使然。此外陆游晚年对于药物嫩苗入馔十分热衷,如在《戏咏乡里食物示邻曲》中言:“药苗入馔逾天台”[9]174,《山庖》:“更剪药苗挑野菜,山家不必远庖厨。”[9]194他在山阴家乡的晚年种植蔬菜兼药苗,以药苗入馔大抵是其晚年身体康健的重要因素,这对于养生亦是大有裨益的。
三、素食养生饮食观念旨因深耘
陆游作为两宋时期的个体,素食饮食观念不是独属于其自身的思想,也不是由他发轫的,他的素食观念是受社会群体的影响,又结合他自身的实际情况,从而使其成为素食饮食的奉行者之一,这是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共同促成的。宋代素食发展已升华于饮食基本苑囿,如《山家清供》记载有一石子羹:“溪流清处取白小石子,或带藓衣者一二十枚,汲泉煮之,味甘于螺,隐然有泉石之气。”[11]29如此煮藓衣石子而品,已然是用口腹饮食寄予清雅观念,是一种升华样式素食饮食文化的较为“极端”性质的表达,而又以饮食为基底,是素食的一种方式。素食对于陆游来讲是一种喜爱和选择,为何于两宋发展如此“质变”,于陆游素食养生观中可以洞见。
自汉以来,儒家是社会主导思想,佛、道发展,到魏晋隋唐,三家思想总体呈激荡互争之势,但已有合流的趋向,入宋之后三家合流渐趋明显,宋真宗曾言:“依佛修心,依道养生,依儒致仕。”[12]552三教合流对于社会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陆游在此环境中也概莫能外。陆游本身自是一位儒者,其深受王安石临川之学的影响,崇尚“平淡而山高水深”的人格意趣,不追求豪奢,在饮食上便是淡而知味,如《对食戏作》中言:“采掇归来便堪煮,半铢盐酪不须添。”[4]3268这种追求质朴归真的思想,其深源于儒家,可如孔孟食道。食无求饱、养气为先、耻于味欲等都已刻入儒者的饮食中,陆游在《居室记》中有言:“朝哺食饮,丰约惟其力,少饱则止,不必尽器。”[13]2159可见陆游对于养生不必饱食的理念源于此处。又有《书警》:“堂堂六尺躯,勿为口腹欲”[4]4037,《暑中北窗昼卧有作》:“中年弃嗜欲,晚岁节饮食”[4]4181,由此可见陆游多崇尚清淡蔬食,而不求豪奢之食,其产生“畦蔬胜肉羹,社酒如粥醲”的饮食观念也就不难理解了。[4]3717
道家对于陆游的影响是初始于少年时期,陆游十分钦羡道家“腾猿俊鹘争先后,饥食松花掬飞泉”[4]687的状态,所以在他的饮食中常常以道家的养生观来指引自己的饮食,希望以此能达到道家餐风饮露的玄妙状态。陆游的一部分养生观自道家养生理念脱胎,如《山中作》“饮水饭蔬身顿清”[4]964以至超然物外境界,另外《次韵范参政书怀》中“芋粟多储煮复煨,一尘那许到灵台。虹穿道室炼丹熟,龙吼空山匣剑开”[4]1753这样的期许也是只有芋粟而已,道家自有进行斋戒渐而养生之意,肥甘是道家饮食所要避免的,《七发》中有言:“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14]2,所故,陆游在《对食有感》中言:“养生所甚恶,旨酒与大肉”[4]4355,这样的养生理念对于陆游日常生活影响益深。另外,道家的饮食养生多贵灵药,如枸杞、茯苓及山药类,他在《道室即事》中说:“松根茯苓味绝珍,甑中枸杞香动人”[4]3870,《秋夜读书每以二鼓尽为节》:“秋夜渐长饥作祟,一杯山药进琼糜”[9]4,这些有所提及灵药,都为陆游素食养生而所食之物,这样的养生理念深源于道家是有迹可循的。陆游的饮食养生观深植于道家饮食养生理念,且此并不单单影响陆游一人。
佛家在后周时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但到了北宋时逐渐舒缓且得到了发展,宋时佛教繁盛,很多文人士大夫通过与僧徒方士的交流,来丰富完善自身的精神境界。陆游多与名僧为友,佛家的戒杀和素食对于陆游饮食影响颇大,我们在他的饮食诗中常看到其与僧人往来的日常,例如《僧饭》中:“何当弃簪笏,终老掩山房”[4]1223,晚年由于地利与佛家修者有频繁的来往,《梅市暮归》中:“旅羹芼芋糁,僧饭敷白毡”[4]4033,僧饭是其喜食之物,陆游爱食粥、羹的饮食习惯很大程度上是借由此而生。陆游一部分食蔬的习惯也由佛家的影响而产生,如《戒杀》中言:“日夜相残杀,曾不置新须……朝饭一鬴豆,暮饭一杯蔬”[4]1886,表明其受到佛家戒杀和素食等理念影响,这在两宋时期是合理的,佛家思想影响普通百姓,民众多有崇佛向道的倾向,陆游虽不是纯正的素食者,但其素食倾向亦是深受佛家影响,对于普通百姓来言更是如此,素食理念在整个宋代社会的发展,与佛家的发展和其素食、戒杀等理念不无相关。
陆游的个人饮食观念倾向于素食养生观,这与其自身性格因素有关系,也是各个方面相互促成的最终选择,但对于社会大范围群众的素食选择行为,和最终演进的素食文化来讲,儒释道三家理念即在此处影响了陆游,从另一种方面来讲也深深间接影响了整个社会群体,在这里上至皇室贵族官僚,下至佃夫走贩,都把主动素食作为自己的一个饮食选择,不管是出于儒者教化、自身实践的原因,还是佛家理念普惠大众因素,抑或是道家的发展及欲获长生梦想的追求,在思想、文化波射范围来讲,素食在两宋时期被大众接受且素食产业能够迅速发展,都与这三家思想下的饮食文化观念联系较深,陆游素食养生理念既有其自身特殊性又有社会群体普遍性,总之,两宋素食养生饮食观念总体是来源于三家理念。
四、结语
两宋之际素食养生的发展是承隋唐的理念迸发而出的,陆游饮食诗中有众多的饮食种类,素食养生能够成为其饮食诗中不可忽视的部分,既与其自身有关,也与素食理念在两宋之际得到很大的发展息息相关,两宋之际的素食理念脱胎于社会主流的饮食观念,被易受到文化影响的文者士大夫群体所接受,在思想观念领域得到了一次重要的饮食观念洗礼,故在实际表现上便是素食成为一种饮食的追求与践行,两宋饮食书籍如《山家清供》《本心斋素食谱》《茹草记事》等关于素食的书籍版刻于众,其对于社会全体民众的素食领向性是非常显著的,素食成为众多饮食中的一种选择而被人接受。素食养生的发展不单单与思想层面有关,还得益于当时在烹饪、物产、交通等方面的进步。正因社会经济的繁荣带来社会总生产的增加,物产的丰富使得人们饮食的选择增多,烹饪技术的发展集成,使得素食的口味能够让更多人所接受,在社会客观物质方面,两宋社会为素食的普及和推广造就了丰厚的实质性土壤,让素食能够落地生根。
此外,素食养生是陆游主动选择的,陆游受整个社会群体的影响,对于素食是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接受的,这种对于素食的追求不单单是其自身的实践,更是整个社会群体的共同行为。素食与养生的前后递进关系,并非在陆游及其所在的两宋时期才产生关联,但是这两者的关系被大众所认可是在两宋时期发生的,当时社会上层对于素食养生倍加推崇,既有由上而下的风气推移,又有由内而外的饮食观念横生,故在整个两宋社会素食能够得到广大民众的接受。
参考文献:
[1]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A]//金明馆从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赵荣光.中国饮食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邱庞同.饮食杂俎:中国饮食烹饪研究[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
[4]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5](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
[6](宋)吴自牧.梦粱录[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2.
[7](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8](宋)吴处厚.青箱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9]孔祥贤.陆游饮食诗选注[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
[10](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1](宋)林洪.山家清供[M].北京:中华书局,2018.
[1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3](宋)陆游.陆游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4]萧统.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作者简介:
郭朝安,男,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饮食文化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