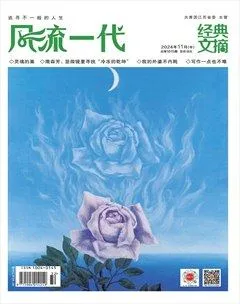稻米恩慈
2024-11-21傅菲
每一粒大米,都住着我们的双亲。
从一碗白米饭里抬起头,看见窗外的田畴莹绿,斜阳朗照,白鹭在柳滩之上低飞。四月的河,吐出泱泱之水。
新草覆盖了田埂,豌豆抽出了丝蔓,开出了花。花是红蕾,粉红花瓣、白色花萼,如一只只彩蝶,迎阳绽放,迎风而舞。田已耕耖,灌满了水,白白亮亮,如天空之境。塑料秧篷里,谷种长出根须。根须细白,如蚯蚓的幼虫,往泥层里扎。暖阳熏七天,谷尖冒出芽叶。乡人称谷笃芽。小鸡破壳,轻轻啄,素称笃。谷的芽胚似乎带有喙,啄破谷壳。
芽叶太嫩,似有似无,不着色,芽须一根根浮起。泥层尚未褪尽寒气,暖阳又熏三日,芽须浮出了一层稀稀薄薄的绿意。这个时候,若是多雨,谷种将烂根而死。谷种下田之前,翻晒一日,用石灰水冲洗,去腐蚀去虫卵,再入箩筐,于温水里浸泡两三日,催发须与芽。须与芽,是植物的生命两极。须,深深往下扎,与泥土深度纠缠,融为一体;芽,积攒所有的拼劲儿往上探,开枝散叶,去迎接阳光,也去临风沐雨。没有深扎的须,就没有遒劲的枝叶。
秧苗油绿了,已过了谷雨。第一次拔秧,称作开秧门。开秧门有淳朴、庄重的仪式:簸箕摆在田头,鞋子摆在田埂中央,拔秧人对着上苍作揖、对着秧苗作揖。祈求上苍,赐予我们风调雨顺;感谢秧苗,赐予我们粮食。
父亲挑着秧苗,扁担咔嚓咔嚓地响,像吃脆饼一样。秧须沿路滴着水,水线弯弯扭扭。我跟在父亲身后,望着自己家里的水田。那块水田有两亩二分,呈不规则长四边形。一家子的口粮来自这里。水田肥沃,泥黑且厚实。泥已烂浆,蹚着没至脚踝的水。泥鳅、鲫鱼、白鲦,一群群,掀起微小的水波。我和父亲并排插秧。父亲移动着手指,蜻蜓点水一般,秧苗就稳稳地插进泥里。我也飞快地移动手指,可插下去的秧苗,又很快地浮了上来。父亲拢紧手指,抄紧秧苗,示范给我看:“秧是手指带进泥的,而不是浮皮潦草地堆在泥上。”
插秧的时候,他很有话说。他还背五代梁时的契此和尚《插秧诗》:
手把青秧插满田,
低头便见水中天。
心里清净方为道,
退步原来是向前。
平时,他是个寡言的人。插秧了,他就和我谈农事,谈他青年时期的生活。回家的路上,他还不忘告诫我:不认真,田也很难种好。凡事怕认真,一旦认真了,难事就不难了,所以不要畏难。
夏风从河面涌来,一阵阵,夹裹着蝉声。吱呀吱呀,蝉声又亮又脆,从田野中央的柳树林滚过来,聒噪,突显了田野无边的沉寂和阔大。
冗繁的夏季,突然来了几场雨。雨是阵雨,雨势却猛烈,从山巅俯冲而下。哦,大暑不约而至。太阳恩慈,照拂万物生灵。稻谷黄熟。父亲早早把打谷机背到田里,收割稻子。他是一个气力比较小的人,背百余米,就歇一下脚。他的双脚稳稳叉开,打谷机撑在地上,扣住了他整个身子。在身后,看不到他。打谷机在走动,稻田在走动,山峦在走动。
新谷出新米。新米煮粥,也许是世界上最好喝的粥。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米入锅,水烧沸,猛火舔着灶膛,水翻出白泡,也翻腾着新米。米白白的,如雪粒散在荷叶之上。沸水腾起的蒸汽,萦绕着房梁。火是那么贪婪,画眉在梨树上叫得热烈。水化为白色,慢慢变得浓稠,变成了米汤。粥盛在蓝边碗里,一下子安静了。粥散发出浓烈的阳光之气、田野的清新之气、南方的野草之气。喝一碗粥,如同吸进了田野的精气。即使是冷粥,也自有无穷妙处。无论多燥热的暑天,喝一碗冷粥下去,浑身清凉。
20世纪末,南方种植水稻,一年两季。早稻米叫早籼米,也叫早米。晚稻米叫长米,也叫仙米。南方以南的亚热带,一年可种植三季水稻:早稻、中稻、晚稻。早米熬粥,晚米煮饭。我们日常食用的大米,是籼米,不常食用的大米还有粳米、糯米。
霜降和清明这两个时节,是酿酒最佳时间。气温在18℃~22℃,粮食发酵均匀,出酒率高,口感更绵柔。父亲是舍不得浪费酒的人,酒滴在桌上,他也要吸。他说,酒是粮食造的,浪费了酒就是浪费粮食,浪费粮食就是造孽。
30多年了,父亲坚持喝自己酿的谷酒,一餐喝小半杯。酒杯喝空了,摸起碗,盛大碗饭,吃得津津有味。他说,白米饭好,满口饭香,百吃不厌。
有一天,我陪父亲喝酒。他问我:“你知道什么是世界上最重的东西吗?”
他常常问我一些奇怪的问题。我当然不会按照金属元素密度回答他。这类似于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其实没有标准答案,答案因人而异。他问的每一个问题,也是他对生活的一个回答。我笑着看着他。他说:“你回答不出来了吧。”
“其实,答案很简单。世界上最重的东西,是米。”父亲说。
我佯装很惊讶,说:“为什么是米啊?钱也重,钱多压死人。”
父亲开怀大笑,笑得像个孩子,说:“你看看啊,从一粒稻种开始,变为一粒米,要经过两季,要保育、抚育,要收割、翻晒,要耕耖、灭虫,要车水、除稗,不是日晒就是雨淋。米缸假如缺了米的话,全家人心慌。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米,就是根本。”
我母亲就笑父亲,说:“一粒米也讲出这么多道理。”
父亲已87岁,那块田也还种着。在21世纪初,他就改种一季稻了,收出来的稻子怎么吃也吃不完。他请人翻耕、插秧,请收割机收割。他下不了田。他舍不得荒了那块田。他说:“可以亏待自己,也不能亏待养活了一家人的田,不能让自己的田长草。”
现在是晚春,在异乡,毛茛花开遍了田埂,野樱花开白了矮山冈。望着泱泱水田,望着那个抛撒谷种的育秧人,我的眼睛一下子迷蒙了。似乎育秧人就是我的父亲,也是你的父亲。
没有什么东西比米更珍贵,没有什么东西比米更淳朴。如同双亲。
(杨乐摘自《意林·原创版》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