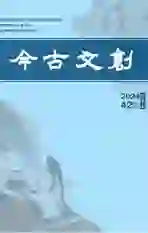非洲流散文学的体认翻译学研究
2024-11-21梁硕盈李慧钰蓝秋榆

【摘要】本文在体认翻译学视角下,利用概念整合理论中概念空间对应与空缺的四种要素关系所形成的镜像直译型、单域补充型、融合折中型和镜像互译型翻译方式,对诺贝尔奖得主——非洲流散文学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的《海边》进行译例分析。本文关注点为译文中体认过程的“同”与“异”以及对译者翻译方式的心理分析,针对文学翻译时的文化异同,以《海边》为例,依据体认翻译学的概念整合理论,解决文学翻译方式的选择问题,揭示体认翻译的策略选择规律,丰富译者在面对不同文化与文学时的翻译方式,从而为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交流贡献力量。
【关键词】体认翻译学;非洲流散文学;古尔纳;《海边》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2-0103-05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2.028
基金项目:广东工业大学2024年创新创业项目“非洲流散文学的体认翻译学研究”(项目编号:xi2024118450796) 和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3年度一般项目“《西游记》英译本的文化形象嬗变与国际传播研究”(项目编号:GD23CWY08)的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随着时代进步,中国翻译研究也在不断发展,如今翻译界越发注重在忠实传达的基础上,用多样化的手法进行翻译,以便于读者理解,迎合翻译需求。四川外国语大学王寅教授的最新翻译理论——体认翻译学,便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本文将采用体认翻译学视角下的概念整合理论,对非洲流散文学《海边》进行原文与中译本的对比研究,旨在扩大翻译认识的视角,丰富文学翻译策略的选择。非洲流散文学是指被迫流亡或自愿流离失所的非洲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非洲流散文学体现了非洲的文化和历史的独特性,也体现了全球化下非洲文化的变化,反映了非洲殖民文化的真实背景。2021年非洲作家古尔纳的作品获得了诺贝尔奖,使得人们重新认识到非洲文学的重要性和意义,非洲文学在世界上的地位虽逐渐上升,但对此的研究仍处于边缘地位,对非洲流散文学的研究较少。为促进中非文化交流,建立中非友好和谐关系,本文选取了古尔纳的经典小说《海边》进行翻译分析,研究非洲流散文学翻译的体认方式,目的在于通过分析具体翻译例子,丰富体认翻译学与概念整合理论的应用场域,为翻译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二、体认翻译学与概念整合理论
(一)体认翻译学
体认翻译学是一门由“认知翻译学”修补而来的新兴译学范式,是体认语言学(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ECL)的最新发展成果。[1]体认语言学由王寅教授于2014年在“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体认语言学”一文中首次提出,是对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CL)的本土化处理,其目的是修补认知语言学的不足,突出认知语言学强调与客观世界进行互动体验的特点,与乔姆斯基主张的转换生成语言学相区分。
“体认语言学”中的体认取自“互动体验、认知加工”八字。[3]“体”彰显人们通过现实世界的互动体验获取感性认识,强调唯物性与客观性;“认”体现人们经过心智运作将感性认识抽象为理性认识的过程,体现人的主观性。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因此,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为:现实——认知——语言,这一原则体现了20世纪以来语言学革命的渐进式发展历史。[2]
据此,体认翻译学的权威定义为:翻译是一种基于多重互动的体认活动,译者在透彻理解原文语篇所表达的有关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中各类意义的基础上,运用多种体认方式将这些意义映射进译入语,基于创造性模仿机制将这些意义建构和转述出来。[3]体认翻译学强调翻译是一种体认活动,必须透过表层的语言分析其背后的体认机制,翻译之“同”皆因较为客观的“互动体验”所致,翻译之“异”则产生自较为主观的“认知加工”。[4]
(二)概念整合与翻译的体认过程研究
王寅从认知语言学家福康涅和特纳于20世纪80—90年代提出的“概念整合理论”中得到启发,将其与体认翻译学相结合,进行了理论上的修补,并尝试用修补后的理论运用于体认翻译的分析当中。概念整合理论主要涉及四个空间:两个“输入空间”(input space)、一个“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和一个“融合空间”(blended space)。体认主体从两个输入空间选择性提取信息。由于类属空间包括两个输入空间所共有的轮廓性结构(即组织框架),所以在类属空间内,两输入空间信息可进行对应性映射,取得对应性匹配的概念要素。概念要素在融合空间中通过“并构、完善、精细化”的处理后,能够形成带有创新性的新概念或要素。
如将原文作者视为输入空间1,称为“作者空间”;将译者视为输入空间2(含语言能力、背景知识),称为“译者空间”,那么翻译过程就是译者将作者空间的要素进行概念解构,与译者空间内的要素不断进行映射、融合后再通过“并构、完善、精细化”的方式在融合空间内产出译文的过程。[5]
虽然概念整合理论能较好地解释翻译中的诸多现象,但却并未提及要素空缺的情况。因此,王寅提出四种情况对其进行修补。[4]
(1)a→a’ b→b’ (2)c→? d→?
(3)c+d→f (4)e→g
图示如下[4]:
(1)a→a’ b→b’
输入空间1中的a、b在输入空间2中有对应要素a’和b’,可直接进行镜像映射。在翻译过程中则体现为,两种语言中拥有对应的词语或句子且组织框架即意义相仿,可直接进行匹配。[4]我们可称这种对应关系为“镜像直译型”。
(2)c→? d→?
图2中c、d点没有经过映射就直接被映射入了融合空间(即译文空间),这是因为作者空间内的某一元素在译者空间内缺乏对应元素,因此,译者必须通过新创词语或增加词语保证句子结构和内容的完整性。[4]我们可称这种关系为“单域补充型”。
(3)c+d→f
两个输入空间中的c与d拥有部分对应的组织框架,因此在映射入融合空间之后,译者采用折中法对其对应概念元素进行完善和精细化处理,以达到意义上的平衡。这一情况在译文中用f来表示。f不一定是一个居中点,可能离输入空间1 (作者) 近点,也可能离输入空间 2 (译者)近点。[4]我们称这种翻译类型为“融合折中型”。
(4)e→g
输入空间1中的e(无连线黑点)缺少对应元素,但译者却能激活产生相同或近似的意象图式和认知框架,从而建立某种关联,被映射入融合空间后可用g(无连线黑点)将其表达出来。[4]这种情况在习语与俚语的翻译中常见。如“雨后春笋”这一整体意象在英语语言中缺少对应元素,但译者却能激活其认知框架,将雨后冒芽的笋与雨后出现的蘑菇进行对应,从而翻译为“spring up like mushroom”。我们可以称之为“平行互译型”。
通过体认翻译学对概念整合理论所做的修补,我们完善了概念整合理论中要素空缺的情况,扩大了概念整合理论的解释范围。但这几项修补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融合互译”的解释分析过于概括,缺少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使得折中情况的判定过于主观化,导致从具体角度判断折中程度的过程存在困难。其次,第四种情况目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针对俚语习语翻译,尚未能扩大到其他日常用语的研究中。
三、《海边》中的体认翻译研究
《海边》是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古尔纳的代表作,讲述了20世纪从桑给巴尔到英国寻求避难的中年人萨利赫·奥马尔的遭遇。桑给巴尔曾是印度洋贸易史上的一颗明珠,然而西方殖民却使得这一帝国迅速衰败。萨利赫·奥马尔作为这一场殖民的亲历者,少年时曾同时接受过当地文化的熏陶与英国的教育,后远走英国避难。此书以奥马尔的第一人称为视角,以个人和家族的经历为切入点,从流散者的角度进行叙事,让读者从字里行间感受英国殖民对桑给巴尔带来的影响。通过对译者黄协安翻译的《海边》进行体认翻译研究,不仅可以直观地了解流散者对殖民的态度与感受,还能剖析中国译者对非洲流散文学的认识与看法。
(一)a→a’ b→b’
这一类型的关系属于镜像直译型,两类元素能够直接相互映射。笔者认为,文学作品中的“直译”并非指字面意义上的逐词翻译,而是指通过直接、不加修饰的手法来呈现小说原文的内容和精神内核,是小说中对人物对话和内心独白的直接呈现。
(1)原文:“I can never forget the past,”said Omar,his voice heavy with emotion.“The memories of what happened are too painful.”
译文:“我永远不会忘记过去,”奥马尔说,他的声音充满了感情。“对发生的事情的回忆太痛苦了。”
原文:“Omar felt a pang of homesickness as he gazed out at the sea.He longed for the familiar sights and sounds of his homeland,the smell of the sea breeze and the taste of his mother's cooking.”
译文:当奥马尔凝视着大海时,他感到一阵思乡之痛。他渴望家乡熟悉的景象和声音,渴望海风的气味和母亲做的菜的味道。”
这些直接引语和内心独白,没有多余的修饰或解释,直接展现了讲述者本身对过去的深刻情感和记忆,比如:奥马尔的声音“沉重”,说明他谈及的是一个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且情感负担深重的话题;还明确表示自己“永远不能忘记过去”,这反映了他对过去事件的深刻记忆和对那些经历的情感投入;接着他进一步解释,“那些发生的记忆太痛苦了”,这直接体现了他对过去事件的痛苦感受。这种方式与“直译”中的直接传达原文内容的方式有相似之处,两者都强调了对原文的直接、不加修饰地呈现。
从另一个方面看,原文不仅是一个情感的表达,还体现了“体验”与“认知”在概念整合过程中的相互作用。首先,从“体验”的角度来看,奥马尔的话语直接传达了他对过去的深刻感受。“永远不能忘记过去”和“那些发生的记忆太痛苦了”都是基于译者个人对讲述者经历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是直接的、感性的,译者不需要通过逻辑推理或分析就能直接翻译出来,被读者所感知和理解。在这里,“体”表现为译者感同身受,对讲述者过去痛苦记忆的直观感受和情绪反应;其次,从“认知”的角度来看,译者的话语也反映了他对讲述者过去经历的理性认识和评价,他能够清晰地表达出主体对过去的记忆是“痛苦”的,这表明他即使在情感上没有经历过这一事件,但在认知层译者面对这些事件时能够进行客观评价和反思。这种认知是间接的、理性的,涉及译者对经验的解释、归纳和推理。在这个例子中,“认”体现为译者对过去事件的理性思考和记忆重构。
(二)c→? d→?
这一类型为单域补充型,作者空间的元素未能在译者空间内直接找到对应元素。这种类型包括借入和增译。
借入为当源语言的内容在翻译过程中找不到与之对应的元素表达时,译者对通用翻译进行参考,或进行新创词语。
借入:在《海边》中,也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如Shyakh——谢赫、 Kofia——圆筒帽子、 Imam——伊玛目等,这些词语在中文中都没有对应的存在和表达方式,因此译者参考了其他译本里使用过的表达进行翻译。
增译:
(1)原文:It was as if they had remade us,and in ways that we no longer had any recourse but to accept,so complete and well-fitting was the story they told about us.
译文:他们俨然重塑了我们的前世今生,也许,我们只能接受,关于我们的故事,他们讲述得非常完整,非常到位。
在此句的翻译中,译者增译了“前世今生”,使得该句的句意更加清晰完整。根据前文情节,书中主人公奥马尔被选入英式学校,在英式教育体系下接受世界历史教学。全世界各民族面对相同或相似的外部世界,又有相同的身体结构和器官功能,这决定了全世界人民的思维必有“同处”。[6]作者出于“体”的普遍性,能够感受到主人公对他国视角下本国历史叙述的惊诧与震撼,因此能够理解此处重塑的是主人公国家的历史。奥马尔的母国在英国殖民侵略前,是一个根据季风洋流变化发展商业的非洲小国,然而在遭受殖民后,他们的国家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译者根据已有认知,用“前世今生”来概括其发展历史,突出桑给巴尔的国家命运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体现了不同民族间语言表达的“异”。译者通过对此处主人公心理活动的生动翻译,表现出了被侵略国国民接受西方教育时的“震撼感”。与此同时,译者并没有根据“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选用带有强烈消极情感色彩的词语对其进行翻译,这表明主人公对西方教育并不完全持反对态度,体现了被殖民者对殖民统治极其复杂的情感态度。
(2)原文:He stood facing the congregation until the first line had formed behind him across the width of the mosque,then he turned and walked into the qibla and began.
译文:他面对着教众站着,接着,教众走到他的身后排成很长的一排,再接着,他转身走进米哈拉布,面对基卜拉开始做祷告。
此处增译的“米哈拉布”指壁龛。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客观地还原了细节,增译的米哈拉布填补了由于文化差异导致的理解空白。同时,译者并没有将米哈拉布译为西方传统说法“壁龛”,而是直接采取音译的方式,这种语言表达层面上的“异”充分体现了中国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与包容。回归情节,此处为书中另一主人公拉蒂夫在英国回忆其父亲进行仪式的情景。仪式是承载文化记忆的媒介之一,而文化记忆建构了统一感、归属感。[7]拉蒂夫尽管离开母国多年,然而仍清楚深刻地记得家乡的宗教仪式,故土仍然构成了流散人群身份认同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三)c+d→f
在这种情况中,作者空间与译者空间内的元素具有一定的共性,因此在映射入融合空间之后,译者采用折中法对其进行完善和精细化处理,以达到表意的平衡,属于融合折中型。
(1)原文:...ready for the blow when it came,rather than dozy and dopy and relaxed and then churned up when it arrived.
译文:做好迎接打击的准备,不要昏昏欲睡、昏昏沉沉、松松垮垮,不至于到时候猝不及防,一击即溃。
其中,“churned up”对应的“猝不及防,一击即溃”为折中的一种翻译方式。churn原意为“剧烈搅动;心烦意乱”等,churn up意思则为搅动,此处译者对词语意思加入了个人理解,采取了折中的翻译。此处前文大致内容为,一名非洲难民逃来英国,难民接待者向“我”(书中主人公拉蒂夫)求助翻译,并电话留言告诉“我”不必为和老家脱离关系而感到羞愧;后文中“我”打电话过去确认详情,并感到“我”与他们(此处为英国人)是同一阵营的。译者认识到 “我”作为一名从非洲前往英国的异化流散者,“我”在面对身份转换以及家乡人的会面时,存在着复杂的心境和身份认同的转变,“我”试图脱离非洲的身份和文化,对英国感到向往和认同,但对于这种脱离,“我”内心还存在着背叛祖国般的忏悔感,这正是非洲流散人民所面临的困境。此外,译者在“相同”体验的现实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认知加工,如译者基于曾经听到某些消息后,心境被剧烈搅动,情绪突然爆发的经历,从而进行了“异”的翻译,更生动形象地表现了这种心情的强烈感。
(2)原文:They did not have the obsessive need of them that of my European customers had–to acquire the world’s beautiful things so they could take them home and possess them...
译文:他们不像我的欧洲顾客那样志在必得,欧洲人看到好东西就一定要把他们带回家去占为己有……
这句话中,译者将“the obsessive need”译为“志在必得”。在此处,书中主人公奥马尔正在经营一家家具店,承接打造、回收家具等业务。他收来的古董家具虽然不太受到本地人的欢迎,但却获得了欧洲游客和英国殖民者的青睐。这句话正是在将桑给巴尔人与欧洲人进行比较。“obsessive need”原指“对某事物强烈的、难以控制的欲望”,而译者却将其译为“志在必得”,不仅体现了欧洲殖民者想要占据外来事物的强烈渴望,还隐含理直气壮感,生动地展现了欧洲殖民者的强盗心理。译者之所以选择这一措辞,正是其基于自身民族经历的“体”而对原文内容进行阐发的结果。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中国也曾遭受欧洲殖民者无情的烧杀抢掠,至今仍有大量文物流落海外。译者融通中非历史,与书中主人公产生共情,不仅完美诠释了原意,揭露了欧洲殖民者的丑恶嘴脸,更展现了中华文明与非洲文明对殖民行为的痛恨与不满。
(四)e→g
在这种情况中,译者通过激活相同或近似的意象图式和认知框架,将作者空间与译者空间关联起来,用译者空间的独特表达方式将作者空间的表达呈现出来,可称为“平行互译型”。
(1)原文:“It was a fabulous and unrepeatable moment,
as if I too had stumbled across an unimagined and unexpected continent.”
译文:这是一个如梦如幻的时刻,就像我也偶然发现了一个无法想象和意想不到的大陆。
首先,原文通过“fabulous”和“unrepeatable”这两个形容词描绘了一个非凡且不可复制的瞬间,同时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as if I too had stumbled across an unimagined and unexpected continent”,即仿佛自己意外地发现了一个从未想象过、完全出乎意料的“大陆”。这个“大陆”不仅代表了物理上的新领域,也象征着心理、情感或认知上的新境界。然后,译者选择了“如梦如幻”这个四字成语来翻译这个句子。这个成语非常巧妙地将原文中的多重含义融合在了一起。译者通过“如梦”暗示了这种经历像梦一样美丽、不真实,而“如幻”则加强了这种虚幻、不可捉摸的感觉。“如梦如幻”这个成语也带有一种短暂、稍纵即逝的意味,与原文中的“unrepeatable”(不可复制)相呼应。在这里,“互译”技巧的运用主要体现在译者将原文中的具体比喻(一个意外发现的新大陆)转化为了一种更加抽象、更具象征意义的表达(如梦如幻)。这种转化不仅保留了原文的意境和美感,而且使得译文更加符合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偏好。通过“互译”,译者成功地将原文中的情感、意象和文化内涵传递给了中文读者。
从体验的角度来看,译者传达了对原文中人物对那个特殊瞬间的直观感受。原文中的“fabulous and unrepeatable moment”表达了人物对这一瞬间的独特体验,非凡美好且不可复制,仿佛是一场梦境。译者使用“如梦如幻”恰好捕捉到了这种梦幻般的体验,使读者能够直接感受到人物内心的激动和惊喜。
从认知的角度来看,“如梦如幻”也反映了译者对这一瞬间的深层次理解和评价。原文中的比喻“as if I too had stumbled across an unimagined and unexpected continent”不仅是对那个瞬间的具象描述,更是对人物内心认知的展现。这个比喻暗示了人物在那一刻经历了一种认知上的突破,仿佛发现了新的领域或境界。译者通过“如梦如幻”这一表达,将人物内心的这种认知上的变化也传达给了读者,使读者能够理解到人物对那个瞬间的深刻认识和珍视。
综上所述,“如梦如幻”这一翻译不仅捕捉了译者对那个瞬间的直接体验,也传达了译者对这一瞬间的深层次理解和评价。它体现了译者对原文的深入理解和对人物体验的敏锐捕捉,同时也展示了译者通过翻译来传递人物体认的高超技巧。
四、结语
通过对非洲流散文学著作《海边》进行体认分析,集中探讨了跨国难民的身份问题。异邦流散对于流散者来说,不仅仅意味地理空间上的变化,更意味着对文化边界的跨越。[8]对于第三世界流散到第一世界的流散者来说,他们通常面临着自我认同、身份转换的问题。一方面,面对迥然不同的文化环境,流散者需要竭尽全力地融入新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在母国的经历、语言、宗教仪式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已构成了他们身份认同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深刻地影响他们。在这过程中,他们难免出现自我身份的矛盾,一方面对“背叛”母国感到愧疚,一方面对逐渐融入新文化感到欣喜。
另外,通过分析对难民心理进行描写的翻译,发现被殖民者对于殖民者存在极其复杂的情感态度。对于欧洲统治者曾经在他们国家实施的侵略,以及现在作为接纳国对他们展现的种族歧视和排斥,非洲流散人民表现出不喜与鄙夷,然而,他们也并不完全否认殖民国对其产生的有利影响,这打破了以往欧洲殖民者和非洲被殖民者间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情形,展现了历史的复杂性。[9]
通过体认翻译学,我们发现中国译者在展现非洲流散人民心理状况方面做到了客观与真实,同时还发掘了非洲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合拍共振之处[10],以中华文化的包容和尊重,生动贴切的翻译对非洲流散人民的状况表达了深刻的共情。这样客观公正的中国视角,为世界了解非洲流散文学提供了中国声音与中国方案,为构建中国非洲文学学提供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祝朝伟.体认翻译学:一种新范式的兴起[J].中国翻译,2023,44(04):29-38+192.
[2]王寅.20世纪三场语言学革命——体认语言学之学术前沿[J].外国语文研究,2015,1(02):2-11.
[3]王寅.体认翻译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J].中国翻译,2021,42(03):43-49+191.
[4]王寅.概念整合理论的修补与翻译的体认过程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20,52(05):749-760+801.
[5]王斌.概念整合与翻译[J].中国翻译,2001,(03):17-20.
[6]王寅.体认翻译学视野下的“映射”与“创仿”[J].中国外语,2020,17(05):37-44.
[7]阿斯曼.宗教与文化记忆[M].黄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8]高文惠.古尔纳《海边》中跨国难民的身份叙事[J].外国文学研究,2022,44(05):31-42.
[9]张峰.后殖民文学中的记忆、语言、异质性与地方性——古尔纳的创作与批评思想解析[J].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2,(02):5-17.
[10]孙毅,蔡圣勤.“中国非洲文学学与学术研究的理论创新”笔谈[J].外国语文研究,2022,8(06):1-10.
作者简介:
梁硕盈,女,汉族,广东东莞人,广东工业大学本科生,研究方向:翻译学。(指导教师:欧阳东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