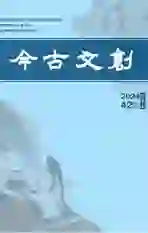生态批评视域下米歇尔·图尼埃的自然观
2024-11-21曹聪
【摘要】“自然”主题始终贯穿于法国作家米歇尔·图尼埃的小说、散文创作之中,体现了作家对生态问题的关注。本文从生态批评视角对图尼埃的作品进行解读,对作家的自然观进行溯源,并阐明作家对物质世界的赞颂、对都市生态环境的批判,揭示作家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幸福观和矛盾的生态审美观。
【关键词】米歇尔·图尼埃;生态批评;自然观
【中图分类号】I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2-0036-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2.011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青年项目“法国作家图尼埃的自然生态观研究”(项目编号:19Q157)。
法国“新寓言派”作家米歇尔·图尼埃(以下简称图尼埃)善于重塑神话故事,并将各种寓言征兆与哲学思辨融入小说创作;同时,他还高度关注人类文明发展,在作品中探究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日益恶化的环境危机和人类生存危机,生态批评的浪潮逐渐兴起与勃发,而几乎同时,图尼埃的作品开始涉及环境污染、消费社会、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现代主题。作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常被视作生态学神话,因g8+/CgUMY7MywPEyDxbVHC8GKBnhyKCldh64/iIDWAw=此中外研究者对图尼埃生态思想的论述多聚焦于此,而对其短篇小说乃至散文作品中传递的生态信息重视不够。本文将对图尼埃生态自然观的形成进行溯源,并梳理其小说、散文中体现的生态意图,揭示作家对现代人生态困境的伦理关怀。
一、作家生态自然观之溯源
图尼埃曾在自传《圣灵风》中谈到自己的创作理想:“我试图成为一个真正的小说家,写出充满木炭香味、秋天蘑菇味和动物的湿毛皮味道的故事,但这些故事应该秘密地由本体论和物质逻辑所驱动。”[1]174 这句话深刻揭示了作家对小说创作的独特追求和美学理念,一方面力求“以物质世界原本的方式描绘这个物质世界”,通过刻画生活中的真实细节激发读者的感官体验;另一方面,故事与自然世界紧密相连,使读者能够在品味各种“味道”的过程中重拾对自然的尊重与爱;最后,这些故事必须隐含哲学思辨、遵循物质逻辑,最终构建一个真实、生动且触动人心的文本空间。究其根源,图尼埃的这一理想既根植于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创作倾向,也体现了一种源于童年经历和教育背景的、对环境和生态的直觉性感知。
1924年,米歇尔·图尼埃出生在巴黎一个深受德语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家庭,外祖父是勃艮第的一名药剂师、植物学家。少年时他受到外祖父启发,培养了对植物的浓厚兴趣,童年生境不仅塑造了作家最初的价值观,也极大影响了作家对物质世界的呈现方式。作家在《圣灵风》中详细描述了童年时期流连于外祖父所开药房的场景——他时常沉浸在一种药剂的复杂气味之中,并沉迷于各式药瓶标签上的奇怪文字,这种有关视觉和嗅觉的双重启迪,就如同普鲁斯特笔下的玛德莲蛋糕一样,萦绕心头、反复回味,成为作家感知物质世界丰富性的第一步。除此之外,外祖父还时常教授图尼埃各种植物学知识:“我们常去市里的植物园转悠,他会一边用拐杖头指着一边用勃艮第口音说出它们的名字:互叶金腰、常绿牛舌草、水苏。”[1]80 作者由此燃起的对植物的好奇心贯穿于文本创作之中:在散文集《思想之镜》中对桤木、柳树药用价值的论述,对椴树、仙人掌、牛蒡播种方式的赞叹;在《庆祝》中对百合、黄杨木宗教属性的思考,对欧石楠、荆棘等“有害”植物的辩护。图尼埃通过将植物学知识融入散文创作,构建了一个既富有诗意又充满理性的文学世界。这种科学与文学的融合,不仅使他的作品更加生动有趣,也引导读者以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方式去理解和思考自然。
图尼埃的写作风格深受法国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流派的影响,他自称“左拉和都德的学生”,并认为巴尔扎克、司汤达和福楼拜才是真正的小说家。此外,图尼埃还多次谈及自己的哲学思想导师们,其中列维·施特劳斯无疑对作家的第一部小说《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影响至深。图尼埃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施特劳斯人种学课程带给自己的启示:“他(列维-斯特劳斯)教给我,没有所谓的野蛮人。在西方文明中,对与我相异的他者的否定有三种:首先是古希腊人对蛮族的否定,然后是基督徒对异教徒的否定,最后是西方文明对野蛮人的否定。这是三个必须消除的可恶的概念……有若干个文明,但没有‘唯一’的文明。”[2]因此,图尼埃在创作《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时的目标之一就是揭示西方长期以来的一大思想谬误:文明没有优劣之分,进步的概念是相对的。这些所谓的“野蛮人”为了在脆弱的生态系统中生存与发展,必须竭尽全力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因此在小说中,作家颠覆了礼拜五与鲁滨逊的关系,礼拜五不再是迪福殖民叙事中的奴仆形象,而是作为鲁滨逊的“精神导师”,引导其抛弃人类中心主义和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从反生态主义者角色转变为与小岛自然生态系统交融一体的“自然本原一分子”。可见,作家的教育背景为其生态书写注入了哲学思辨的文本动能。
二、作家生态自然观之体现
(一)赞美物质世界
图尼埃的文本空间充满丰富的自然意向,作家对各种动植物、地理景观(沙漠、森林、岛屿)和自然现象(潮汐、季节变幻、大气现象)的描绘体现了作家对物质世界的浓厚兴趣以及敏锐的感知力。同时,图尼埃笔下的世界也充满对“物质性”的尊重,其中每一棵杂草、每一只野鸭都叙述着自身的意义,与周围的一切共同编织成宇宙间复杂而精细的网络。图尼埃发表于后期的散文集《庆祝》最为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所收录的八十二篇文章中,物质主题超过全书的三分之一。从四足动物的步态到退潮揭示的海滩秘密,从夜间刺猬的漫步到树木之间的仇恨,作家邀请读者进入一个不那么为人所熟知的物质场域,借此赞美世界的绚丽多彩。值得注意的是,图尼埃对物质世界的赞美并不流于表面,而是通过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肯定物质的主体性和生成性、强调物质之间的内在互动来揭示一个更为广阔、深刻且相互依存的自然图景。
在《为杂草辩护和阐释》一文中,作家描绘了园丁主宰花园的场景:“至高无上的园丁区分着好的植物和杂草。然后被选中的成群结队进入天堂,被摒弃的滚入地狱,玫瑰、百合花和大丽花在花坛里盛开,而海绿、狗牙根则被扔进堆肥里藏在篱笆后边。”[3]21园丁对花园中植物进行的“好、坏”二元划分反映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下,人类自视为自然界的统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利益来评判和改造自然。作家指出,这种修剪工作实际上是“将一片草地变成一块无懈可击、均匀的贫瘠地毯”[3]22,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人为干预和简化,会导致生物多样性的消逝。此外,文章还提到了人们对自然的另一种错误看法,即认为不再耕种的田地和森林砍伐区会荒漠化。从物质生态批评的角度看,物质具有“施事能力”,物质的真正维度不是静态、被动的存在,而是“创造性的生成过程”[4]77,因此,不再耕种的田地和森林砍伐区不仅不会退化为荒漠,反而会蜕变为“布满欧石楠、荆棘、灌木丛、矮树林的荒野”[3]24,成为野生动物的天堂。正是因为肯定了物质的主体性和生成性,图尼埃才必须为杂草和杂草丛生的“荒野”辩护,并提醒读者改变对自然居高临下的看法,无论是否对人类有益,它们都是真正的自然的一部分。
为了突出表现物质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图尼埃采用了“植物拟人”的写作手法。在《树与森林》中,作家与树实现了想象式共情:“树是极端个人主义的、孤僻的、自私的。我就这样理解了从森林中渗透出的焦虑。森林,就像是一个集中营里的强制混居。所有这些树木挤在一起,彼此受苦并相互憎恨。森林中的空气充满了这种植物间的仇恨。”[3]16图尼埃笔下的树和森林不是静止的、被动的、毫无灵魂的物质存在,而是像人一样拥有个性和情感,具有强烈的感知力。另外,拟人化的描写也使得树与风、阳光之间的互动变得富有诗意,唤起人们对自然生发出母性情感:“树木不能忍受森林,因为它需要风和阳光。它直接吸吮着风和阳光这两只宇宙的乳房。”[3]16可见,这种拟人化的写作手法有助于揭示人类主体与非人类主体之间的同构性。
图尼埃有关物质间内在互动的描写并不仅限于植物与环境,在《鸭子的肖像》一文中,图尼埃还生动再现了生物与景观间的相互依存:“每种景观都呼唤着其特有的动物轮廓。野兔在开阔的留茬地阴影中奔逃,狍子在树林边缘警觉地倾听,山鹑从新耕的田埂上发出响亮的鸣叫飞起,野猪则在泥潭中尽情打滚。但是,没有什么能比得上绿头鸭和沼泽之间幸福的结合和完美的适应。”[3]45这一有关生态整体性的描述不仅体现了动物对生存空间的依赖和利用,也反映了它们与环境之间潜在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图尼埃笔下的植物和动物都是通过与环境进行持续深入的内在互动维持住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并最终实现和谐共生。
(二)批判城市生态环境
图尼埃对城市生态环境抱持彻底的负面态度,在为数不多有关城市的描写中,作家将其塑造为一个被实用性、功能性绑架的权力空间。图尼埃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家乡巴黎:“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城市对幸福生活的艺术更陌生,更彻底地不热情好客,或者更愚蠢地让树木为汽车牺牲。生在巴黎,我就好像不出生在任何地方,如同天上掉下来的流星一般……巴黎满是为事业而来的外省人,一旦时机到了就赶紧逃离……巴黎像一个泵一样吸引又排斥着外省的法国人。”[1]19作家从两个层面批判巴黎城市发展的疴疾,巴黎的问题也是当代都市集体面临的问题。当代都市一方面通过砍伐树木、牺牲自然环境不断让渡出居民幸福栖居的权利,让位于全球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没有建立起一种适用于本地居民和城市移民的文化融合机制,因此城市生活既造成了人与自然的疏离,也导致了人的文化身份的消解。
城市化发展也激发了作家关于人类世界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反思,他不止一次提到人类对地球环境的威胁:“我们最近才知道,自然界因人类害虫的大量繁殖而面临死亡的威胁。”[6]74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又将人类与地球的关系比作杀死宿主的寄生虫:“很显然,甲虫和愚蠢的人类一样,是唯一会毁灭它所赖以生存的植物的动物。”[3]154图尼埃通过“害虫”的比喻对人类这一生态危机的肇始者进行强烈批判,也提醒人们重新审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从对环境的寄生走向与自然的共生。
与作家的散文创作不同,图尼埃的小说很少透露出明确的生态信息,短篇小说《小布塞出走》和《铃兰空地》是为数不多的例外。两篇小说都提到了城市现代化发展对环境的破坏,尤其是高速公路的延伸导致树木和森林的消失。在《小布塞出走》中,小布塞的父亲是巴黎伐木工工长,对现代生活的向往使他决意离开乡下小屋、入住城市高楼。他同时还骄傲于自己的职业,认为伐木工们为巴黎的城市发展扫清了障碍:“巴黎将会出现由高速公路和立交桥构成的错综复杂的交通网,成千上万的车辆将以每小时一百公里的速度驶往四面八方。”[5]83 类似的情节也出现在《铃兰空地》中,半挂车司机比埃尔疑惑为何离高速公路如此之近的休息区名叫铃兰空地,却得到这样的答复:“原来是一片树林。到了春天开满铃兰花。高速公路一修,树林就不见了。被高速公路吃了,吞下去了,就像发生一场地震似的。于是铃兰花也消灭了!”[5]53图尼埃将高速公路比作怪兽,吞噬了树林和鲜花,而现代性也在吞噬人性,导致人之存在的疏离化。那么,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人是否还有可能逃离城市并重新栖居?在《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结尾处,鲁滨逊最终没有选择离开荒岛,而是过着远离人类文明、与自然元素相伴的生活。这一结局带有明显的神话色彩和乌托邦性质,于是作家又在随后发表的短篇《鲁滨逊·克鲁索的结局》中为主人公安排了另外一个结局。重返故乡的鲁滨逊无法忍耐城市生活中物欲文化对精神的侵蚀,在礼拜五失踪后,鲁滨逊也重新踏上寻找“希望岛”的路途,但经年累月的努力都是徒劳,直到一个老舵手说道:“你那个荒岛肯定一直在那里。甚至我可以担保:那个岛你已经找到……在它面前你经过有十次也说不定。可是你认不出了。”[5]79小说结尾极具寓言性,“希望岛”作为自然的象征,不再准许异化之人的侵入,现代人终究难以找寻到安放心灵之所。
(三)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幸福观
图尼埃在作品中表现出一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幸福观,这种融入体现在身体和心灵两个维度,即身体的积极参与和想象力的全情投入。
人类主体与非人类主体虽然无法做到物质性的融入,却可以进行主体间的靠近,通过两者的亲密互动实现人类感官的充盈和心灵的澄明。在《马》一文中,作家写道:“对于孩子来说,对马的爱是从与巨大、温暖、肌肉发达、散发着汗水和马粪的身体直接接触开始的,他们愉悦地将自己的脸颊贴在马身上,一直到脚趾。当然,这必须是骣骑(不带马鞍骑马),孩子也应该尽可能地赤裸,因为他的身体与马的身体之间不能有任何隔阂。”[3]30 与马赤裸相对的场景奇怪而温馨,既体现了一种万物平等的观念,也揭示了一种人类冲破一切阻隔与“自然之物”无限接近的愿望。对于图尼埃来说,人类必须用皮肤的纹理去感受自然的纹理,才能获得最大程度的满足。正因如此,当他处于退潮的海滩时,坚持裸足行走:“我想在裸足下感受到这些海草、沙滩和卵石的触感,这些柔软的泥滩、颤动的水洼……重要的是行走,和那些滑入脚趾间的泥沙一起奔跑,尤其是那种裸露的生命的强烈味道……”[3]27可见,图尼埃与自然融合的幸福观反映出一种回归人类本真状态的倾向,这种倾向要求我们与自然万物建立一种最密切的关联和感应,形成一种超越主次、仆从的深刻关系。
除了人类肉身与自然的靠近,心灵的冥想同样能使人与自然实现精神上的同频共振。幻化成树的场景出现在图尼埃的多部小说之中,对植物的想象为主人公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在《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中,鲁滨逊“直接参与树木显然可见的机能活动,树伸出它千千万万手臂拥抱着空气,用它亿万只手指把空气紧紧搂抱在怀……绿叶,是树的肺,就是树的肺腑,所以,风是它的呼吸,鲁滨逊这样想着。他想象他自己的肺,也在体外张开来……”[7] 而在《小布塞出走》中,小布塞幻想自己变成一棵巨大的栗子树:“他悬浮在静止的蓝天中。突然,一阵风吹过,皮埃尔轻轻地叫了一声。他那成千上万的绿色翅膀在空中舞动。他的枝干轻轻摇摆,为人祝福。一扇阳光展开又关闭在其簇叶的海蓝色树影中。他快乐之极。”[5]94 鲁滨逊与小布塞都感受到自然活力的召唤,通过幻想自己与树交融获得心灵的慰藉,从倾听自然的言说到与自然共同言说,使得幸福感不再流于表面、转瞬即逝,而是根植于内心空间与宇宙空间的合一之中。
三、作家的生态审美观
图尼埃的生态审美观具有矛盾性:一方面,对人类清除杂草、厌弃沼泽行为的批判体现了作家对人类中心主义自然审美观的质疑,以及从主体性审美走向主体间性审美的尝试;另一方面,图尼埃对自然景观的欣赏仍受到欧洲传统审美观的影响,即“更喜欢修剪整齐的景观而非原始的自然”[8],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家的人本主义思想和等级观念。
图尼埃对杂草和沼泽的赞颂表明其有意抛弃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审美观,由以人为尺度审美转为以生态整体为尺度。由此,审美标准发生颠覆性改变,那些被人类社会厌弃的自然因素在作家笔下成了和谐有益的存在,“布满荆棘的荒野”被视作野生动物的天堂,危险、阴郁的沼泽转变为迷人的湿地形象。再者,为了更好地进行生态审美,人类必须与自然融为一体,建立主体间性。就像《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中的鲁滨逊,当他把小岛当作无生命的客体看待时,他看到的是小岛的荒蛮和无序,而当他最终与自然交融,才发现一个“生机勃勃、充满爱意”的小岛。
图尼埃虽然排斥城市生活,却并不主张人类退回以森林、荒野为代表的纯粹的自然之中,淳朴的乡村田园生活最能体现作家真实的生态理想。在《树与森林》中,图尼埃描绘了原始森林的可怖氛围:“我用我的所有感官和肌肤的每一个毛孔亲历了原始森林,感受到了它令人眩晕的密度、令人窒息的潮湿,以及突然打破寂静的可怕声音……在那里,我看到了某种地狱。”[3]15对作家来说,原始森林的压抑空间并不能带给人美的感受,而“只有单独种植才能培育出美丽的树,树的四周要有能够伸展开来的无限空间”。[3]15因此,美丽的自然只存在于森林公园和花园之中,是人类劳作的成果。作家的这一态度使人联想到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对“中间景观”的赞赏,“中间景观”处于“‘人造大都市’和‘大自然’两个端点之间”[9]106,比如农田、郊区、花园等都可被称作中间景观,它“看起来更加真实,更富有生活的气息,而且更像是生活的本来面目”[9]107。也许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来看,图尼埃的生态审美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这并不影响作家对人类面临的现实生态困境进行伦理关怀。
图尼埃的生态自然观极具前瞻性:作家对物质世界的赞美与物质生态批评的若干理念不谋而合,对城市生态环境的批判提醒人们重新审视自身发展模式,而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幸福观也与建立生态共同体的时代愿景遥相呼应。虽然作家并不致力于通过作品传递明确的生态立场,也无意政治介入,但他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体现了一种超越时代的生态主义敏感性。此外,图尼埃的生态书写也独树一帜,他将诗意的图像与征兆、神话相联系,将人类学与文学创作相联系,将生态叙事与人性探索相联系,避免了生态问题的表层书写,获得了哲学、神话学层面的文化深度,呈现给读者一个饱满、隽永的文学世界,极大地扩展了生态文学的艺术空间。
参考文献:
[1]Michel Tournier.Le Vent Paraclet[M].Paris:
Gallimard,1977.
[2]Michel Tournier.“Entretien avec Michel Tournier.”With Zhaoding Yang[J].Dalhousie French Studies,1998,42:58-149.
[3]Michel Tournier.Célébrations[M].Paris:Mercure de France,1999.
[4]Serenella Iovino,Serpil Oppermann.Material Ecocriticism:Materiality,Agency,and Models of Narrativity[J].Ecozone,vol.3,no.1,2012:75-91.
[5]米歇尔·图尼埃.皮埃尔或夜的秘密[M].柳鸣九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
[6]Michel Tournier.Le Miroir des idées[M].Paris: Gallimard,1996:74.
[7]米歇尔·图尼埃.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M].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184.
[8]Rachel Bouvet,Stéphanie Posthumus.Eco-and Geo-Approaches in French and Francophone Literary Studies:
Écocritique,écopoétique,géocritique,géopoétique[G]//
Handbook of Ecocriticism and Cultural Ecology.Berlin/Boston:de Gruyter,2016:404.
[9]宋秀葵.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生态文化思想研究[D].山东大学,2011.
作者简介:
曹聪,女,湖北襄阳人,湖北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当代法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