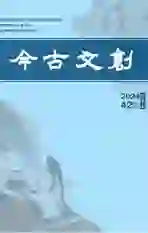浅析张爱玲《半生缘》中顾曼桢的角色悲剧性
2024-11-21郑珮
【摘要】《半生缘》是张爱玲创作的首部长篇小说,张爱玲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凄凉的笔调叙写了民国乱世的爱情故事。主人公顾曼桢是作品中最为让人同情的悲剧人物,张爱玲以细腻而尖锐的笔触和华丽阴郁的写作风格,塑造了顾曼桢这一形象。顾曼桢是时代的牺牲品,作为女性有对自己命运无可把握的无奈。本文试通过对作品《半生缘》的探究,进一步从特殊的时代背景、人物自身性格来探讨主人公顾曼桢命运的悲剧性。
【关键词】顾曼桢;悲凉;女性地位;人物悲剧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2-0023-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2.007
一、引言
张爱玲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女性悲剧意识尤为强烈。张爱玲笔下的这些女性的命运基本上都是不完美的,她们的命运都是不幸地经历了各种的人生悲剧[1]47。《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被金钱奴役,心理扭曲变态;小说《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在经历失败的婚姻之后,追求自己的“爱情”,虽然最后和范柳原在一起了,但是命运中也充满了悲剧与苦难[1]46;《色·戒》中的王佳芝为爱情奋不顾身,最终却以悲剧收场;《半生缘》中的新女性顾曼桢追求思想与生活的独立,但还是在封建男权制度下屈服了,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最后落得悲剧性的半生。在封建社会中,她们都无法摆脱命运的悲剧性。
张爱玲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在她的众多作品中,《半生缘》(又名《十八春》)对女性的悲剧剖析尤为深刻,从女性的独特视角揭示了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半生缘》中也融入了张爱玲的缩影,体现了她对人生的思考。
二、《半生缘》的解读
(一)创作背景
1947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的传奇之恋谢幕。张爱玲的文学创作也进入了衰退阶段,虽时常有新作品问世,但数量大不如前。
《半生缘》是张爱玲的首部长篇小说,张爱玲用其女性的独特视角和悲剧的审美特性创作了这一优秀作品。该书讲述了在旧上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凄凉的爱情故事。《半生缘》在另一个重要层面上的意义在于它作为由女性作家创作的文本,其深具悲剧意义的故事与极其复杂性格的人物,无疑成为剖析时代背景下女性悲剧如何产生、如何发展、如何扩大延伸,以及研究张爱玲自身女性悲剧心理的重要范例[2]。《半生缘》讲述了在20世纪40年代新旧社会价值观相互交错的时代背景下的爱情悲剧,作者怀揣着想挣脱现实却又屈服于现实的矛盾心理,从而促进了《半生缘》的创作完成。
张爱玲的《半生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完成的。当时整个社会都弥漫着新的气息,所以《半生缘》中体现的思想是一种切合时代的思想。这与她别的作品中体现的思想不同[3]。
(二)作品解读
《半生缘》以含蓄的主角,鲜明的人物,悲情的故事,无奈的错过,兵荒马乱的时代背景,描写了在20世纪30年代旧上海的一些人物故事。小说里的男主角沈世钧是南京人,他跟许叔惠是同学,之前就认识,后在许叔惠的推荐下,沈世钧来到许叔惠的工厂任实习工程师。女主角顾曼桢,幼小丧父,家中有祖母、母亲、姐姐、弟弟。姐姐顾曼璐为了养家,牺牲自己做舞女,一家人都住在上海,而顾曼桢与许叔惠在同一家工厂做打字员。姐姐为了后半生考虑,嫁给了有钱有势的祝鸿才。顾曼桢与沈世钧通过许叔惠相识相知,最终坠入爱河。顾曼桢是善良独立的新时代女性,因为两人的家庭并不相称,顾曼桢不愿拖累沈世钧,所以不愿意早早结婚。然而,姐夫祝鸿才对顾曼桢一直心怀不轨,而姐姐为了自私地保住家庭地位,不惜设计让自己的妹妹被祝鸿才玷污。姐姐一方面将顾曼桢囚禁在家长达一年并生下孩子,另一方面制造误会让沈世钧放弃爱情,最终与不爱的石翠芝结婚。许叔惠也因此错过了石翠芝。母亲目睹姐姐的所作所为却不加制止,反而任其发展,凸显了封建社会人性的弱点。而后顾曼桢终于逃出祝家,却发现早已物是人非,沈世钧早已不在原地,不久后顾曼璐也去世了,顾曼桢发现儿子在祝家经常被仆人虐待,出于对孩子的考虑又无奈嫁给了祝鸿才,最后还是离了婚。在小说结尾,沈世钧和顾曼桢多年后的重逢,顾曼桢道了一句:“我们回不去了”,更是增添了悲剧色彩[4]。整篇小说笼罩在淡淡的伤感氛围中,顾曼桢的命运辗转坎坷,结局令人心生悲凉,不禁引发读者对命运的感叹。
三、《半生缘》顾曼桢的人物解读
20世纪30年代的旧上海,是还带有封建思想的社会。顾曼桢有自己的工作,用自己的工资补贴家用,而许多女性却依附于男人而生存。在繁华的上海,她有自己的追求与向往,不同于其他普通女性。
顾曼桢不是安于现状的封建女性,她受过教育,自立自强。对于爱情,她大方承认接受;对于家庭的责任,她勇于承担;对于生活的磨难,她不愿意放弃。她是与时代背道而驰的叛逆新女性。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为家人谋得幸福,求得安稳,不愿靠姐姐嫁入祝家来接济自己。
《半生缘》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在那个时期,女学生都带有守旧的思想,到哪也喜欢带个女同学一起,即使和未婚夫一同出去,翠芝也是这样。”[5]165这是顾曼桢第一次到南京沈世钧家中,与石翠芝相见时形成的强烈反差。石翠芝与未婚夫出去还要遵守封建礼教,而顾曼桢却是跟沈世钧和许叔惠大方谈话,相处自由。
(一)顾曼桢的形象特点
1.坚忍自立
书中写姐姐顾曼璐为养活家庭牺牲自己做了舞女,小时候顾曼桢经常在家里见到形形色色的“客人”。书中写道:“原来顾曼桢去换了一件新衣服,因为姊姊结婚,新做了一件衣服,这种比较娇艳的颜色她从前是决不会穿的。”[6]她永远穿着一件蓝布衫,除了为省俭之外,她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因为家里有许多姐姐的朋友进进出出[6]。她不喜欢姐姐的生活,更是不可能像姐姐一样生活,所以顾曼桢永远穿着一件蓝布衫,隐忍着,缺少了这个年纪应有的色彩。这体现了顾曼桢坚忍的性格特征。
父亲去世后,她与母亲、姐弟及祖母共同生活。大学毕业后,她找到工作,依靠自己的努力追求美好生活。小说中写道,顾曼桢默然听到这里,忍不住跟顾母说,以后无论如何,家里的开销都由她拿出来,她不想再继续靠姐姐工作来养活家,她认为自己已经有能力养活自己的家人了。她的母亲想到就算家里紧点几个小孩还得上学,表现得还是比较担心。顾曼桢安抚顾母,并让顾母别着急,到时候总有办法的,她可以再找点事做。[5]24顾曼桢渴望追求独立,不愿重复母亲和姐姐的生活,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家人谋求更好的生活。
书中还写道沈世钧跟顾曼桢提出结婚,想到结婚后顾曼桢的负担就可以小一点,顾曼桢推辞说再等两年,她相信自己可以做到经济独立,生存独立。她没有选择依靠男人或婚姻。她相信自己能够自立,像男人一样支撑起自己的家庭。她身上充满了活泼的时代气息,是新时代女性的象征。
2.坦诚随和
小说刚开始写顾曼桢、许叔惠和沈世钧三人的见面场景,“蓬松的头发,很随便地披在肩上”[5]3。这是沈世钧对顾曼桢的第一印象,而且在那个还带有封建色彩的社会,顾曼桢不像闺房小姐一样忸忸怩怩放不开,而是跟他们落落大方地交谈,摆脱了旧社会女性的形象特征。随着两人交流的加深,顾曼桢展现了她坦率真实的一面。她毫不掩饰地讲述自己的家庭遭遇,且不做任何的掩饰和隐瞒。她的坦诚和真实让沈世钧对她产生了更深的好感和信任。这些都体现了顾曼桢的坦诚和随和。
3.勇敢执着
顾曼桢作为新时代女性的缩影,她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追求专一的爱情,不像过去的人那样,可以接受几个女人分享丈夫的爱。她在面对与沈世钧的家世落差时,并没有感到卑微而退缩,而是勇敢地守护爱情,追求爱情。在被祝鸿才侮辱后,也依然坚守爱情,不愿放弃对爱情的向往。而许叔惠却有一种封建落后的门第观念,在比自己家世好的石翠芝面前退缩了,此时更体现了顾曼桢的新时代女性特征。
顾曼桢在姐姐顾曼璐的预谋下,被祝鸿才玷污后,姐姐一直限制顾曼桢的活动,顾曼桢也少进食,身体非常虚弱,顾曼璐劝顾曼桢跟了祝鸿才,但顾曼桢不屈服于这个现实。她以强大的生命力和顽强的意志最后为自己争得了自由。顾母封建的思想使她葬送了女儿的青春,而顾曼桢勇于反抗的精神,为自己博出了自由。同时她的故事也激励着人们勇敢地追求自由和尊严,不受任何外界的限制和束缚。
4.软弱无奈
在顾曼桢的骨子里还是有封建意识的,虽然顾曼桢是当时社会“新时代女性”的缩影,但她还是没有摆脱内在的软弱性。在她逃出祝家以后,她是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命运的,在豫谨知道顾曼桢的悲惨遭遇之后,他劝顾曼桢坚持自己,让她拿定主意,只要她坚定一点,摆脱骨子里的封建观念,她的未来也还是一片美好。可是顾曼桢是不幸的,她没有挣脱传统女性思维对她的控制,又因为孩子不得不屈服于现实跟祝鸿才结婚,但最终对命运的无法把握,也是顾曼桢命运走向悲剧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顾曼桢的形象意义
张爱玲塑造的顾曼桢这一悲剧形象是有时代性的,女主人公顾曼桢个性鲜明,是新女性的时代缩影。她受过较好的教育,是追求独立的职业女性。渺小的存在、贫困的生活没有压垮她们,还坚定了她们努力生活的信念[7]。但在那个封建社会下她们还是无法摆脱命运的悲剧性。顾曼桢的悲剧命运是封建社会下的产物也是新时代的警醒,她有对封建男权社会下不得已的屈服,对自己命运无法把握的无奈,有女性意识的觉醒,也有对独立自由的追求。她不再依附于男人,并从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与顾曼桢相比,顾曼璐一类的女人,也曾为自己的命运作过斗争,但现实留给她们的机会太少,她们只能向命运低头,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这是可悲的。
顾曼桢和顾曼璐命运的比较,反映了封建社会下女性命运的多样性和悲剧性。她们的命运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折射,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的写照,呼唤着人们对女性的关注。在张爱玲笔下,这些女性形象承载着社会对于女性发展的期望,也激励着人们为女性解放事业而努力。
四、顾曼桢的悲剧性及悲剧的必然性
(一)具有“新女性”表象的悲剧命运
在小说《半生缘》中,顾曼桢这个角色更加开放,她追求自由,向往自由的婚姻。但这种“新女性”的命运却又是悲惨的,顾曼桢没有办法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爱情。因为在顾曼桢那个时代中,还广泛地存在着封建主义的价值观。而这更体现在女性的婚姻上,还存在着封建的唯父母是从等传统保守的思想[8]。在封建社会中,顾母在女儿被侮辱囚禁的情况下,受金钱奴役。她既不愿营救女儿,也不让女儿声张,最终将顾曼桢许配给祝鸿才。
顾曼桢的出现与当时社会上的女性形成对比,言谈举止,落落大方。祝鸿才在顾曼璐那里看到她的照片时,便开始打起了算盘。显然,她与祝鸿才见过的形形色色的人截然不同。书中还提到,祝鸿才在顾曼桢面前实在缺少自信心。在祝鸿才心中,顾曼桢是“新女性”,是美好的象征,他一直觊觎顾曼桢,最终导致顾曼桢难逃他的魔爪。在顾曼桢逃出祝家后,发现沈世钧结婚了,支撑自己的信念崩塌了。而顾曼璐死后,顾曼桢得知女仆虐待自己的儿子,她向命运妥协了。她又不得不为了儿子返回祝家,嫁给了祝鸿才,体现了女性自身的性格弱点,揭示了处在封建主义价值观下的女性走向人生悲剧的必然性[8]。
(二)时代环境对顾曼桢的压力
在新旧时代交替的旧上海,社会上出现了很多的新鲜事物。然而,时代背景依然是封建的男权社会,女性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顾曼桢就像囚在牢笼里的鸟,渴望挣脱束缚,却又无可奈何……在男权主义社会下,顾曼桢的人生更具悲剧性。她象征着“新女性”,追求自由,但即使走出了家庭,依然无法摆脱时代的束缚,最终只能向男权社会妥协。顾曼桢与沈世钧的爱情也是一场悲剧,两人的家庭背景悬殊,且在姐姐顾曼璐的问题上,两人的分歧是无法避免的。顾曼桢不喜欢姐姐的工作,但是从来没有看不起她。在顾曼桢将自己的家庭坦然相告时,沈世钧也表明了不介意顾曼璐的身份,可后来却也以社会的眼光来看待她,使得两人最后的见面不欢而散。在顾曼璐的安排下,祝鸿才玷污了顾曼桢的清白。不幸的是,在男权当道和旧社会伦理道德的约束下,母亲做了有钱女婿的帮凶,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对顾曼桢袖手旁观。
顾曼桢靠自己顽强的意志,好不容易逃出祝家,却发现自己的信念支撑——沈世钧早已不在原地。她绝望了,孩子成了她最大的慰藉,无奈她顺从了时代嫁给了祝鸿才。如果顾曼桢敢于做时代的叛逆者,不屈于封建社会的统治,放下孩子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那么她的结局可能就是另外一片天地。不论顾曼桢是为了孩子,还是因为沈世钧不在了而选择嫁给祝鸿才,都是一种封建社会思想统治下女性对男权社会制度的屈服,这似乎是最大的悲剧性。话虽如此,人终究难以超越时代的局限。顾曼桢的结局不仅仅是属于她自己的结局,也是属于那个时代千千万万女性的结局。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半生缘》中,张爱玲成功塑造了顾曼桢这个人物形象。本文通过分析故事的时代背景与顾曼桢的形象特征,深入研究其人物悲剧,将顾曼桢的悲剧性展现给读者。顾曼桢作为时代的牺牲品,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展现了她的悲剧。张爱玲以女性视角出发,透过这一独特的视角审视封建男权社会,揭示了新时代女性在封建社会中的悲剧命运。封建男权社会不仅是女性面对的生活现实,而这还是无法根除的时代烙印,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女性意识的觉醒。[8]。然而,尽管顾曼桢的命运悲剧深刻展现了封建男权社会的压迫,张爱玲在塑造这个人物时,也让读者看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挣扎。顾曼桢在追求独立与自由的过程中,不仅是对旧有秩序的反抗,更是新女性觉醒的象征。她的命运虽然坎坷,但其对自由与自我价值的追求,映射了那个时代众多女性的内心渴望。正是在这种悲剧性的命运中,张爱玲揭示了女性面对的不仅是个人的不幸,更是一个时代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1]李炎超.凄清苍凉的人生——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7,(09):46-47.
[2]房广涛.论张爱玲《半生缘》的悲凉韵味[J].科技视界,2015,(30):238.
[3]殷小兵.痛苦的转型:张爱玲在1949—1952年[D].福建师范大学,2006.
[4]谈姝雅,李梦琪.浅析张爱玲《半生缘》中顾曼桢的人物悲剧[J].海外英语,2018,(08):167.
[5]张爱玲.半生缘[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6]贾丽.解读张爱玲小说中女性的服饰描写[D].山东师范大学,2010.
[7]杜存迁.尘埃里的爱情悲歌——张爱玲小说《多少恨》赏析[J].大众文艺,2009,(23):45.
[8]陈宏.剖析张爱玲《半生缘》中曼祯悲剧的必然性[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