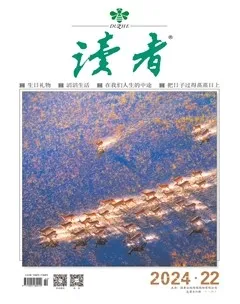战火中的蓝色小方巾
2024-11-15S.A.阿列克谢耶维奇

1942年9月,我们抵达莫斯科。整整一个星期,我们都坐在铁路环线的列车上,沿途停留各站,每到一站就从车上下去一批姑娘。人们俗称的“买家”来到姑娘当中,他们是不同军兵种的干部,从我们中间挑选狙击手、卫生指导员,或者无线电员……所有这些都没有让我动心。最后整列火车上只剩下13个人,都被转到一辆闷罐车,拉到了路轨的尽头,在那儿停着两节车厢:我们这节和指挥部的一节。连续两天两夜,没有一个人来找我们,我们只管又说又笑又唱俄罗斯民歌《被遗忘和被遗弃的》。到第二天晚上,我们终于看到有3个军官和列车长一起朝车厢这边走来。
“买家”来了!他们身材高大魁梧,扎着武装带,军大衣上的军扣锃亮,带有马刺的皮靴擦得发光。好帅啊!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军官。他们走进指挥部的车厢,我们就把耳朵紧贴在车厢外墙上,偷听他们在说什么。列车长在念我们的名单,并且对每个人的特点做了简要说明:某某原来做什么工作,老家在哪里,受过什么教育,等等。最后我们听到一声命令:“让她们全都过来。”
于是,列车长走出指挥部车厢,命令我们列队集合。上级问大家:“你们想学习作战技能吗?”我们怎么会不想呢?当然求之不得,可以说是梦寐以求!以至于我们居然没有一个人想到要问一句:“去哪里学习,和谁学习?”只听到长官命令道:“米特罗波尔斯基上尉,把这些姑娘带到学校去。”我们都挎上自己的精品袋,两人一行,由军官带上了莫斯科大街。亲爱的莫斯科,祖国的首都!即使在这种艰难的时刻也是那么美丽,那么亲切。那名军官在前面大步流星地疾走,我们都有些跟不上他,只得一路小跑……
我还清楚地记得军校毕业考试中的一个问题:“工兵的一生可以犯几次错误?”
“工兵的一生只能犯一次错误。”
“没错,姑娘……”
接下来就是军校的行话:
“你通过了,巴拉克学员。”
上级把我带到我要掌管的工兵排,下令道:“全排集合!”
但是全排士兵都没有站起来。有人躺着,有人坐着,有人在抽烟,还有人在打哈欠伸懒腰,浑身的骨骼咯咯作响。他们都假装没注意到我的存在。这帮久经沙场的男侦察兵居然要服从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女孩子的指挥,他们感到很丢人。我当然明白他们的心思,只好就地下令:“解散!”
就在这时,敌人突然开始炮轰。我跳进了战壕,因为大衣是新的,我没有一下子卧倒在泥土上,只是大衣侧面沾了一些薄薄的白雪。人年轻的时候常常是这样,把一件军大衣看得比性命还珍贵。当然这遭到了士兵们的一阵讪笑。
工兵侦察是怎么进行的?就是战士们在深夜悄悄潜入中间地带,挖一个双人掩蔽沟。有一天黎明之前,我和一个班长悄悄爬到双人掩蔽沟里,其他战士给我们打掩护。担心换人会惊动敌人,我们就在沟里埋伏了一整天。一两个小时后,我们的手脚都冻僵了,就算穿着毡靴和皮袄也不顶用。4小时后,人都快成了冰柱,要是再下雪我就变成了一个雪姑娘。到了夏天,我们又不得不在烈日下或雨水中趴着,一整天趴在那里仔细观察敌人的所有动向,并且画出前线观察图。
在我军进攻之前,我们要在头一天夜里做好侦察工作,一寸一寸地探测区域地形,在雷区中确定一条可以行进的路线。我们总是紧贴地面匍匐移动,肚皮就像滑行的船底,而我则需要急速地从一个班爬到另一个班。我探测的雷区比别人的更多。
我遭遇过各种各样的情况,那些故事足够拍几部系列电影。
有一天,军官们邀请我去吃饭,我同意了。工兵们并不总是能吃到热食,因为大多数时间我们都在野外度过。可是,当食物都摆在餐桌上时,我却盯住了一个炉门关闭的俄罗斯烤炉,走过去想看看里面是什么。那些军官看到我这个样子都笑了,说这个女人神经兮兮的,大概以为烤炉里会有地雷。我正要回应他们的笑话,却立即注意到烤炉左侧的底部,有一个小孔。我仔细地朝里面看去,只见有一根细细的导线通向烤炉。
我急忙转身对坐在屋里的人喊道:“房子里有地雷,请马上离开房间!”军官们顿时安静下来,难以置信地瞪着我,没有人想从桌旁站起来。我又大声说了一遍:“马上清空房间!”随后我带领工兵开始工作,先卸下烤炉门,再用剪刀剪断导线。这下就看到了:在烤炉内,有几个用麻线捆在一起的一升大小的搪瓷缸子。在烤炉深处,隐藏着两大卷东西,用黑纸包着,那是20公斤炸药。
在战争中我尽量不去想爱情和童年的事情,即使面临死亡也不去想。为了活下来,我为自己定下很多禁区,比如我绝对不让自己去触碰任何暧昧和温情,连想都不能去想,回忆过去也不行。我还记得在解放利沃夫之初,上级批准我们有几个夜晚可以自由活动。那是整个战争期间的第一次,我们全营到城市剧院看了一场电影。起初我们已经不习惯坐进软圈椅,不习惯看到这样美丽雅静、舒适安宁的环境。当电影结束时,我一时间竟忘记了有些地方还在作战,忘记了我们马上要开赴前线,忘记了不远处仍然有死神守候。
只过了一天,我们排就奉命去清理通往铁路那段崎岖不平的地区。在那里,有几辆汽车被炸飞,又是地雷造成的。我们侦察兵带着扫雷器沿着公路前行。天上下着冰冷的细雨,寒气很重,所有人都被雨水淋得透湿。我的靴子泡胀了,越来越沉重,仿佛脚底是两块铁板。我把军大衣的衣襟塞进皮带里以免踩在脚下被绊倒,走在前面的是我的军犬涅尔卡,我用皮带拴着它,它负责寻找炮弹和地雷,然后就坐在旁边等待我们排雷。它是我忠实的朋友。
战争结束后,我们还要花整整一年时间排雷,从田野到湖泊和河流。在战争中,所有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跳进水里,主要任务是渡过去,准时到达目的地。现在,我们开始想活下去的事情了。对工兵来说,战争的结束要在战后好几年才能实现。胜利之后还要继续等着炸弹爆炸,这是怎样的感觉?胜利后的死亡,才是最可怕的死亡,那是第二次死亡。
作为1946年的新年礼物,上级奖励我一块10米长的红缎子。我笑了:“我要它有什么用呢?难道复员之后我要用它缝制一件红色连衣裙,胜利的红裙子?”不久,我的复员命令就下达了。全营战友为我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在晚会上,军官们给我献上一份厚礼——一块大大的刺绣蓝头巾。这块蓝头巾让我不得不献上一首歌曲《蓝色小方巾》。那次,我为战友们唱了一整夜。
在回家的火车上,我发烧了。脸肿得嘴都张不开,原来是长出了智齿。我从战争中回来了。
(春秋笔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战争中没有女性》一书,本刊节选,李晓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