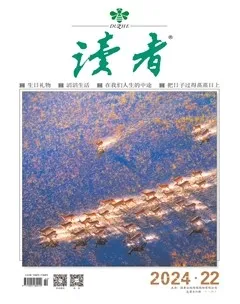为什么律师事务所很少做广告
2024-11-15刘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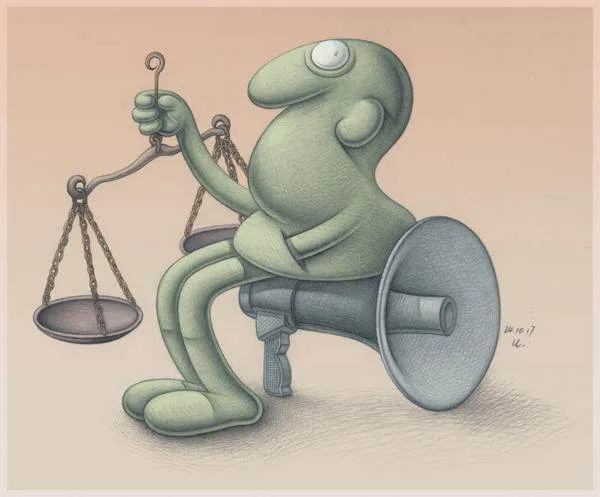
我们生活在一个“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商业社会,几乎各行各业都特别注重营销。尽管广告遍布大街和网络,但是我们似乎很少见到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律所”)做广告。而且,好的律所基本上不做广告,以至社会大众普遍不清楚国内有哪些名牌律所。
更有意思的是,律师行业自身似乎也在营销方面极为谨慎,需要遵守一些条条框框。例如,大所云集的北京就有硬性规定。《北京市律师事务所执业广告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禁止律师个人做广告,律所虽然可以做广告,但广告内容不能像商业广告那样过于夸张。在业内,如果个别律所做了较为夸张的广告,也会引起负面的评价。
美国也是如此。在历史上,美国各州的律师协会都禁止律师做广告。即便此类硬性规定在1977年被美国最高法院明确废除,但律师圈里还是有“高端律所不打广告”的惯例,只有那些做移民业务之类的小律所才会打广告。
这就未免让人感到奇怪:为什么律师行业要如此限制做广告呢?
答案是,律师行业需要刻意与社会保持距离,即“高贵的消极性”。律师行业一方面要坚持“高贵”,建立高深的行业壁垒,只接纳少数精英进入;另一方面要坚持“消极性”,保持绅士品格,恪守职业伦理,减少营利冲动和市场思维。因此,律师行业是现代社会中少有的像欧洲中世纪行会的组织:对外垄断,相对封闭;对内等级森严,有着条条框框。
那么,问题随即出现: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信息在流动、知识在流动、圈层在流动,律师行业为什么还要维护“高贵的消极性”?为什么不能顺应趋势,大力推行市场化运作呢?
对此,我总结了3点原因。
第一,维护律师行业公共形象的下限,才能保证整个行业的存续。
律师行业必须有操守,否则就有可能被社会抛弃。原因在于法律知识太专业、太复杂,法律人和普通人之间存在极大的信息不对称性,普通人很难判断律师服务的质量,只能通过对他们人品好坏的判断来选择,因而法律服务经常被称为一种“信任产品”。正因如此,律师的公共形象就变得特别重要。
更何况,律师的形象在公众眼中可能有些负面。姑且不说网上大量投诉律师,甚至咒骂律师的帖子,中国古代社会早已称呼这个行当的从业者为“讼棍”。西方经典文学作品中对于律师的描写也少有正面形象。这也应了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艾伦·德肖维茨的一句话:“任何行业遭受如此恶名,必定是得罪了人。”
在美国,律师的形象相对较好,毕竟很多著名政治家和社会管理人才都是法律行业出身。然而在20世纪,美国法律行业也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公共信任危机。
这场危机的起因是1972年的“水门事件”。众所周知,时任美国总统、共和党人尼克松为了赢得竞选、实现连任,派人潜入水门大厦的民主党总部安装窃听器。东窗事发后,引发轩然大波,造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丑闻之一,尼克松也因此被迫辞职。重要的是,事发之后,公众发现尼克松的竞选团队里几乎都是律师或者法学院毕业生。于是,人们就把愤怒发泄到了法学院和律师界,导致全美社会对法律人的深度厌恶。后来,美国甚至出现了一类格言、段子和寓言,专门用来抨击、嘲讽和挖苦律师。
于是,为了挽回行业形象,让律师们有饭吃,美国律师协会开始通过各种举措加强律师职业伦理建设,塑造良好的行业形象。“水门事件”之后,美国律师协会立即要求所有接受协会认证的法学院开设法律职业伦理的必修课程,而且要求全美统一考试。要知道,美国律师资格考试都是各州分别组织的,唯有法律职业伦理这一项是全国统考。圈内人都说法学院里的其他课程是为客户学的,唯有法律职业伦理是为自己学的。
限制律师做广告就是法律职业伦理的要求,其目的是维护律师的形象。2018年,我国的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发布新规《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业务推广行为规则(试行)》,叫停“胜诉率名列前茅”“跟某机关有特殊关系”“不胜诉就退款”等具有虚假性、误导性和夸大性的业务推广方式。
禁止律师乘人之危揽生意也是法律职业伦理的要求。行话将此种行为形象地称为“追逐救护车”:律师一看到救护车在街上跑,就追着救护车直至医院,因为救护车里很可能有受伤的人,大概率会涉及人身损害赔偿问题,自己就可以揽到生意。美国律师协会明文禁止这类行为。英国也有类似规定,禁止律师在大街、港口、医院或者事故发生场所揽生意。在我国,中华全国律师协会2018年发布的新规也明确,律师不得在法院、检察院、看守所、公安机关、监狱、仲裁委员会等场所附近张贴各种广告。
此外,律师还有从事公益活动的义务。好的律所每年都会免费提供一些法律服务。在我国,一些律师会在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和全国法制宣传日期间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美国律师协会的伦理规则建议律师每年提供至少50小时的公益服务。此外,律所出资在大学设立奖学金,律师在法学院授课、出版专著、发表论文,都是塑造品牌形象的方式,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也是一种高雅的广告。
第二,设置适度垄断、限制自由竞争,更有利于行业的长远发展。
在市场化时代,一听到垄断,人们通常会联想到这是一种人为设定特权的行为。然而法律行业仍然特别坚持垄断,它不仅垄断了从业资格,还有各种条条框框。
为什么?因为在一定时期内,法律业务的总量有限。如果从业者过多过杂,就容易形成恶性竞争。如果再没有惩戒机制,就会有人为了生存铤而走险,甚至赤裸裸地违法。长此以往,劣币驱逐良币,整个行业的声誉和机会就会被全部毁掉。
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各国的法律行业为什么要设立很高的准入门槛。在美国,一个人只有在经过美国律师协会认证的法学院接受过法律教育,修满核心课程的学分,才有资格参加律师资格考试,之后才能成为律师。
我国也在不断提高法律行业的准入门槛。2018年,司法部推行了新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严格限制报考者的学历。要求报考者必须至少具有法学类学士学位,或者非法学类本科学位并获得法律硕士、法学硕士及以上学位或有3年以上法律工作经验。在此之前,人们只要有大学学历就能报考,且不受专业限制。
以上还只是对准入门槛的限制,律师在进入行业之后,还需要遵守有关内部竞争的条条框框。例如,各国的法律行业内部规范几乎都规定,律师的收费不能低于行业标准。以我国为例,长期以来,在民事、刑事、行政和国家赔偿等案件中,律师收费标准实行政府指导价。近年来,虽然很多法律业务领域的政府指导价已经放开,但前文提到的2018年出台的全国律协新规,也禁止律师在业务推广和行业竞争中不收费或者降低收费,除非是法律援助案件。
英美法系也是如此。清华大学法学院已故的何美欢老师,拥有中国香港、美国纽约等地的律师资格。20世纪90年代,她帮助我们的一些国企在港股上市。出于民族情感,她不想收取太多律师费,但根据行规,她也不能降价。最后,她就干脆不收钱,算是做公益了。律师之所以这样不按市场规律办事,就是为了防止劣币驱逐良币,维护行业的长远发展,毕竟行业自治的前提是自律。
第三,维护行业发展利益,塑造专业精神,才能促进公共利益。
这听起来像是口号,其实一点儿都不虚。2016年,曾经担任通用电气总法律顾问的本·海涅曼出版了一本名为《内部法律顾问革命》的著作,他从自身多年的法律职业经历出发,大力提倡商业律师的公共精神。
他在总结自己的成功经历时指出,真正的好律师,就是要让企业在高绩效和高诚信之间维持平衡。如果律师为了企业营利不择手段,不顾社会责任,放任企业违法,甚至协助其违法,不仅会伤害企业,更会伤害社会。在海涅曼看来,商业律师承担着复兴律师公共精神的重要责任:律师必须站在法律一边,促使公司的商业行为合法合规,尽量遏制公司不正当的营利冲动,负起社会责任。
商业律师如此,诉讼律师更是如此。自从有律师职业开始,律师的工作就一直都有公共服务的成分。比如在美国,律师在法律中的正式称呼是“庭吏”,即“法庭官员”;而且美国律师行业的最高理想仍然是“法律人—政治家”,而非只靠法律赚钱的某种商人。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律师,也拥有国家干部身份。虽然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律师变成了私人主体,但公共精神依旧存在,律师本身仍必须承担维护公益的责任,也可以说,律师必须具备某种君子之风。
(沧海一粟摘自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想点大事:法律是种思维方式》一书,刘 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