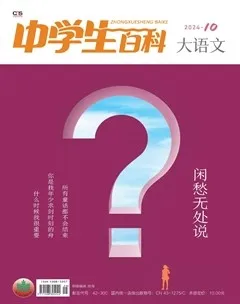丑陋的手不戴手套
2024-11-11吴卓锦

“你的手,就洗不干净了吗?多加点肥皂!好好洗洗,用热水烫一烫。早操的时候,在操场上竖起来的几百条手臂都是白的,就是你,特别呀!真特别。”萧红的短篇小说《手》,讲述了乡下姑娘王亚明在学校被歧视的故事。她有一双黑手,一双洗不干净的手。她想让父亲带一副手套来,并向校长表明了这一想法。校长笑得咳嗽了起来:“不必了!既然是不整齐,戴手套也是不整齐。”
虽然只是文字描述,但我依然能想象出那是怎样一双手——它们令人不适,甚至是令人气急败坏。所有这些情绪,跟我看到或者想到母亲的手时何其相似!是的,我总觉得母亲的手非常丑陋。说出来有些不好意思,每每瞥见其他同学妈妈的白皙的手时,我就会想到母亲那双沟壑纵横、散布着老茧的手。那双手,绝不是多加点肥皂洗一洗、用热水烫一烫就能面目一新的,也不是戴手套就能遮掩住丑陋的,因为它们就像刺一样扎在我心里。
虽说的确需要打理繁重的家务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事情,可她毕竟是一个在办公室上班的人,怎么能有一双张翼德式的手呢!这实在不符合我正确的、先进的审美。我素来嫌弃那双手。每当她要伸出令人发怵的手触碰我时,我会条件反射一般往旁边挪蹭。倘若实在躲不掉,只好耐着性子将手推开。她难道没有察觉到我的厌恶吗?我犯错误时,她总是用这手来拧我。我非常不服气。那是什么手呀?可是,就是这双手把我拉扯大的,我又怎么能厌恶呢?
复杂的情感萦绕着我,白天和黑夜,每一分每一秒都不消停,直到中考前的一天,老师让我去校门口拿饭。我当时感觉十分突兀,很不爽快,但又毫无办法。我来到校门口,不见人影,只得徘徊踱步。不一会儿,周围的同学越来越少了,我转圈的步伐逐渐加快。终于,她来了。我没好气地问她为什么这么晚。她露出憨厚的笑容说道:“我跟你说过的,今天从单位食堂打饭……有米粉肉呢?”我又觉得好笑:“我学习任务重,当然忘了。你从单位食堂打饭送来,还不如我自己去学校食堂吃呢。”
她倒不在意我怎么说怎么想。可是,校内校外隔着一道铁栏杆,且栏杆的间距太小,饭怎么递进来呢?高高的铁栅栏上,一排锐气十足的尖刺反射着正午的骄阳,似在耀武扬威。母亲这时展示了她潜藏的勇气,一只手抓住栏杆,吃力地踮着脚,顺势把盒饭高高举起。就像是《人类群星闪耀时》里的马霍梅特奇迹般地带领他的舰队穿越岬角,我的“马霍梅特”带领我的饭菜翻过铁栅栏,并将其举起,高高地举起。
又是那双丑陋的手!一只手颤巍巍地抓着栏杆,一只手提着饭菜,摇晃着越过尖刺,几乎要碰上去了。这场景实在是惊心动魄。我不敢懈怠,赶紧伸手接过来。饭菜有些沉,往下坠了坠。然后,我头也不回地走了,没说一句话,留下身后啰嗦的叮咛在空中回荡。我终是不忍心,回头想说一句“谢谢”,结果又看见那双丑陋的、沟壑纵横的老手正向我挥舞着。母亲仍站在几步外看着我。我不禁鼻头一酸,一股驳杂的热流顿时涌上心头。
我没再回头,但能想象母亲那日渐消瘦的、总是十分匆促的身影,以及那双注定遭受苦难、丑陋无比的手。母亲如何用丑陋的手把沉甸甸的饭菜送过危险的铁栅栏?我苦苦寻思着,而后倍感震惊。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她?是什么力量如此磅礴宏伟、无坚不摧?是什么力量长久地对抗时间,鼓舞人心?
我素来不能忍受那双手的。手的丑陋是不争的事实,连带一些复杂的情感,在我脑海里根深蒂固。有一天,我发现我再也无法像小时候那样快乐地攥着母亲的手了。时光改变了母亲的手,也改变了我。不过,我还是想说,即便在世间游荡千百年之久,我也无法找到一双更丑陋的手了——母亲的手已是我心中的唯一。她,我的母亲,像一个真正的勇士340f6f3d3daf770ffd9d31df6ae1c989d9d9e8a4996587f9e9a15a392674b84f。或许她的手衰老枯槁,却在我生命中的转折一刻,把爱越过障碍送到我面前。原来,这双手一直伴随着我,支撑着我。
“月光犁开掌纹/阡陌纵横/沉睡的命运/有春风也不敢触摸的疼痛……”在我看来,深藏于母亲手掌中的,倒不是她的疼痛,而是我在挣脱丑陋印象后的感动与悔恨。事实上,每位母亲都曾有过一双好看的手。那双手,抚过青春的脸庞,然后稳稳抱起我们的童年。至于之后它们历经风雨,被粗粝的生活打磨,终究变得丑陋不堪之时,是否像乡下姑娘王亚明所想的那样,需要一副手套呢?想必是不需要的。为什么要遮掩呢?诗人海子说,“手/摘下手套/她们就是两盏小灯”。我喜欢这个明亮又温暖的比喻。你看,一双丑陋的手,最终点亮的是灯,写下的是关于母爱的最美“手写体”!
(作者系湖南省新化县第一中学学生,指导老师:戴雄英)
特约评析 | 宋雨霜
成都文理学院文法学院写作教师,讲师
亲情是散文写作的重要主题。
一些作者写到父母、祖父母等长辈时,会有“为亲者讳”的顾忌心理。他们往往侧重写无私与爱,把亲人塑造为高大上的形象,刻意让一些不掺杂质的浓烈感情洋溢在字里行间。这种写法会导致同质化,并且失真。读完《丑陋的手不戴手套》后,我心里涌起一个声音:这是一篇书写真实、情感真诚的作品,而其中的“真”又会产生一种直抵内心的力量。
书写真实,源于作者对母亲双手的观察。这双“沟壑纵横、散布着老茧的手”让作者产生不满、怨憎。作者重点写了母亲给自己送饭的场景,让那双手展示出了丑陋和有力量的两面性。这种真实的生活场景,被作者看在眼中,激发了后续的自我反思。
起先,“它们就像刺一样扎在我心里”,后来“你看,一双丑陋的手,最终点亮的是灯,写下的是关于母爱的最美‘手写体’”。面对母亲的手,作者儿时亲近,长大后疏远,如今却被常常触动——这既是母亲在岁月流转中的变化,也是作者心绪的转变。这种转变是真实的,符合青少年的成长心理。作者的勇敢之处在于此,不遮掩、不粉饰自己的想法,而是真诚地吐露心声。这种勇气、真诚、自省的品质是成长的蜕变,也是写作者的必备素养。
开篇引用萧红的作品《手》,侧面突出母亲双手丑陋的形象。结尾处,引用诗句“月光犁开掌纹/阡陌纵横/沉睡的命运/有春风也不敢触摸的疼痛……”“手/摘下手套/她们就是两盏小灯”,彰显手的内涵和美感。首尾的变化,在结构上形成对比映照,凸显作者认知和情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