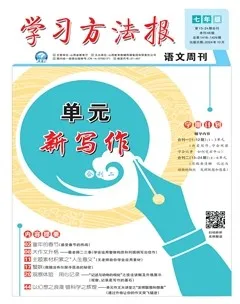“联想与想象”片段赏析
2024-11-07王淦生
联想和想象是写作——尤其是记叙文写作中常用的手法。联想和想象都是由此及彼的思索,联想是想象的基础,想象是联想的升华,二者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本质区别。联想是已有生活经验的组合,通常是指由某些人、物、事联想到与之相关的人、物、事。这些人、物和事之间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定的联系。想象则是在已有生活经验的基础上的新创造。在心理学上,想象是指在知觉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新的组合而创造出新形象的心理过程。
联想和想象不受时空限制,可以从所见所闻中生发出来,帮助人们扩展取材的领域,获得无限丰富的写作材料,开辟出广阔无垠的思维空间,创造出无穷无尽的新形象。因此,写文章,不管是立意构思、谋篇布局,还是写人叙事、勾画形象,都不能没有联想和想象。特别是文艺创作,更应富于想象力。古今中外的经典名篇,都是运用联想和想象的典范。
01
听着《苏东坡传》走在河边,无意间抬头,竟然从一绺一绺的柳枝的间隙里,看到了月亮。仿佛那月亮单是停在那儿等我,等我闲散游荡了一整个下午,耗得日落天黑,走过那棵树下,脚步顿在一个完满的角度,不偏不倚地向上看了一眼。
而那月亮,还是900年前的月亮。它曾望着苏东坡出生、长大,看他一生浮浮沉沉,22岁丧母,30岁丧妻,49岁丧子,60岁还在被贬谪的路上;它在深夜里,听过他沉沉的叹息声,凝视过他那双无奈却也达观的眼睛,看着他用美食抵御无常;它也看着他度过生命里的最后一刻,看着他的诗词在或太平昌盛或战火纷飞的年岁里流转……它会一直看下去,看得比我们都久。
一直以来,比起好恶,我好像更习惯于用缘分来评判与人或事的关系。和苏东坡就算是极有缘的,他的诗词我很早就喜欢,很长一段时间,都最喜欢那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每每默念在心里,很是畅怀。
今晚同他的缘分,只因那枝梢的月亮,偶遇了耳机里播着的故事。大约很多年后,我都会记得这种心境和处境的隔空映照。
(摘自张妍《人生天地间,处处遭遇,处处相遇》)
[点到为止]
借助想象的力量,作者将夜晚树林间的一次散步演绎得满含诗情画意。耳朵里是《苏东坡传》的诵读,头顶上是明媚的月亮的映照,脚下是空间与时间的流转……于是,在想象当中,作者完成了一场穿越:她看到了900年前的月亮,看到那轮明月下苏轼一生的悲欢离合;听到了苏词在时空中的回荡: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美妙的想象,让作者充分享受到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
02
羁旅北京的日子长长,我的窗前纵是也有这样一块草地、一簇绿柳,在春天的阳光里还会有一树杏花装点,但是北国没有雨季,我看不到小孩子们折纸船的情景。北京是要到七月或者八月才会有雨,那是槐花开放的时节了。北京的雨会与槐花下了一街,一街的槐花雨把整个日子都流淌得芬芬芳芳,但是这样的雨,仍不会积上一洼水,引来天使一般的小蛙,所以即使雨后有月,它在这芬芳里也找不到栖落和梳洗的地方。
我固执地想,如是北京的槐花雨能够积成一个洼子,这样一个清浅的弥漫着槐花芬芳的水洼子,有一轮皎月把水映得银银的白,有一群天使般的小蛙,它们围着月儿唱歌,那该是多么的好啊。我常常在雨后的北京的夜里出走,我以为我是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地方的,它就在某一扇窗下,甚至那窗前也有一个痴情展卷的学子,甚至水边,还留着孩童戏水的赤足的脚印。可是,我的出走,却并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地方,我想终归是有这样一个地方的,只是我没有找到它罢了。
居京的月夜,于我它是散文化的时光。我在键盘上演绎着一个个的梦,情至深处,会忽然在某一段落浮起一片蛙声,是南国的春宵里那天真烂漫的蛙鸣,初是浅浅低低的几声,孤独而悠远,渐渐地汇合起蛙的合唱,且愈来愈临近我的窗,仿佛就在那一簇柳下。此时人便恍惚地进入以往的时光,一颗羁旅中的心,忽然地一热,为之深深地感动。但待我有心凝神细细地聆听,却发现窗外是一片寂静,静得月的清辉飘落到柳叶儿上发生的细小的沙沙声都能够听到,只是没有了蛙声。哦,此时的我,这才感到深深的失落,原来那一片蛙声,它源于我的梦里,或者说,是那永远也拂不去的幻听了。
(摘自古清生《总有那一片蛙声》)
[点到为止]
作者生于南国,春夏的雨后,窗前水洼中总有青蛙欢鸣,这也成为家乡铭刻于作者心中特有的印记。羁旅北京,蛙声也就成为作者乡愁的寄托,而且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每到春夏之交,尤其是雨后月明的晚上,作者总会想到那天真烂漫的蛙鸣,甚至觉得蛙声就跳跃于琴键之上,萦绕在自己身边。这样的联想和想象寄托了羁旅他乡的游子强烈的思乡之情。那想象中的蛙声,正是一缕缕乡愁的具象化表达,如泣如诉,感人衷肠。
03
在乡间的古楼里,当青苔从不远处的山坡上开始随着春风波动、蔓延时,门前的台阶也变绿了,古楼便春光融融,于是陋室不陋。此时,只要你细心观察,就会发现这些微不足道的青苔竟是如此有气势。它们都是一根连着十根,十根连着百根,连绵起伏,渐成气象。无论是断墙残垣还是悬崖绝壁,别的植物无法落脚,青苔却能从墙缝里、石隙中奋力拱出,四处蔓延着绿意,在荡漾的春风中记录着比石头还硬的倔强。
小时候,我的家乡,每年春日,也就是春雨即将来临之前,父亲总要爬上古楼,上屋顶清理盖瓦,家乡人称之“拾漏”。他总是弓着腰,小心翼翼地翻起一片片布满青苔的瓦,或剥下苔绿,或扯下苔丝,或拔出瓦沟中的苔草……然后装进一个蓝色的布袋里。他从木梯上下来后,便径直去后花园,从布袋里掏出一撮撮、一把把的青苔,或填于兰花盆,或黏附于梅花树干上,或塞进干枯的罗汉松那一个个细小的木洞穴中……父亲说,青苔也有一些诗意的名字,叫“绮线”,也称呼为“绿衣元宝”,百花有青苔衬托,人世间才会春色满园。
在岁月的戏台上,青苔似乎错过了《诗经》,却赶上了唐诗宋词的好时光,也融进了明清纷繁的花事。在诗意的年代,青苔倍加受人珍爱,“应怜屐齿印苍苔”,园子的主人因怕满地青苔被人践踏,所以闭门谢客。但有时也夹杂着几分苍凉和凄美,“小庭春老,碧砌红萱草”,青苔似乎总是见不到阳光,只在凄凄惨惨中顽强地生长着。
真正懂得青苔心意之人,应是清代的袁枚。我非常喜欢袁枚的那首《苔》诗:“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诗人笔下的青苔生长环境是很恶劣的,可它依然长出绿意来,展现出自己的青春。青春从何处来?它从苔草旺盛的生命力中来,它凭着坚强的活力,冲破困境,焕发青春的光彩。苔草是不会开花的,但它“也学牡丹开”,既是谦逊,也是骄傲。它虽然如此弱不禁风,却凭着自身的自强不息,争得和百花一样的开放权利,春天有它们不断地点缀,才显得如此春意盎然。
(摘自洪振秋《青苔撑起的一片绿意》)
[点到为止]
这部分关于青苔的描写中,前两段是对于青苔的写实性描写,后两段则是由此联想到古代诗文中描写和赞美青苔的语句,尤其是对它生长于恶劣的环境却依然保持一片绿意的旺盛的生命力和“也学牡丹开”的自强不息的精神的颂扬。实际上这已经是由物及人,由青苔的特点联想到了做人的风骨。其实在第一段的写实性描写中,就已经出现这种联想,“当青苔从不远处的山坡……于是陋室不陋”不正是源于对《陋室铭》中“苔痕上阶绿”的联想吗?
04
在青州,我又重新喜欢上了问路。我的姥姥也是山东人,我很喜欢听那熟悉的“山东味儿”,告诉我怎么向前走。
返程那天,下午的高铁,中午去了青州博物馆。这里最著名的藏品是1996年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的600余尊佛教造像,时间跨越北魏至北宋,长达500年左右。
展馆入口是青州微笑的代表,一尊贴金彩绘圆雕的佛像,身披圆领田格纹通肩袈裟,跣足立于覆红弥座上,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施无畏印。这尊佛像长着一张娃娃脸,弯弯的眯眯眼鲜活生动,脸上漾出那不经意间的安然浅笑……我想起来青州第一天问路的那个小姑娘,她笑盈盈地指给我,“再过一个红绿灯,看到一座阜财门,就是古城啦。”
这是一个微笑的海洋:有的佛像嘴眼含笑,温暖祥和;有的佛像曹衣出水,令人一眼佛面,一身释怀;有的佛像慈眉善目,面容欢喜,安心自在……它们的微笑仿佛有种魔力,从千年时光中款款而来,犹如天地间的一股清流滋润心田,瞬间治愈了我。这些佛像大多来自北魏至北齐时代,其实,可以隐隐看到他们身后的幕帷中弥漫着烽火狼烟……
突然想起姥姥的话,“重的东西要轻轻放下。有些苦,笑一笑,就过去了……”北齐工匠把参透佛法和内心喜悦通过冰冷的石头表现得淋漓尽致,它们脸上那不经意间的安然浅笑,告诉我,没有什么能阻止你热爱生活。
一路走出来,瞅瞅时间,还有半小时的富余,打算再走一遍,不得不承认,在青州的日子里,我一次次沦陷在这“青州微笑”里。
(摘自刘吴瑛《一次次沦陷在这“青州微笑”里》)
[点到为止]
笑,是人类最美的表情,也是人类满足、惬意、自适的心理的外露。作者从出土的一尊尊佛像的安然浅笑中联想到尘世间的一张张笑脸,又从这些出土文物想象到其背后弥漫着的烽火狼烟,并由此联想到了奶奶曾经说过的一句话:“重的东西要轻轻放下。有些苦,笑一笑,就过去了……”这些面含微笑的佛像,或许没有让作者改变信仰,但是却让作者收获了人间的至理:人生中有许许多多的苦难,但是只要轻轻放下,一切都会变得风轻云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