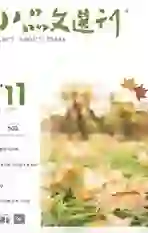怀恋文学
2024-11-07石清礼
要说与文学结缘,还得追溯到我的童年。幼时我即喜爱作文课。每逢老师绘声绘色地朗诵,我总是激动不已。小学四年级时,老师总把我的作文作范文让同学们评阅。于是我的幼小的自尊在老师的褒奖呵护下更是不断膨胀,于是便有了习文之癖。有一次作文,记得是记一次有意义的劳动,我便生涩地创造了“分不容等”这样的别词,后来知道了原本就有“刻不容缓”这个成语。
再后来,“文革”了,学校不再上课,学生也无须读书。我便从学校混乱的图书室借阅了几本较厚的小说:《红日》、《钢铁巨人》、《烈火金钢》以及《鲁迅杂文》等。在许多时日里,我轮番着读这几本书。再后来,图书室关闭了,无奈,我便从邻居同学家借了高年级的语文课本去读。
突然有一天,学校通知学生复课。匆匆到校,便见校园里堆了蒙古包那样规模的书堆。旁边一字排开的是我昔日尊敬的语文老师,当时他们的统称是“牛鬼蛇神”。
同学们集合齐了,校造反派领导宣布:点火烧书。片刻,滚滚浓烟把图书室乃至这些语文老师的藏书都化作灰烬。此时,我感觉,我的文学梦都破灭了。
烧书的火势绝不似点燃别的燃物那样旺盛,而只是一个劲冲散着、喷放着浓烈的黑与白的烟,我趁着烟的掩护,从火里抢出了几册那个年代反映文学动态与文学理论的《文艺报》,趁着混乱,装在衣襟下。
那次离校,我就与学校彻底告别了,当年底,也就是1967年的12月,我便怀揣几册《文艺报》与玛拉沁夫的《春的喜歌》踏上了漫长的军旅生涯。
缘由几册《文艺报》的导引,我的生命历程埋下了文学的火种。那时节,在军营里,除了训练、施工,然后就是“天天读”(领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当新兵时,我几个早上就背诵完了《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剩余的时间差不多都是反复翻阅那几册《文艺报》和玛拉沁夫的《春的喜歌》以及仅有的小说《红岩》……这种空泛但疏淡的阅读依然重新点燃了我的文学激情。我还是不断地练笔,做写生式的日记,或者写点当时时髦的“红太阳”诗。
后来,我居然做了师政治部的新闻文化干事,好像可以堂而皇之地做文学了。然而这种喜悦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就又夭折了。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作为师级机关文学创作员,参加了某军区文学创作班,当时适逢要求写军内“走资派”;面临这个陌生而苦涩的主题,我实在是提不起一点激情来,反倒觉得文学不那么可爱了。于是我一门心思写新闻,写人物通讯,做官样文章。没想到至此丢弃文学,便开始了苦涩而漫长的写作官样文章的历程。
转业地方后,对文学的酷爱还没有泯灭,我依然循着“文”的方位,寻找自己的生存环境。然而现实却又一次击碎了我的文学梦。地方机关要求的不是你能吟花作月,写出什么优美的散文,做出什么小说诗歌之类,而是要你能够驾驭机关公文、领导讲话或是理论研究的文体,为存计,还是弃文从政吧!这种选择与文学竟隔绝了近20年。写了20年官样文章,尽管取得了一些浮名躁绩,但我的感觉是麻木与懊丧。审视我数百万字的陈旧文稿,更深刻地感觉是写了一堆废纸,消磨了大半个生命!
想起文学,心头依然隐隐作痛。特别是步入中年后、岁月迟暮的时候,我清晰地感到:人生最终留给我、陪伴我走向生命尽头的依然是曾经给予我激情与梦想的文学。文学对于我就是全部,我会在迟暮之年重新寻找文学,培植激情去涵养生命。我会在文学的感动中,在文学的陪伴下,度过以后那些难于激动但依然充满希望的岁月。
选自《山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