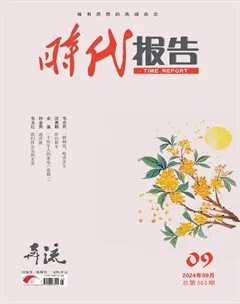一树桐花,暗香浮生
2024-11-06韦忠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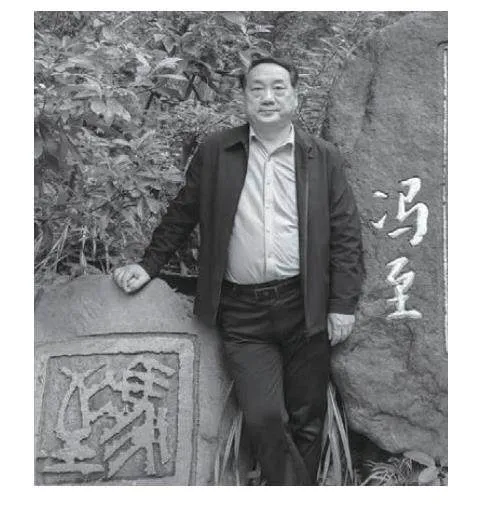
一
在我的记忆里,老家塬上,川下,崖边,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桐树。
小喇叭似的花朵,紫色的花瓣儿微微泛着红晕,妩媚中洋溢着蓬蓬勃勃的热烈。满树的繁花,相拥相依,多而不乱,鲜而不艳,把最亮丽的色彩、最窈窕的姿态、最妩媚的风韵、最动人的芳菲,交给暮春,留给喜爱她懂她心意的人们。
山坡、山腰、山脊,漫山的桐花。那寂寞的白,诱惑的紫,枝枝串串,层层叠叠。春风拂来,浅白的浪花在辽阔的花海里翻涌,顿生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气势。
穿行在桐林里,行人不语,浓郁的花香在空气里流淌。仰望天空,蓝天澄碧,白云悠然。置身花海,素瓣黄蕊感召已被俗世污染的灵魂,一时心灵澄澈,纤尘不染。心里眼里只有寂静的苍穹、无垠的净土、花开的磅礴。
淘气的我,拿一根竹竿,前面做个叉子,仰头对准花团锦簇的桐树枝用力一拧,一串繁荣茂盛的桐花瞬间就在我手里,带回家插在瓶子里,便把春天也带回了家。
桐花一面盛开如锦,一面飘落如雪。农人手掌犁铧,兀自耕田,浑然不觉落花染衣。田埂上的行人早已失了魂,拈花轻叹,慎终思远。
我捡起凋谢的桐花,用舌头舔一下花的根部,甜甜的,再把花朵放在手心,双手轻轻一揉,待它变得软软的,这时候捏住顶端吹一下,“啪”的一声响,吹花嚼蕊的诗意,于顽童便是无边的快乐了。
二
桐花落后,村子里处处桐荫匝地,村子的生活便是在这遮天蔽日的浓荫下一幕一幕上演着:我和小伙伴们在桐树林里嬉戏打闹,玩躲猫猫,尽情地奔跑;胡子拉碴的师傅在桐树下磨剪子,抢菜刀;女理发师把摊子摆在桐树荫下,5分钱理一次头,引来男女老少排成长长一队;更有拉着风箱,火苗通红,“嗵”的一声里,白烟弥漫,飞溅的玉米花是我们哄抢的最爱;奶奶搬来一个小凳,坐在桐树的浓荫下一边乘凉,一边纺花织布;而为了看《地雷战》,我早早爬上麦垛旁的桐树上,抢占“最佳”位置……
村中间,我家新院门口有一棵桐树,有一枝从中间分叉,旁斜长出,如一副平放着的弹弓架子,一直伸出墙外。我便找来一根麻绳,让爷爷绑在分叉上,再用一截圆木头当座,做成了村里的第一个“秋千”。“秋千”荡起荡落,桐树轻轻摇晃,我和小伙伴们在欢声笑语中渐渐长大。
有一次,我和几个小伙伴们去县城赶集,在临近县城的大桥坡下,一辆突突疾驰的拖拉机掉下一棵桐树,我追上去喊半天,终因拖拉机机器轰鸣声音太大,根本没有停下的意思。看着那棵孤独、蹭破皮、横躺在路上拳头粗般的桐树苗,小伙伴们你看我我看你,似乎没有人对这棵树感兴趣。路上行人稀少,我把这棵意外掉下的桐树双手握住捡起,走下路基,把它轻轻放在草丛里。赶集回来,那棵桐树还在。我把它放在肩上扛回了家。第二天,我和爷爷一起挖坑,把这棵桐树栽下,从挖坑、填埋到浇水,一气呵成。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栽树。
没几年,这棵桐树快速生长,看我玩耍,看我上学、放学,风雨无阻,在家门口陪伴我成长。我曾经在这棵树下,弹弓打麻雀,细竹竿、牛鬃逮知了,目睹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景象。又过几年,家里老院子盖了两间平房,为上下方便,爷爷找人把这棵树伐掉,请人做了一副梯子。只是梯子中间踩的横撑用的是硬扎木。小小的我,不嫌费气力,每天搬来搬去,上上下下,爬高上低,忙活不停,乐在其中。而被砍伐的桐树根部竟然又发出新芽。我找来几棵vhaJwEfOMTNae5m1PTmG9jLCe126j0m7tJQggZpyM14=带刺的酸枣枝插在周围,呵护它不被损毁。
正月十五即将来到,爸妈在县城给我买了不同造型和颜色还可以折叠的灯笼送回来,让我从正月十三试灯儿到正月十五每晚都有不同。每每我打着灯笼出去,都会引来大人小孩的注目。不仅如此,爷爷还找来一张桐木板,竹枝扎架子,上面用彩色纸糊棚子,一个轿子花灯便成型。再找来一截鸡蛋粗细的桐木棍儿,锯下四个做轱辘,棚子中间点上蜡烛,一根绳子拴在前面,我拉着走在坑洼不平的村里,小伙伴们羡慕的眼珠子都要掉在地上了。
村里每一家院子大多都有一棵桐树,秋季到来,凡是树杈多的桐树上,收获的玉米穗被主人编成辫子挂在树杈上,堆将起来。既能风吹日晒,又防止鼠类糟蹋。一棵棵桐树,把人们劳作一年的收获扮成了一张张金灿灿的风景,在人间烟火里发挥了作用,在金风秋阳里昭示着丰收的喜悦。
三
有一天,村头石碾空场,出现了一堆粗大的桐树桩,随之出现的还有几个陌生面孔。他们把树桩搬到板凳上,一头高,一头低,上下其人,两人挥汗如雨拉着大锯。还在不远处挖个坑,点上火,把解开的桐木板材放进去。解板、炕板后,匠人们各尽其职,尽显身手,忙活得不亦乐乎。那几天,匠人们吃白馍,喝白酒,吸好烟,东家隔三差五蒸肉、包扁食,做杂混菜好吃好喝好招待,还有主家四方的亲戚拿着油条、点心来“瞧”匠人,村里来来往往,欢声笑语,一下子热闹许多。
我在那个时候,见到了合抱桐木截开的状况,第一次听大人说那一圈一圈的叫年轮,有几个圈,说明树有几岁。
回到家说起这事,爷爷说是人家给三爷做寿木(棺材)。又过几天,一具寿木赫然矗立两条板凳上,再后来,漆匠刷漆,颜色由白变黄,由黄变黑,令人望而生畏的寿木出现在面前。
听大人说,寿木最好的材质是柏木、楸木和松木,因为长得时间久,材质坚硬,防腐性非常好,使用寿命长。但这些一般家庭大都用不起。桐木性价比最好,也最好找,所以百姓用得普遍。只是讲究一些的家庭会在两头用上柏木档。三爷的寿木板材就是桐木,但听说是柏木档。上面雕刻有人物,有花鸟。
桐树陪伴了我整个童年,给予我无限的快乐,它用一圈一圈的年轮让我感知时间,又用雕花勾图的棺材让我感知生死。
四
年岁渐长,读的书多了,我对桐树的了解也逐渐加深,梧桐作为我国诗文记载的最早树种之一,有青桐、中国梧桐、碧梧、青玉、庭梧等,《诗经·大雅》有语:“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桐树更被称为“栖凤之木”。
静心吟诵那些以桐树入诗的篇章,桐树的形象便在我心中更加丰盈起来,
读到耿湋的“桐花间绿杨”句和倪瓒的“门前杨柳密藏鸦,春事到桐华”时,便知春的美丽和青春的美好了,“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中李煜亡国的哀痛,“缺月挂疏桐,寂寞沙洲冷”中苏东坡被贬黄州的彷徨失意,“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中李清照晚年的凄苦落寞,我便知道桐树在众多的诗人眼中原来是凄美的存在,大概是因为桐树叶大,秋来风吹叶落,萧瑟的秋季特征更易于表达人心中的哀愁吧。
五
后来,我作为一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参加洛阳市教育局组织的党务干部培训,有幸成为焦裕禄干部学院的一名学员。这次学习让我在焦裕禄的感人事迹里对桐树有了更深一层意义的了解。
曾经的兰考,风沙肆虐,沙子一起就打毁一片庄稼,一亩地收不到40斤麦子。“冬春风沙狂,夏秋水汪汪,一年辛苦半年糠,扶老携幼去逃荒”是当时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
1963年初春,焦裕禄调任兰考县委书记,刚到任不久便向在兰考插队的几个上海知青请教,确定了种植泡桐抗风沙的科学思路,带领兰考人民大量种植泡桐,如今,焦桐蓬勃地生长在兰考大地上,成了当地百姓发家致富的“摇钱树”,给兰考人民带来了经济财富,更在精神上带来了绵延不绝的财富。
50多年过去,焦桐早已成为兰考的地标。它宛若一座丰碑,无声地激励和鞭策着兰考人,更将焦裕禄鞠躬尽瘁、服务人民的精神广播远传。
春风拂面,又是一年桐花开。一座以焦裕禄命名的干部培训学院拔地而起,焦桐树下变成了小小的广场,每年,大批参观者、学习者在焦桐树下聆听焦裕禄的故事。与人民群众的血肉之情,成为焦裕禄精神镌刻在这片土地上最深厚的印记。
人们说,“看到泡桐树,想起焦裕禄”。泡桐能吃苦,沙窝子里也能扎根,并迅速根深叶茂,挡风压沙,这是焦裕禄为治理“三害”找到的金钥匙。坐在那把有个大窟窿的藤椅上,他写下生命中最后一篇文章的提纲,题目是《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临终前,他留下一句话:“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在焦裕禄干部学院桐树林里,我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栽下的一棵桐树下伫立,难抑心中的感动,吟诵着总书记1990年词作《念奴娇·追思焦裕禄》: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
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路漫漫其修远兮,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
吟罢抬头,再看桐树林立,我深深地感到一个共产党人、一名教育工作者肩头的沉重。
六
2019年,我和桐树又一次结缘。
春季开学不久,几位退休教师到学校找我,反映家属院里原有一棵桐树,是建校那年大家亲手栽下的,陪伴了他们40年,由于树身中空,有安全隐患被砍去,现在那里空荡荡的,老人孩子出来连个歇凉的树荫也没有,希望再种一棵,我当即答应,并立即安排。
三天以后,一棵来自豫东、拳头粗的品种桐树到了洛阳。
我邀请了几位退休教师代表一起挖坑,培土,浇水,一棵新的桐树在家属院里栽了起来,我给这棵桐树挂上了一块牌子:育才,旨在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栋梁,选拔人才。
现在这棵桐树已经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成了家属院里孩子和老人们乘凉避暑的好地方,也见证了一批又一批附中人的成长和发展,它静默伫立,一如附中对学子的守候、守望。
至此,距离故乡里那棵我儿时种下的桐树,已匆匆四十余年矣。
一棵树,众人心,万人情,一种情愫,万般倾注。
两棵树,亭亭如盖,同心共情,涓滴暗香,注解浮生。
作者简介:
韦忠民,河南省洛阳市洛宁县人,中小学高级教师。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南省文艺家评论家协会会员。公开出版诗集、随笔和小说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