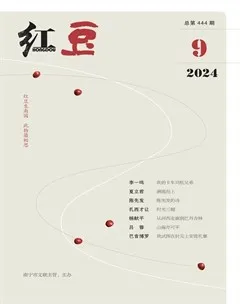直面生死的记忆诗学
2024-10-30王迅
以记忆诗学拉动叙事是众多小说家的选择。尤其是女性作家,以记忆的闪前和闪回调度叙事节奏、开掘人物心理,是小说写作中的常见策略。当代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林白就是依赖记忆诗学,打开了女性书写的另一种向度。林白小说中的N城、W城、B城都留存着她的人生足迹和生命气息,写作于她而言无异于搜索记忆。记忆碎片的拼贴与重组,构成林白书写女性生活的美学机制。陕西女作家吕蓉的短篇小说《山海亦可平》亦可视作此类作品。尽管小说中的主人公是男性,但其情感过程无疑包含了创作主体的生命体验,而且尤为深刻。作者以直面生死的姿态探究主人公内心的伤痕,呈现了其从昏暗走向新生的艰难历程。
从题材来看,故事的讲述在家族成员之间展开,似乎可以归入家族叙事。然而家族利益纠葛与情感冲突并非小说叙事的重点。由于短篇文体的限制,作品没有《白鹿原》那样宏大的叙事气象。作者把主人公放到家族背景中考察,通过他与姥爷、舅舅的故事引出他的家庭变故及个体不幸的遭遇,以此来重审自身。说到底,小说所探究的是主人公精神病态的成因及疗愈的可能。作者就像外科大夫,就着主人公的病象层层解剖,在生与死的界线上探索,破解生命的谜团。
首先,小说以一幅颓废的画面开启叙事,为故事情节的发展奠定了暗淡的基调。陈海山自我封闭十年,过着一个人的生活:“他就像是一棵植物,在那间小屋里牢牢地扎了根。”看到这样的画面,读者必定会追究主人公精神悲剧之成因,期待作者为我们揭开生命的谜团。当然,这个画面只是一种提示,它意味着累累伤痛与惨淡人生。从写作来看,它也意味着记忆诗学在此类小说叙事中的分量。只有借助记忆碎片的打捞,把过去的伤痛与温情链接在现实的画面中,故事的发展才有了逻辑的支撑,人物的精神裂变才变得真实起来。
其次,短篇小说的文体性得到彰显。短篇小说的篇幅不容许枝蔓横生的故事情节,也无法承担复杂的人物谱系与重大的宣教功能。写作者必须集中精力勾勒“横截面”,以此展示人物内心的秘密与精神的历程。事实上,这篇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主人公陈海山与杨妍自由恋爱,但陈母提出杨妍的听力障碍,可能源于遗传,怕会影响后代。无奈之下,陈海山与杨妍分手了。而两人相爱之深,加之单位同事的议论,让陈海山痛不欲生,这直接导致其精神的陷落与自我封闭。如此,在封闭的空间迷恋上网游,以至因网络诈骗而输掉母亲所有的积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当然,情节的推演并非作者的目的,而是想说,作者对短篇小说文体的理解是到位的。这篇小说并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而是以追忆的手法切开人物的内心,在“过去”与“现实”的缝合中见证了生命突围的奇迹。
再次,在生与死的界点上拷问主体的心智,是小说出奇制胜的叙事策略。作为青年作家,吕蓉对生活的思考不只于社会生活的表象,而是向着生命伦理的深处掘进。对生活的观察浅尝辄止,是青年文学创作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青年作家走向成熟的主要障碍。当然,随着写作的持续和认知的加深,这种情况必将有所改观。在这种形势下,吕蓉对现实题材的驾驭及其敏锐的观察力是值得关注的。直面生死的姿态,以及在死亡的凝视中咀嚼记忆的温暖,为小说主题的深化提供了可能。姥爷垂死挣扎及其强烈的求生欲望,为主人公走出颓废状态提供了精神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人物关系的拿捏极有分寸,亲疏有别,为小说人物的情感发展轨迹提供了真实的艺术刻度。在短篇小说的限度下,作者以简省的笔墨勾勒陈海山与姥爷朝夕相处的诸多画面,让主人公目睹死亡来临之际个人的无助,也让他感受到一个人在生命垂危之际所迸发出的巨大能量。然而,作为抑郁症患者,陈海山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去照顾生命垂危的姥爷?仅仅是迫于亲情伦理吗?从小说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可以看出作者对人物情感发展逻辑的把握是到位的。这是考验一个写作者的重要尺度。让我们先看看小说中亲人对姥爷的态度:
他们说姥爷不负责任、自私。当年在农村,姥爷上过小学,属于那个时代的读书人,也就当上了干部。他当干部家里没落到一点儿好处,倒是把家里的三间破屋、十几亩地、两个老人、两个孩子,还有同样张着嘴要食吃的牲口都留给了姥姥。
姥姥挨打却默默承受,任劳任怨,临终之际也未得到姥爷的好脸色,母亲对此颇为不满。舅舅因为姥爷嗜酒如命以至影响到高考而怨恨在心。总之,姥爷在家人眼中是自私的,不负责任,也没有担当。由此,面对这样一个长者,即使其生命垂危,舅舅也显出无动于衷的态度,我们就可以理解了。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姥爷就此定格在一个坏男人的形象里。然而,作者没有就此粗暴地打发一个人物,而是通过陈海山与姥爷的关系,写出了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借助主人公的回忆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姥爷在陈海山记忆中却展现出另一副面孔:
他记得那时的姥爷,虽然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朴素的衣裤永远都是干干净净、平平展展的,冬天的时候,戴一顶呢帽,配一条格子围巾。当时姥爷快六十岁了,头发却像年轻人一样茂密油黑,梳成整齐的三七分。姥爷看到他了,冲他眨眼一笑,总能从口袋里掏出点儿小惊喜——有时是零食,有时是小玩具。
这是外孙视野中的姥爷形象:尽管农村出身,却穿戴整洁、干净,还不忘打扮一番。像这样的段落,小说中还有很多。比如写姥爷带着他去村边河里游泳,去看马戏,给他讲久远的故事,等等。姥爷带给他的是“沾染着泥土芬芳的欢欣”,在他生命里是难得的“轻灵一笔”。这个形象与舅舅、母亲视野中的姥爷形象形成反差,但我们读起来,一点儿也不觉得生硬和失真,反而觉得无比鲜活。在吕蓉的记忆诗学里,过去的一切都是复杂的存在。如果说家族记忆中的姥爷是记忆的阳面,那么,陈海山眼中的姥爷形象则是记忆的阴面。主人公的叙述激活了历史,将单向度的人还以血肉,那个被遮蔽了的真实生命便浮出水面。
无论如何,这是小说中的重要一笔。童年的记忆唤醒了陈海山,促使他把最后岁月里的姥爷当作值得尊敬的长辈去孝敬,给予细心的照料。在这里,小说在人物的情感逻辑上实现了贯通,让读者意识到主人公与姥爷的关系,是作为小说叙事的伦理来维系人物内心的走向的。这里隐藏着叙事发生的契机。儿时记忆的复活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主人公落魄而颓废的精神状态,为其新生提供了逻辑起点。
从阅读心理学来讲,对一个不幸的主人公来说,读者的兴趣点往往是这个人物的过往,是导致精神创伤背后的那些的故事。对此,吕蓉当然明白,但她并不急于揭开人物的伤疤,而是在作品后半部分才再次打开记忆的开关,徐徐道出主人公不幸的遭遇。按照常理,这一部分的叙述,信息密度相对较大,叙事节奏也相对较快。事实上也如此。作者仅仅留出了两节的篇幅,匆匆带过。然而,这是一个成熟的写作者,在细细思量后做出的决定。小说叙事的核心层次,已经被作者定位在人物内心秘密的揭示。这是内向型叙事,因而也是更现代的关节点。其中所潜藏的叙事智慧,来自作者对现代小说艺术的领悟,极大提升了小说的美学品格。
写什么,不写什么,是评判一部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吕蓉把人物的精神履历作为叙事的核心,不断强化心理演变的逻辑。这表明她把小说当作心灵的艺术来对待,而放弃了传统意义上讲故事的套路。主人公的心理症结缘于母亲对他的“放纵”,正如姥爷所说,这种“放纵”的养育方式并不适合男孩。多年后与前女友重逢,杨妍同样对此做出了指认:母亲保护得太好了!当然,之所以如此,缘于母亲内心深处对儿子的亏欠,缘于之前那一次显得“不光彩”的离婚,这是她面对儿子的天然软肋。同时,母亲对儿子的“放纵”,又直接导致了自己病危无所依而亡的凄凉结局。对母亲的冷漠以至失去了亲情的本能,这又何尝不是陈海山所欠下的一份心债呢?这种心理敷衍的叙事格局一直持续到小说的最后。那么,也许有读者要问,与弥留之际的姥爷相守多日,激发了与母亲及姥爷相关的诸多记忆,这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解开主人公的心结呢?我们不得而知。小说结尾并未显示陈海山是否走5zUF7fMMi1qjIUCKCKXhx5OowSEe2WZq4gLdWSZvIpM=出人生的低谷,抚平心中的“山海”。然而,扶姥爷拄拐杖下楼看花的细节描写,已经恰到好处地做了暗示。其中所预示的,是一种精神力量的接力,是希望之光的照射,自然也是生命复苏的迹象。
【作者简介】王迅,文学博士,评论家,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四批客座研究员,日本大学残雪研究会会员,浙江散文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在《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民族文学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争鸣》等发表论文二百余篇。多篇作品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论文获奖十余次,出版专著《不必等候炬火》《麦家小说论》《浙江散文现象研究》等五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等四项。
责任编辑 练彩利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