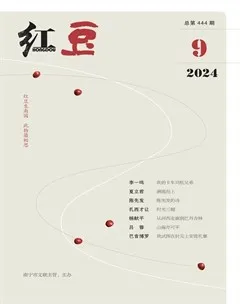俄贤岭叠奇
2024-10-30杨道
立夏之后,时序更新,但东方市的城区和郊野的阳光仿佛停滞了,暑气压着土地。我坐在开着冷气的车里,看窗外忽闪而过的人行道,扬起一些沙尘,阳光落到沙尘上,一道犀利的银色弧线横贯天空。在更强烈的阳光到来之前,车进入了俄贤岭的山门。
九峰山
俄贤岭另名俄娘九峰山,沿昌化江中游东北岸蜿蜒,是海南现存面积最大、原生态保存最为完整的喀斯特地貌原始热带雨林。
进了山门,俄贤岭的九座山峰遥遥在望,曲折连绵,在草叶间若隐若现,恍如我们图腾般的祖先,走过远古大地时,在自己的脚步之后撒下了一串文字与音符,这些文字和音符与特定的大地连接起来。
车在乡间行驶,向东、向南、向东,驶到一个拐口。拐口处一块平整的空地,背倚东方广坝湖,湖上风景如宋人画卷,远山近在咫尺,相对而出,近景的湖面,盛着明亮的光影。此时尚未近午,阳光温和些,远峰是带状的缥缈,俄娘九峰山之九峰开始显露一些可爱处。凡山水风光之美,不在于土地尺幅大小,车往前走,人的目光便从大、高、远的境界,渐趋小、低、近的精妙细微。
山有三远,因为大广坝与广坝湖的调剂,九峰山高远之色渐渐清明,由东北而向西南,山势绵延起伏,山峦间坡岩交叠状如云卷,奇异处在于其间确有流云卷舒。车至“仙龟拜峰”景观处,阳光愈烈,九峰山于烟岚中露出尖状鸟喙。这鸟喙类凤,忽隐忽现,让我想起柳三变的羁旅词《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是柳永怀念恋人的作品。这里的柳永因思念已近乎痴狂,他日渐消瘦衣带渐宽。一个春日的傍晚,微风习习,词人伫立于高楼上,凭栏极目远眺,想在目之所及内看见一些想看的景色。我们无法知晓当时的柳永想看的是什么,再看天边,他心里生起了点点春愁,眼里的所见之物,也因之沾上了淡淡的愁绪。此时烟雾迷蒙,残阳斜照芳草。其实,此时残照里最惹人遐思的,是词人长身独立的身影。我们无法明确引起词人愁绪的人或物象,但他后来对酒当歌、疏放求醉的方式,让我们了解了他内心因思念而生的愁苦。而词的最后两句,对于爱情的执着极具感染力,它被王国维称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所必经之境界,并最终成为关于爱情的千古绝唱。
759760e83fed2bb860458cb8a41d2ee6峰下小山葱翠,湾为俄贤湾,当地人称湾中小岛为蓬莱岛,蓬莱岛便自有仙龟游弋。而与九峰山遥相呼应的是我背倚的一面山坡。山坡上一巨石状如唐时大诗人杜子美,衣袂飘飞于大片树林间。初秋俄贤岭的草叶,被硕大而刺眼的阳光压得有些消沉,那些热带羽状复叶也没有更好的抵抗办法。倘若杜子美先生来了此地,这些像是死去的干树枝,也许会陪着他一起等着春天突然冒出来的新鲜粗壮的嫩芽。
巨石“杜子美”隔着俄贤湾与九峰山两两相望,不下堂筵,坐穷泉壑,而来来往往的东方人,却没想起借这巧合给杜陵野老与东方添些羁旅逸事,显见了他们的务实内敛。这或许便是俄贤岭“贤”之所在,山川原是通了人性的。
草木深
这真是一个阳光过分热烈的正午。当我开始踏上俄贤岭林间的栈道时,有山泉滴落的声音从森林深处传来,我整个身体在听到滴水声时就像中了魔法一样,仿佛长成了优雅柔和的青翠枝叶。我在这大自然间拾级而上,我觉得林中万物都很亲切。荡漾的微风送来一些飘忽的鸟的歌声,栈道两旁的石头垒成新生溪涧的和声乐器,雨水充盈的季节,溪涧在石头缝里歌唱。我来得晚些,八月的东方,雨总是稀罕,一些溪流开始变得干涸,阳光照射水流过的印迹,蜿蜒曲折,如飞天的银色腰带从山顶翩然飘落。
八月的阳光始终在施展它作为调色板的天赋,它使俄贤岭看起来像一座墨绿色的高树林,一座由树叶和树枝形成的富有变身魔法的山。它由无数的草木与花枝组合而成,风来得猛些,枝叶摇摇晃晃。
海红豆的枝叶常常从栈道围栏的缝隙探过头来,羽状的复叶在风里微微摇动,披针形的花瓣看起来防卫性很强,但我还是忍不住伸手触了触。童年时代,看海红豆荚果开裂的过程就像在欣赏一次奇妙的艺术创作,荚果摇晃着,而后一声脆响,荚果突然爆裂开来,露出红艳艳的润泽的豆子。它的红由边缘向内部逐步加深,最里面特别艳红的部分则呈心形,可谓心心相印。故而认识它的诗人们,便给它取了更富情感的名字“相思豆”。被赋予“相思”意味的海红豆,平白地就长了一副天使的面孔,从荚果裂开的门里,伸出一双圣洁的手,递出爱情或者友情的信物。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我们的诗佛王维咏颂红豆的这首名诗,随时被相爱的人们提起。鸟有相思鸟,树有相思树,豆亦寄托了无限的情思。相传古代有个少妇,因思念出征战死于边塞的夫君,朝夕倚于门前树下恸哭,泪水流干了,眼里流出了血,血泪染红了树根,于是就结出了具有相思意义的红色小豆子。
豆有相思意。王维的诗《相思》起句因物起兴,语虽单纯,却极富想象,全诗情调高雅凝练,情思饱满奔放,语言朴素无华,韵律和谐柔美,故而诗一出便传唱不衰。此外,唐代绝句名篇经乐工谱曲而广为流传者甚多,王维的《相思》就是梨园弟子爱唱的歌词之一。
在俄贤岭,移步可换景,其间草叶、老树与随处纠结的青藤枯藤总会让人想起王摩诘,他晚年居于蓝田辋川别墅,画人物、丛竹、山水等,他以破墨法画成的名作《辋川图》,似乎能见得些许俄贤岭的烟岚。苏轼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或许由此引申,俄贤岭的风景,是入得诗佛的诗画的。高大的老树伫立在一块稍微凸起的土地上,一些树冠倒垂下来,大地寂静,它们也静止不动。它们没有血液,它们没有神经,但它们的浆液凝结了时光,它们不声不响地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无论多大的风雨,它们都被钉在原地。它们不是狮子也不是蛇,它们没有动物那样灵动的躯体可以逃走或者进攻,它们就这样默默地坚守着。于节令而言,八月已经入秋,在我遇见俄贤岭第三棵高大的海南梧桐时,感到空气和流云都在奇异地鼓胀——那种努力是憋住的、几欲喷薄而出的快乐。几片心形的梧桐叶从枝头落下。秋在梧桐落叶中,果然是的。落叶渲染了山间的基调,下午却有着夜晚的所有宁静,四周有啁啾声,也许是画眉在歌唱。阳光透过梧桐叶,在栈道上投下光线和倒影。几根长而粗的藤条穿过后山的大石扭结而来,越过新近生出的小树丛,与栈道上的旅人一起仰望更远更高的蔚蓝色山岭。
关于梧桐,我们从古诗词里读到很多古典的意象,而海南梧桐与古诗词里的梧桐是“血缘”上的近亲。海南梧桐树干高大直立、苍劲挺拔,在开花季,枝上一团团的白黄色小花,风微动,小花烟雾般飘散于半空中,正如“一叶梧桐如唤客,起来搔首听秋声”。宋时诗人苏泂就用这么一片梧桐叶,唤来了秋声。
在《诗经》里,梧桐是凤鸟青睐的栖居之所。“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家有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俄贤岭有梧桐树,自然引来了它的凤凰——海南梧桐新飞来的叶瓣,就落在了俄贤岭山顶上的洞口。
花梨录
在俄贤岭脚下,一家黄花梨山庄,漫山的花梨树成排而列,波浪般的树枝,在阳光下荡漾起伏。有风来,枝叶在微微晃动,柔软、翠绿、阴凉,细碎的阳光落到花梨叶上,像小精灵的眼睛一样闪闪发亮。
同行的友人与曾经的庄主是故友。曾经的庄主是外地人,当年对这片土地一见钟情,便留了下来,开垦土地,种植花梨,在山庄里辟了湖,建了花梨工坊,往来的旅人可以真切地触摸花梨的肌理,这是切实的福气。如今十多年过去了,原庄主已年近古稀,这花梨山庄也易了主。但老人舍不得这土地,便一直住着。老人说,他已经是这庄上的土著居民了。
这是一个平静的下午。我们坐在玻璃房里,看玻璃外湖边的花梨。湖是地球的眼睛,花梨枝是它纤细的睫毛。我在凝视湖水时,看到了那些睫毛的颤动。空气里饱含着一种圆满的宁静,太阳褪去了它的辣和神秘,对面墙上的时钟在柏木槌的撞击下发出深沉的旋律。
从前的东方人似乎毫不费力就过了一辈子,农耕、捕鱼、读诗,枕着花木听海潮。花木在滩前川上都有,老了的树根不知怎么就成了家里的神龛,渐渐地蒙上了灰尘。子孙在休憩时把灰尘掸了下来,灰尘在午后的太阳里飞舞着。有人在这回忆里闻到了花梨木的香气,淡而清雅,像记得兜兜转转的快乐,也像茶的氤氲,缭绕着许多的意味。
在许多记载里,都说明清家具使用的多是花梨木,事实上,从唐代开始,就有用花梨木制作龙床的传说。传说里花梨木由海南运出,须经近一年的时间才能到达京城,除了皇帝下榻的龙床,他人是不能够享用的。明清时期,花梨木似乎更趋近于一个集万千宠爱的奇女子,在宫廷和官宦的家中高居正堂。而此时的海南花梨木,仍旧是皇宫的珍品,除了皇帝,其他无关的人万不能睹其芳颜。
花梨木是有新老之分的,大都色彩鲜艳,纹理清晰。新的花梨木据说颜色浅黄,有浅淡的香味,是明清家具的主要材种,但因其色泽纹理粗糙,始终也得不到皇帝的珍爱,便流落到宫外的官宦家里。老的花梨木,便是极受皇家宠幸的生于海南的海南檀。海南檀木色金黄而温润,不张扬,芯材的颜色另有他样,多是红褐色也偶有深褐色,其间的纹路似乎都存有清幽的香气。海南檀的比重较小,说是质感极好,底子里其实是坚硬厚实的,且其纹理从容淡定,如行云流水。奇特的是,木纹中还常有许多木疖,木疖大都平整,没有裂缝,纹理却常现出狐狸头、老人头及老人毛发的形状,妙趣横生,这当是人们极爱的所谓的鬼脸了。
几年前,一个朋友说看过他老家当年一户有钱人家的花梨木四柱床。这张床应是晚明或是清初的作品,它由床罩和床身组成,两侧面和后面挂檐及床帷子都用四簇云纹攒接,整张床显得端庄秀丽。正面挂檐镶着两块透雕的板片,刻着传统的吉祥图案双凤朝阳。正面围子透雕的图案他看了半天没看出是何种动物,有一种类似少女的巧笑倩兮。厅里还有花梨木制作的四足香几和雕着“寿”字的扶手椅。据说这家人在解放战争时就人去房空,有一些远房的亲戚偶来打扫灰尘,但后来那张四柱床还是丢了,没有人追究过它的下落。好在那香几和扶手椅留了下来,成了文物,但过去的总归是一种不能忘却的记忆。
因为好奇,后来我赶了几百里路去拜访朋友说的那户花梨人家。绕了几条山道,村庄就躺在昌化江边上。一些山,一些水,一些石墙,主人迁居国外多年,这房子空荡荡的,早就没了烟火气。庭院很宽,石墙边婆娑的椰子树和杧果树的枝叶在半空中叠层相接,郁郁葱葱的,偶有几片发黄的叶子夹杂其中,彰显了田园的宁静与瞬间的寂寞。听到说话声,看守庭院的老人从左侧厢房走了出来。老人热情地邀请我们一起品尝他儿子送来的点心,却不让我把任何物品放到花梨木的香几上。香几当年主要用于置放香炉,几个面都用四段弧形大边攒成圆框,并打槽装上了面心板。束腰下的牙条浮雕卷草纹,以插肩榫与四弯腿相交。香几的腿足细长,足底翻出云头。这种细节的繁复,显现了当时最闲的人的生活态度,只有他们能领略到其中的妙处。制造这许多种图案,实在是需要艺术和时间。
我不大能够想象过去的世界,譬如那张遗落了的端庄秀丽的床,上面睡着的,一定是个美丽温婉的女子吧?可清朝三百年,女人好像是没什么时装的,都是宽大的衫裤、紧窄妖媚的水红小袄,据说睡觉时也不脱下,生生就让这美丽的花梨木床冤屈了去。据说当年宫廷里的这些花梨床,都取材自海南,而皇帝的龙床,必得由俄贤岭的黄花梨所制而成。
花梨山庄的主人给我们添了花梨茶。花梨茶的颜色是混着暗沉的清透,须得分几个层次来饮。初入口,先观其色,汤色如琥珀,有明亮金圈,香味独特,滋味更是醇厚,而茶韵浓郁;喝第二口时,会感到淡雅柔和,香味独特,入口回甘,且甘暖不涩;第三口则是细品其意,悠然自得,青的汤色映于眼帘。我品着花梨茶,听友人和他的故人坐在时钟的嘀嗒声里聊天。他们的话题一直散漫,绕着这些年花梨的行情和各自的人生际遇。老人说得很慢,想起来就说一句,像滚烫茶水中回旋的清叶,缓缓地浮泛着。半掩的门里悄无声息,仿佛一切还在远处,没有醒转。
云水谣
我们到南浪村去寻找那棵最老的花梨树。南浪村里的小路,都长着齐整的花梨树,每一户人家门前,都有至少两棵花梨树矗立左右,仿佛忠实的护卫。村里没有围墙,每一户人家的庭院都敞开着,房屋墙脊砌以青砖明瓦,白的墙。我们在两两相接的翘起的屋檐下行走,穿过狭长的小巷,眼前豁然,别有天地。
这是一座过于粗糙的关于花梨的园林。大大小小的花梨树随意散植其间,年岁最高的两株花梨树被铁丝网围了起来,人只能站开了仰望。园主人听到声响,开了后窗,探出头来招呼,说这棵花梨树现在是被保护的文物了,常常有人远道而来,就为了看它一眼。
这棵老去了的花梨树显然淡定了许多,它像人一样直立,巍然不动,根深深地扎入泥土之中。它的枝柯在碧空里伸展,盛接细碎的阳光,在漫长的炎热岁月里,它的枝叶怀着无限的喜悦,四处延展,宛如柔软却又倔强的草茎,服从大地的安排。它喜欢平展展地伸向天际,像月亮那样仰躺在最纯净的光影中间。我决定前往村子背后的俄贤湾。一只黑狗突然从园子的后山跑出来,气喘吁吁的,它远远地打量着我们这些外来者,大概在斟酌它应该摆出怎样的姿态。园主人拍了拍它的脑袋,它转头看看我,摇了摇尾巴,算是问好吧。
俄贤湾是广坝湖的一个分支。这片被当地人称为小桂林的山水,其实美得也很细腻与和谐。它的周围是一片山峦,奇峰突起,九峰山就隐在帷幔一样的烟云中,下临深涧,通达其间。山脚沉浸于湖湾之中,湖面半覆金色的夕照,湖中有岛,倒映于一湖碧波之间。岛上山石嶙峋,枯叶纵横,恍如天地混沌初开、水岩奔驰的景象。铅灰色的荒石裂缝交错,绿枫树虬曲的枝柯就立在荒石中间,看上去面目沧桑,却也寥廓而纷繁。苍茫暮色中,俄贤湾与九峰山、湖中荒岛以及落日,形成了神秘之谜,宛然秋日幽深的辞章。
俄贤湾的风景并不算十分壮丽,但它与我的理念很和谐。当我站在游船上往湖湾深处行进的时候,风用它的语言与我交流。这种交流像魔法一样,我不需要用船桨敲打船帮,也能激起回声。那声音在九峰山和湖湾中那些野岛的树林中萦绕扩散。夕阳的余晖落到水面上,越拉越长,半湾瑟瑟半湾红,湖湾下静卧的森林碎木的影子,和着暮色里的山坡山谷,都欢叫了起来。
当风荡起波浪时,云在天上被扯成了碎片,霞光把它们往湖湾深处拖曳。我在船上看到的水面反复起着褶皱,水随着夕阳的颜色发生着变化,一会儿蓝,一会儿绿,它栖息在俗世和天堂之间,共享俗世和天堂的颜色。
在俄贤湾,天空的颜色是没有修饰的蓝,夕阳铺在水面上的暗败的金色凸显湖湾与蓝色天空之间的旖旎私语,长尾狐或者火鸟一样的白云在山峦间飘来飘去。我们的船越过一座裸着岩石的岛,不远处就是码头。一些灰色的云在小岛头顶上浮动,像是大小犬星座在守护着点点群星,它们的倒影在水里摇晃,夕照的光芒在湖湾上形成波纹斜线,一片光辉。
船从俄贤湾深处返航时,我远远地看见九峰山顶上的云渐渐地添了些铅灰和蜜的颜色。在水的波纹中,我看见身后的太阳正悄悄地落下去,这时我眼前的九峰山缓缓地耸立起一座长长的山峦,夕照和山峦把水面划出一道界限,我隐约看见夏日太阳的旧影。船继续朝前走,水波不兴,万籁俱寂,我甚至想光着脚走在这镜面世界里,或者仰躺在镜面上,看天空中忽隐忽现的粗糙的空气颗粒,它们像悬空织网的蜘蛛一样,沿着神秘的路线进行古怪的飘移。一些类似布谷鸟的叫声从九峰山深处传来,听上去十分清晰。一轮苍白的月亮从山峦中那蜿蜒曲折处悄悄升了起来,其清冷的眼睛在涟漪中不断复制。
蓝色的天空在浅吟低唱,蓝色的湖湾用尖亮的嗓音唱起它的落日之旅。八月的黄昏,天气开始转为宁静温和了,日子变得迟缓、明亮而灵巧。这个激变是在湖湾与白云亲近的瞬间发生的。光亮突然充满了我的眼帘,尽管天色渐暗,夜晚即将来临。九峰山山峦间飘忽的白云,像扇动翅膀的黄莺鸟,它在山峦间自由地飞翔,仿佛宇宙间全无他物,它的巢就筑在那白云的角落,用夕照的金丝与湖湾袋装的褶皱编织而成,点缀着地上渐趋清凉的初秋柔和的雾霭。
我们的船在平静的水面上航行,在落日剩下一抹余晖时,我们抵达了岸边。暮霭中一群牛在一长溜的草地上吃草;一户人家随意坐落在空旷的草地上;庭前树下的吊床里躺着闭眼小憩的旅人;悠长的黎族民歌从湖湾深处翩然而来,那曲调仿佛携着清水和细沙,和蓝绿色的湖、黑而凝重的山峦、飘忽的白云搭配得浑然天成;几个孩童抱着椰子在玩耍,被剖开的椰子,散发出一股家乡的仙气。
一溪云
在前往俄贤岭的旅途中,因为天空都是满屏的云,我爱上了两种颜色:云的白和天的蓝。这爱来得缓慢,好像需要经过一番思考,以显出它的庄重和长远。
从《说文解字》对“云”字的解释中我们了解到古人对云这一自然景物,有着更多细节的发现。云之变幻本是一种自然现象,无论天气阴晴与季节更替,云都会在天空中游走。因其有独立的姿态,散淡飘逸,自由闲适,因而成为文人墨客吟咏表现的对象,并借之抒发自己的情怀。
云的意象历来为诗人们所关注,在中国的古典诗歌里,运用云意象的诗句比比皆是。我最早对“云”感到惊喜的是读《离骚》,当时觉着云里的仙气,如此飘忽不定,充满魅惑:“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事实上,这两句诗中的“云”,是作为神话世界中仙人抵御外来入侵的防御工具出现的,具有某种人格象征的意味。但我在初遇此句时,觉着满纸都是中国古典最富奇思的玄幻色彩,惊喜不已。而此次俄贤岭的云,把这份隐匿了二十多年的惊喜,重新续上了。
我喜欢满目的白云,它能随时变身,如游龙或者鸣凤,有时它甚至可以盘旋为海马的形状,一种薄的声气应和,在天空更宽大的蓝色中努力被迷惑。每一朵白色的云都可能是海妖身上一袭白色的裙子,海妖的内里在燃烧,就像山林里着火的灌木,钩着那些芜蔓的枝叶,把所有的想象都飘拂起来。一些云落到芭蕉叶上,像白色油布把整个宇宙都罩在了炽热的光圈中,需要一种类似博物馆橱窗里的密码,来标志区别于人类俗世的欲望。
前往俄贤岭的路上,我想把天地间的白云都收入篷窗一样的手机里。广坝湖上,落了三四点白鸥,与九峰山的青绿形成应和之势,恍如画家数笔绘出的横塘夏意图。芦花摇曳,清淡的云影飘浮于邈远的蓝色天空。我总是想着,等这阳光减些声势,就把这一半烟水和白云剪回家。古时词人就偏爱素淡平远的风景,譬如蔡伸说“落日归云,寒空断雁。吴波浅淡山平远”,这是人极自由的一种状态。望向长空,云间自有色彩晕染,人的眉眼便盛了湖间声色,如同斜风细雨的宋词,描了半阕的旖旎白玉。
而白云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是一种象征性极强的符号,“白”有圣洁之意,可代表纯净之心;而云之飘忽,迎风起意,南来北往,自由而闲适。故中国古人隐士的诗词里,断不能缺了关于白云的吟咏。譬如陶潜,他一生贫穷,“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却始终与酒与云为乐,“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他曾出仕三四次,终觉心为形役;四十一岁时,他辞掉了彭泽令,从此远离世俗世界,开始了自己后半生躬耕隐逸的自由生活。陶潜和他的诗都是我极喜欢的。他诗里阐写的云、鸟、菊和酒,是我关于魏晋隐士生活的所有想象。其实,隐士的标签是后世安给陶潜的,于陶潜自身而言,归隐只是服从他自己心灵愿望的一种选择。他要做独立于流俗之波的中流砥柱,他对自己的人生选择表现出坚定不移的信念。
我走上俄贤岭的栈道时,已近正午。阳光肆无忌惮,云也不怯,带着一种奇怪的自由在我头顶的枝叶间来来去去,与山林浑然一体。我感觉整个身体都凝成一种感官,每一个毛孔都沁透了愉悦。我对于云和草叶总是异常亲近,并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陶潜那些关于云的诗句和意象。
摆脱仕途生活后的陶潜,回归到乡村田园,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然而此时的诗人在精神上是孤独的,他没有可以进行精神共鸣的朋友。于是诗人在古代圣贤堆里寻找知音,“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后来陶潜与朋友惜别,作了一首《于王抚军座送客》,借云的意象来表达自己孤苦惆怅、无可皈依的处境。在陶潜看来,自然已是凄风苦雨,与朋友别离更添凄苦,这样的双重伤感,令诗人心情沉重。而此时,山涧中的寒气云蒸而起,孤独的游云四处飘荡,无所皈依。
与前代诗歌中云的意象相比,陶潜是创造性地丰富了云的内涵,譬如,他用“白云”来表现自己对隐逸生活的向往,用“孤云”“游云”的意象来表现自己高洁傲岸的节操。总之,他和他诗里的云是浑然一体的,他的人格性情、抱负追求以及所处的时代风云,都借助云的意象得到了生动的展示。与此同时,他的人格魅力及其背后的精神向度也得到了具有丰富而广阔意义的阐释。
我倚着俄贤岭一棵高耸的重阳木,望头顶上的白云,想起我们海南人最喜爱的那位北宋文学家苏轼,他是陶潜的粉丝,他的终极理想似乎也有着陶潜的影子,他甚至在他的《行香子·述怀》里做了坦率的表白: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
虽抱文章,开口Uipm6licIJw4iuups8cLBcmlCixRoVn6c4qFHosPCXU=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这是苏轼描述他自己老去后想要的一种生活方式。苏轼从未厌弃人生,他生性乐天旷达。人生原本短暂,回首望,一切皆为虚无,与其浪费生命去追逐名利浮云,不如做个闲人,对一张琴,倒一壶酒,听溪水潺潺,看白云浮动。
这个正午,在俄贤岭繁茂的林间,我也看到了这样的一溪云,我想给她赋上我自己对云的修辞(《一溪云的修辞》):
小片的云的影子突然印在明亮的湖光中
我在一片草叶的背后看到
我们朝着我们的生长
如同你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
你一直栖息在词语上面
东篱把酒,暗香盈袖
我听到你散落在湖边的几声低叹
疏帘铺淡月,好黄昏。枕隐流年
秋到窗前十里青
夜里被放牧的记忆有你余温的辞令
每一个修辞其实都是幻影
熟睡于云的航海图上
月亮的黑暗睡去又醒来
悬挂在奔涌的夏天之中
两只白鹅压着月光
一片翅影
【作者简介】杨道,女,海南东方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天涯》《北京文学》《青年作家》《四川文学》《诗刊》等,著有散文集《终古凝眉》《珠岸碎影》。曾获南海文艺奖文学奖、晓剑青年文学奖,散文作品多次获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奖。
责任编辑 练彩利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