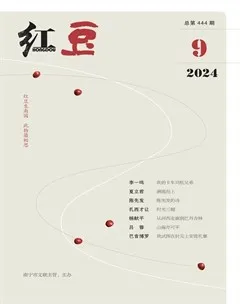老林
2024-10-30杜卫东
1
那天早晨,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十分悲伤地说,她父亲走了。临终,她父亲叮嘱她一定通知到我,希望我能去送他最后一程。
我一怔,一个身影立马在脑海中浮出:身量不高,穿一身深色的中山装,头发浓密且黑,总是梳得一丝不苟,操一口福建味普通话,说话有板有眼。一九七六年,当时我二十二岁,他已年过不惑,是中国青年出版社一编室副主任林君雄,我们称呼他老林。一天午饭后,他把我叫到办公桌前,很认真地问:“你愿意来出版社当编辑吗?”当编辑?这提议来得太突然了,像是幸运之神从天而降,让我有点儿猝不及防。见我一脸愕然,老林猜到我在想什么,笑了笑,用手捋捋整洁的发型,语气中充满鼓励:“你行,只要努力,会成为一名好编辑。”
一九六三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书出版后,作者寄了一套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很是称赞,给了作者极大的鼓舞。为排除各种噪声的干扰,创造更好的写作环境,姚雪垠于一九七五年十月再次写信给伟人,很快得到毛主席亲笔批示,同意作者继续完成《李自成》第二至第五卷的创作。因为要出版《李自成》第二至第五卷,停业十年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全面恢复了业务。一编室人手短缺,便从工厂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抽调了一些文学青年和工农兵学员帮忙。一九七六年初,我退伍回到北京第一机床厂,经厂团委推荐,奉命参与了中国青年出版社两本书的编辑工作,得到老林赏识。不承想,这竟成了改变我的命运。
可是,我调动的过程并不顺利,因为车间主任不放。
同年十月,“四人帮”被粉碎,老林认为事情会有转机,又一次骑着自行车跑到位于东郊的新铸工车间,请求主任高抬贵手,没想到小老头儿仍不为所动。老林向我描述当时的情景:“小杜到出版社工作,也是为‘四化’作贡献嘛!”或许是被找烦了,车间主任眼皮也不抬,一挥手,说:“少来,净想着进高楼、坐办公室,我问你,翻砂的活儿谁干?”
老林儒雅,但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性子。我曾随他到南方某省出差,亲眼见证过他的脾气。中国青年出版社是团中央直属的出版社,到各省搞调研或组稿,对口的接待单位一般是团省委。那天,我和老林下了飞机,辗转找到团省委,办公室的一个女干部看了介绍信,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你们坐在这儿等一下。”转身就出去了。老林开始还耐心等待,过了半个小时仍不见人来,明显焦躁起来。他站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又不时看看手表,嗔怒道:“怎么搞的?”又过了二十来分钟,火山终于突破了喷发的临界点,他从沙发上一把拎起皮包,脸色铁青地招呼我:“小杜,走,我们走!”一拉门,昂着头,甩着胳膊,冲进楼道里,状态很像一头被激怒的公牛。楼道很长,进出办公室的人见到老林怒气冲冲的样子,不明所以,不便问,也不敢拦,还是那个接待我们的女干部从后面跑上来赔礼道:“不好意思,因为一点儿事耽搁啦,对不起。”老林不理她,只顾往前走。女干部紧跑两步,拦住去路。老林停下脚步,愤然道:“五十分钟了,不理不睬,太过分了吧?我们是来谈工作的,不是来受冷落的!”那个女干部自知闯了祸,忙不迭赔着笑脸说:“老师,是我工作失误,我向您赔礼道歉。宣传部部长请您到他的办公室,商量一下工作如何对接。”
和老林共事十年,那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见他发火。
调动未成,厂里把我叫回。本来去之前我在车间搞宣传,小老头儿冲天一怒,我无辜躺枪,被“发配”到班组当了翻砂工。那是我一生中最迷茫的时光,如同一片枯叶,心里落满惆怅。同年进厂的师兄弟早就出徒,一个个手艺杠杠的。我当了好几年兵,技术上完全是一个“小白”,修出的铸件惨不忍睹,必须由师兄弟返工。人们看我的目光,有同情,有理解,也有嘲弄和轻蔑。一道道目光织成一张网,我就是一条被网住的鱼,每天都在痛苦地挣扎。日子像一块沉重的磨盘,在我的精神和肉体上碾过。万幸,老林做事很有韧性,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打来电话,问问我的现状,让我安心工作,说社里从未放弃调我的想法,正努力做通厂里的工作。于是,我内心重新燃起了希望。
2
一九七八年,在老林的努力下,我终于成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最年轻的编辑。
报到时正是人间四月天。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办公地点是一座清朝时的王府,几座四合院相互勾连,布局规整,端方有序,绿树掩映,曲径通幽。院子里鲜花盛开,有樱花、玉兰,印象最深的是一片翠竹,生意盎然。我的心境和美丽的春天一样,所有的惆怅都如云烟一般散去,洒满生命天空的净是美好的光影。我回来了,以前我只是圣殿的一名香客,从今以后,我也是这座院子的主人之一了。命运真是一个魔方,不断变幻,呈现出它的无穷魅力。
我很快进入角色,提出的选题一个个被通过。端详着发稿单上责编一栏“杜卫东”的签名,我觉得,这才是命运该有的样子。生活如同兑了奶的咖啡,芳香四溢。正当我以为整个世界都在为我喝彩时,我突然遭遇一记“迎头棒喝”。一天上班,我走进编辑室,气氛有些诡异,同事们没有像往常一样和我打招呼,而是沉默不语,埋头看稿。我坐下,桌面正中摆着一个文件夹,编辑室用它传阅重要的文件和通知,看后,每个人要在自己的名字上画圈。房间里的气氛暗示我,今天传阅的内容非同一般。是什么?任免名单,处分决定?有同事在偷瞄我,无疑,和我有关。我长嘘一口气,定定神,打开文件夹——是老林的一个批示,并附有我写的一份审读报告,上面用红笔一一标明了好几处错别字和语法错误。他的批示措辞严厉,说:“不论是水平低还是工作疏漏,都不能成为被原谅的理由。编辑是很严肃、很高尚的职业,要对作品进行整理、加工和修改,通过编辑的书籍传承优秀文化。这样的审读报告,何以匹配编辑称号?何以履行编辑职责?”
我蒙了,大脑被按下暂停键,一片空白。前几天,老林已经“修理”过我一次:我担任一本咏物抒情谈哲理的散文集的责编,送审时夹带了一篇私货——我写的《荷花赋》。那时,我在文学的道路上刚刚起步,很想在公开出版的书刊上发表作品,跃跃欲试写了一篇。可是老林招呼也没打就撤掉了。我顿时蔫头耷脑,如同一朵刚被风雨吹打又被阳光暴晒的花儿。
午饭时,老林从抽屉里拿出一只蓝花大瓷碗,起身走到门口书柜的玻璃窗前停下,用手捋捋头发,探头照照,然后招呼我:“小杜,走,喂脑袋去。”我站起身,无精打采地跟在他的身后。一编室主要出版青年修养读物,作者以党政干部、学者和教师居多,我曾建议请作家撰稿,改变一下文章风格。老林一直不置可否。就是在那天的饭桌上,他肯定了我的想法。或许,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陌生的自己。老林的支持一下子点燃了我的热情,我的潜能得到超常发挥。随后,我列出的几十个选题把当时的文坛名家几乎“一网打尽”。苏叔阳住在北京的一个小四合院里,我找到他时,他正悠闲地躺在葡萄架下的躺椅上,摇着扇子,闭目养神。刘心武用一把锁锁门,当时的北京出版社在一座破旧的小楼上,条件很简陋。蒋子龙刚刚出差回来,正清点票据,听我说明来意,他友善地摇摇头,说:“咳!打个电话就行了,这么远,还用跑一趟?”王蒙到社里文学编辑室找王维龄、许岱聊天,见到冒冒失失闯入的我,很爽快地认领了一个题目:《真理是时间的女儿——青年人怎样对待流言蜚语》。冰心坐在洒满阳光的书房里,和蔼的微笑至今仍在我的记忆深处绽放。她站起身走到写字台前,从笔筒里取出一支铅笔递给我,柔声批评我的情景历历在目:“小伙子,当编辑的怎么能不随身带一支笔呢?”在张洁的住所,我见到了她的母亲,那个世界上最疼她的人,善良而慈祥。王安忆、张抗抗也都答应撰稿。最难忘的是王愿坚,约完稿后,他送我走出很远,一路上多有鼓励和叮咛。后来,诗人华静采访王愿坚的夫人翁大姐,老人家居然还记得我——当年那个上门约稿的小编辑。我和秦牧先生从未谋面,可是在广东省作家协会门口,看到一个器宇轩昂的老人,我断定他就是我要找的文学大咖,追上去一问,果然是。他耐心听我说明意图,欣然接受了我的约稿。这之后,我们的合作愉快而持久,印象中他从未拒绝过我,如果稿件迟交几天,还会专门写信说明原委。有同事从广州组稿或开会归来,常常会捎来他的问候。一向对名人大家敬而远之的我,春天时会接到秦牧先生的电话,告诉我他来北京参加全国两会,下榻在某饭店,约我有时间一晤。一次老林听到是秦牧电话,要和我一起前往。他从饭店出来后仍兴奋不已,原来他也是秦牧的铁粉。一九九二年,惊闻秦牧先生辞世,我含泪写了一篇文章《心香一瓣祭秦牧》,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上。
老林对我的工作很满意,不过对我的个人创作却表现冷淡。比如他有时会悄悄走到我身后,窥视我看的书或写的文字,如果发现是在经营“自留地”,他脸一沉,没好气儿地说:“工作时间,不要干与工作无关的事。”只是,我对写作有了浓厚兴趣,尝试着写了两篇思想散文。《我们还年轻》《露珠在阳光下才会闪光》,很快在《中国青年》杂志和《中国青年报》刊出。我大受鼓舞,于是突发奇想,列出了二三十个题目连同几篇样稿,寄给上海人民出版社,咨询能否结集出版。一个月后,办公室的门被敲开了,进来两个操上海口音的中年人,自称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张志国和顾兴业,专程来北京组稿,顺便见一见我。他们表态说,如果我的文章整体水准不低于样稿,可以酌情考虑。我太兴奋了,像是穿越草地的行者,突然见到漫天花雨。我送走客人,兴冲冲找到老林请创作假。老林正在看稿,听我说明了情况,端起茶杯吹吹上面的浮叶,兜头浇过一盆冷水:“签合同了吗?没有。对吧?整体达到样稿水平,怎么把握?怎么衡量?很难有一个恒定的标准嘛!你也是编辑,难道听不出来,这不过是一种客套?书能不能出完全在两可之间。”他放下茶杯,咚的一声,动静有点儿大,看我的目光也如同秋天的风,带着些许寒意,“况且,现在编辑室工作也很忙,你这时候请假去搞个人创作,合适吗?”我无言。我承认,老林说的不无道理。但是,有些机会是单行道上的风景,一旦错过就很难再次相遇。那年月还不兴自费出书,在国家正规出版社出一本书有如攀登蜀道,要经过严格的选题论证和三审,许多喜欢文字的人终其一生也难有一本著作问世。我怎么能轻易放弃这个机会?我不想在生命中留下遗憾,即便没有撞线,也不能放弃奔跑。
不给假就挑灯夜战。那一段时间,我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除了上班就是写作,熬到后来,每天晕晕乎乎的,走起路来就像脚踏五彩祥云。几个月后,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将誊写整齐的一摞书稿寄出。不久,由秦牧先生作序的青年修养散文集《青春的思索与追求》,就摆上了各地新华书店的书架。这件事后,老林看我的目光中有惊诧,也有歉意。
那时,我太年轻了,对图书编辑的慢节奏渐生厌倦,对老林不支持我写作也心存怨怼,动了调动的念头。一九八四年,《中国交通报》创刊,曾是交通部政策研究室笔杆子的柳萌推荐我去。面试我的报社人事处处长王静,是一个很干练的老大姐,她对我的情况很满意,当即让我填写了“干部登记表”,并说:“只要中国青年出版社同意,交通部马上下调令。”新的工作岗位对我很有诱惑力,尤其王静处长的一句话更是令我神思飞扬:“来吧,年轻人,《中国交通报》虽是专业报纸,但它的活动半径广阔,世界上凡有港口的地方,你都有机会去。”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在食堂找到老林,说:“我想和您说点儿事。”
老林很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把没吃完的菜往碗里一扣,起身就走,说:“这几天我很忙,没空。”那时,他已升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分管好几个部门,工作头绪确实很多,但是再忙也不会抽不出几分钟吧?我感觉他是在刻意回避我。
忍了两天,实在起急,一天下班后,我敲响了老林的家门。
老林开门,见是我,神情并不意外。他接过我带去的一袋苹果,随手放在桌上,招呼我坐下,问:“你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我直截了当说了自己的想法。他或许是听到了风声,神色平和,坐在沙发上,右手的食指一下下有节奏地敲击着扶手,问:“他们给了你什么承诺?”我回答:“记者部副主任。”又补充了一句,“没主任。”老林点点头,“噢”了一声,说:“我们对你的安排也正在考虑呀!”我又补充了一句:“还答应给我分一套两居室住房。”
老林又点点头。那时我们一家三口住在不到八平方米的平房里,老林去过,深知它的逼仄。出版社宿舍紧张,他虽是副总编辑,却不分管后勤。这回总没话说了吧?不想,老林依旧不慌不忙地说:“出版社正计划盖职工宿舍。”
想到当初老林调我时的艰难,又看到他诚意满满,我调动的念头开始动摇。但一想到无垠的大海和多彩的世界,我还是想走,就祭出撒手锏:“我不想编书了,想办报或办刊。”
这个要求无解。办报、办刊牵扯的方方面面太多了,非个人能够协调。
没想到,老林似乎已有思想准备,还是点点头,微微一笑,说:“你想办刊,不是不可以考虑呀。你搞一个方案,社里研究一下。”
就是那次谈话之后,一本新刊《追求》横空出世,并风行一时。
一九八七年,因为年少轻狂,在编辑理念上时与老林发生碰撞,又恰逢朋友不断伸来橄榄枝,我还是决定调离。这一次,老林听了我的想法,沉默不语,许久,才说:“你去找老阙吧。”老阙叫阙道隆,年过五旬,不苟言笑,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编辑。他显然和老林有过沟通,言辞恳切地挽留了我一番。他见我去意已决,便抽出一支烟点燃,默默吸了两口,在烟灰缸的边沿轻轻蹭去烟灰,说:“不急,你回去再想想,如果主意不变,三天后找我签字。”
离开中国青年出版社后,我和老林的往来渐渐稀疏。一编室的老人几次聚会,目睹时光如一把刻刀,把他从一个儒雅中年人雕刻成了菊老荷枯的长者。
我也不再年轻。往昔的一切随时光走远,留宿在一个叫“记忆”的客栈。
3
二〇一四年,我的长篇小说《江河水》出版,我意外地接到老林的电话。原来他看到了报纸上刊登的评论,很是高兴,打电话希望我送他一册签名本。耄耋之年,老林还有精力读完一本七十万字的纸质书吗?我很怀疑。没想到,他不但读了,还写来了详细的读稿札记。这是他长年养成的习惯,审稿或看书,每每会记下一些稍纵即逝的感想。老林说:“小说可读性很强,我是一口气读完的,如果改编成电视剧会很好看。”
不能不说,老林具有很高的文学鉴赏能力,他的读稿札记颇有见地,对故事推进和小说的人物命运走向都有独到见解。而且如他所料,小说出版后很快被影视公司买断版权。可惜的是,四十四集电视连续剧《江河水》在江苏卫视播出时,他已作古。
老林不事张扬,行事低调,我曾对他的文字水平有过质疑。一次我去送稿,无意间看到他办公桌上摊开的本子,上面是他随手写下的读稿札记,言简意赅、文辞秀丽,而且字迹工整、娟秀飘逸,令我很是折服。还有一件事也纠正了我的认知。一九八〇年,老林接到一个约稿电话。我清楚地记得,他准备走时已是下午三点,他一边穿风衣一边对我说:“我要赶一篇稿子,先走一会儿。”第二天早上,署名“林君雄”的大块文章《青年与修养》,就赫然在《中国青年报》头版占据了半个版面。出手之快,令人咋舌。
老林很有才情,如果他专注个人写作,也会成为作家或学者。他放弃了,他的志向是风,看上去无形,却能吹动风车欢快地歌唱。他不鼓励我个人写作,希望我也成为一名专心致志的好编辑,并亲自为我打了样儿。印象中,老林用《青年与修养》的稿费买了一大包糖果,与编辑室的同事共享。这样做很重要的原因是,文章的写作占用了工作时间,报社约稿又与他所担任的职务相关。那时候,中国青年出版社风气很正,工作时间在院子里基本见不到人影,每个人都在埋头工作。休息铃声一响,院子里才会热闹起来,打羽毛球的,练太极拳的,三五成群聊天儿的,都有。同事之间从不称呼职务,即便是老社长朱语今,一个一九三六年参加革命的前辈,每天骑一辆半旧的自行车上班,人们见了他,也只是点头一笑,叫声“老朱”。整个出版社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大家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恪尽职守。
严苛是老林的表象,表象后面,其实也飞翔着一个很有趣的灵魂。
比如他不支持我个人写作,却暗中为我送来祝福。《荷花赋》被他毙掉后,我不服,投给了《奔流》。没想到,这篇自由投稿很快被杂志采用了。同事小徐告诉我,老林在资料室看到《奔流》上刊登的《荷花赋》,兴奋地对正在查找资料的他说:“如果我们编辑室未来能出一个作家,就是小杜。”说这话时他两眼放光,好像这篇散文的作者不是我而是他。这个预判太令我震撼了,那是我的梦之乡,能否抵达,心怀忐忑,老林的话无疑点亮了我心中的那一盏灯。严苛的老林有着非常宽厚的一面。一次,他带我出差,晚上,我被他风箱一样的呼噜声吵得无法入睡,翻身、咳嗽,一点儿也降低不了鼾声的分贝,便去前台另开了一间房。老林早晨起床后不见我的人影,急得够呛。后来,终于在服务员的引领下推开我的房门,走到床头,他掀开被子,扒拉扒拉我的脑袋。我睁开眼,见是老林,以为他会生气,不承想,老林的神色竟充满惊喜,像是沙漠中的跋涉者终于看到了一泓清泉。他堆出满脸苦笑,亲切地问:“睡好了吗?现在起来,还赶得上吃早餐。”
有一年夏天,中国青年出版社组织员工到北戴河休养,一编室下榻在一栋临海的别墅里。当天晚上,老林张罗了一次螃蟹宴,在别墅的大露台上,大家一人手捧一只大海蟹,蘸着加了姜末的醋,品蟹赏月。老林还用他那福建口音很浓的普通话朗诵了曹雪芹的《螃蟹咏》:“铁甲长戈死未忘,堆盘色相喜先尝。螯封嫩玉双双满,壳凸红脂块块香。多肉更怜卿八足,助情谁劝我千觞。对兹佳品酬佳节,桂拂清风菊带霜。”
那晚夜色真美。海风轻拂,像绸缎划过面颊。从阳台望过去,无垠的大海就在眼前,夕阳的余晖映照在海面上,波光粼粼,仿佛有万千碎金在海面浮动。偶尔会看到数只海鸥如箭镞一般掠过,几艘帆船像倦鸟一样归巢。
螃蟹宴后回到房间,老林意犹未尽,坐了一会儿,又对我说:“走,读海去。”
读海?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些懵懂。随老林来到海边,我们并肩坐在沙滩上。
这时,晚霞早已退去,月亮缓缓升起,天色逐渐暗下来。夜一抖黑色的大氅,罩住了世间万物。大海如一个饱经沧桑的长者,在浓浓的夜色中沉睡。海浪有节奏地拍打沙滩,发出一阵阵高亢的呼啸,那该是大海发出的鼾声吧。老林一直沉默,许久,才喃喃道:“你不觉得,海浪拍岸的声音正是大海最深情的诗篇吗?它让我们领悟什么叫壮美,什么是永恒。而且海是由无数的江河汇成的,它的包容和坦荡多么令人崇敬。”在月光的映衬下,老林做思考状,面孔呈青铜色,很有一点儿罗丹的雕塑作品的范儿,“你再想,大海的深处有些什么?海沟、沉船、巨兽,或者远古的城池遗址?哪样不和时光相连?时光是历史的载体,没有了时光,一切归零,而我们则是时光的剪裁者。”
或许是因为晚宴喝了点儿白酒,那天晚上,老林妙语连珠,颇有哲思高论。他告诉我,一个人不仅要读书,还要读山、读水,总之,要努力领悟自然,使自己的心智更加健全。
这个场景定格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距今已过了四十余年,仍恍如昨日。
老林是我编辑生涯的第一个老师,他的严苛犹如一座山,看上去巨石突兀,却也有溪水潺潺。这么多年过去,心中的芥蒂早已随风消散,剩下的只有自省与感慨了。无边往事难忘却,心向昨天觅旧篇。蜡烛有心始垂泪,一梦依稀四十年。什么是感恩?真正的感恩不在乎是否有过嫌隙,只要他是一束光,曾经照亮你的人生。牢记逝去的美好,珍惜相伴的日子,一生有一生的缘分,一程有一程的芬芳。
我抑制住内心的悲伤,告诉来电话的老林的女儿小英:“去,我一定去!”在老林的遗像前,我会深深鞠上三个躬,并虔诚地说一句:“敬爱的君雄老师,一路走好!”
——敬爱的君雄老师,您是我生命中的启明星,在那些暗淡的日子里,是您给了我前行的勇气与方向。
【作者简介】杜卫东,曾任《人民文学》副社长、《小说选刊》主编。已发表各种题材文学作品五百余万字。结集出版四十余部,作家出版社出版四卷本《杜卫东自选集》。出版长篇小说《吐火女神》、《山河无恙》、《江河水》(与人合作),散文集《岁月深处》由美国全球按需出版集团译成英文在全球发行。散文《明天不封阳台》被收入苏教版初二语文课本和香港高中语文教材。曾获《人民文学》报告文学奖、《北京文学》散文奖、全国报纸副刊年度金奖等。另有编剧作品《洋行里的中国小姐》《江河水》和《新来的钟点工》。
责任编辑 练彩利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