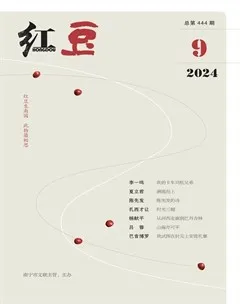混合记忆
2024-10-30徐迅
边陲城市
经仔细了解得知,我到防城港的那几天都会有雨,依次是阵雨转中雨、阵雨转大雨、中雨转大雨、阵雨转多云……看了天气预报,我对防城港的雨有着充分的准备,我不仅带了一把雨伞,还破天荒地带了一双雨鞋。我知道防城港是亚热带季风气候,那雨不仅是边陲城市的雨,还是亚热带的雨、南中国海的雨……因为雨,我还对防城港这座城市有了一种莫名的兴奋的期待。
但二〇二四年六月十四日防城港没有雨。我看到的是阳光,间或阴天,体会到的是亚热带城市的闷热,一种类似蒸桑拿的感觉。防城港没有下雨,我就不用带伞,也不用穿雨鞋,而能轻装上阵地看这座美丽的城市——套用托尔斯泰的话说,幸福的城市是相似的,不幸福的城市各有各的不幸。对于防城港,我感觉它是幸福的。它的幸福是由企沙、渔澫、江山等三个半岛以及东湾、西湾、珍珠湾等三湾组成。有岛有湾就有水,这水,不是简单的水,而是南中国海的水。事实上防城港拥有城市应有的一切: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楼房,街道,各种商店……还有公园。公园里铺着红色的塑胶跑道,我在塑胶跑道上跑,看到水里生长的一大片红树林。我以为红树林是红色的,但看到的却是绿色。我以为这是季节的原因,但显然不是。红树林本来就是绿的,是长在海水里的绿叶植物。看到一簇簇红树林,我就感觉这座城市的个性出现了。
但很快就有人否定了我。他说红树林不只防城港有,甚至不是防城港的市树。防城港的市树是秋枫树,市花是金花茶。秋枫树的树干多笔直,树冠蓬大,防城港的十万大山就有十万株秋枫树。秋枫树是防城港的一种精神象征,有“正气凛然、奋发向上”的美好寓意。而红树林在南方则很普遍,它是由秋茄、刺桐、木榄、对叶榄李等树组成,广西、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都有。这不算是防城港的另类。如果要算另类,就算金花茶。他们尊金花茶为“茶族皇后”。金花茶金灿灿的,黄里有红,红里有黄,娇嫰得让人看上一眼,心里就颤颤的。
我开始喜欢看防城港疯长的一些植物。赤橙黄绿青蓝紫。那些植物,如白兰花、月季、三色堇、紫薇、木槿、紫花地丁、千日红+V65mzDMlL1YBNvBXDGrMNxqeFXwrgGZ58qI3tRlkuk=、荷花、扶桑、蔷薇、玉簪、萱草、天人菊、茉莉、栀子、龙船花……什么颜色的花草都有。有我见过的也有我没有见过的,有我熟悉的也有我不熟悉的。
我在岛上看到一株芭蕉树,芭蕉树朝我不停地做着鬼脸。芭蕉叶像是大地吐着绿色的舌头,显得一脸无辜。但有时它又得意扬扬,双肩垂立,像一个京族少女深情地望着情郎,又像一个绿衣宽袖吟哦的诗人……
说到诗人,有那么一刻,我就感觉找到了防城港的不同。因为在簕山古渔村,我看到了唐代大诗人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正在邀月台上。
据说住在簕山古渔村的都是李氏“陇西堂”的后人,是他们发现了这块风水宝地,命名为簕,在这里定居下来。朝暾中出海打鱼,有月亮的夜晚,对酒当歌。除了邀月台,海边还有揽月阁、观月楼……有李白后人,当然也就有李白的豪情。这豪情便是防城港独有的一种诗情了。我们不仅在这个渔村吃了午饭,还兴致勃勃地看了防城港的其他几个海滩,短短几天时间,我们分别到了金滩、白浪滩和怪石滩。
我是在车上看金滩的,透过玻璃窗,我看金滩上聚集了很多游客。天空乌云滚涌,海浪滔天,不见一艘打鱼船。这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白浪滩。白浪远远推去,吐着白色海沫,一望无际。黑沙一望无际。黑沙白浪。防城港有着多么顽强的黑沙,千年万年的海水也漂洗不白……我心里嘀咕,对着“黑沙白浪”的石刻用手机乱拍,忽然一阵海风吹来,手忙脚乱,手机掉到了地上。我心里一惊,自忖自己的唐突怕是让大海听见了,故意给了我一个小小的惩罚!……这样想着,就到了怪石滩。怪石滩怪石嶙峋,海风起处,“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我赶忙搬上一句古诗,大声地朗诵,像是用一把镇尺镇住海一角。果然波澜不惊。
我这样说着,大家便知道我是在海边。在海边,我们当然要吃海鲜。当地朋友说,这些海鲜刚从海里捞出来。为了证明他说法的准确,他带我去了一个海鲜市场。牡蛎,海参,鱿鱼,白鳝,对虾,大蚝,青蟹,沙虫……这里的海鲜新鲜无比。新鲜的是这次吃了沙虫。沙虫生长在泥沙滩涂,又名沙肠虫。顾名思义,沙肠虫就像一根直筒肠子。
当地人说,沙虫出没的海边没有污染,其是环境标志生物。环境标志生物?我上次听到这个说法是在一座大山。那座大山有很多山蚂蟥。他们说有山蚂蟥,就表明大山的生态环境好。但山蚂蟥不能吃,沙虫却可以吃。沙虫的味道鲜美脆嫩,吃到嘴里沙沙响,有咀嚼感——我这样说,是想表明我吃到了与众不同的食物。但话未出口,来自连云港的陈武和大连的张鲁镭两位作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黄海和渤海的滩涂就有沙虫,他们早就吃过,沙虫也没什么特别。
从资料上看,早在五千年前防城港就有先民在这里渔居,繁衍生息。这有大量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为证。硬是要说不同,是他们不叫居住,而叫作渔居。他们很早就懂得靠海为生。再说不同,就是这里有边境口岸。
有边境口岸就有边防的故事。当地朋友似乎存心让我们寻找防城港的历史,不仅让我们参观了一号界碑,还带我们瞻仰了白龙炮台。一号界碑矗立在防城港北仑河出海处的竹山港,界碑高一点七米,宽零点七米,厚零点四米,上面写有“大清国钦州界”的字样,字是清光绪年间钦州知州李受彤所书。笔力遒劲,铁骨铮铮,一笔一画都呈现了不屈不挠、脊梁挺拔的汉字尊严。而位于江山半岛一个小山包上的白龙炮台,更是防城港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历史铁证。登上炮台,我看炮台尽管有被废弃的落寞,但却仍昂扬着国家和民族精神。
防城港的异样就这样一点儿一点儿浮出海面。我很快走到东兴侨批馆。在侨批馆的门前,侨批研究会林会长给我们讲了个有关侨批的笑话。他说,当年有些人来到侨批馆,原以为这是一个华侨批发市场。林会长说,在边境城市,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侨批”并不是华侨批发市场。“批”是当地的方言,实际是写信的意思。“侨批”又称“番批”“银信”“批信”,是华侨寄回国内的信与汇款合一的家书。一九四一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以及南洋各地相继沦陷,邮路被掐断,华侨家书无法寄送,突如其来的灾难使他们无依无靠、度日如年。但智慧的边陲人民不畏艰难,秘密地在防城港东兴开通了一条交通枢纽,让侨批源源不断,迅速通过四通八达的东兴镇,使处于断炊断粮、缺衣少食的侨眷们绝处逢生,渡过难关。“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侨眷们热血沸腾,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侨批之路成了革命与生命并行的一条道路……
我也是第一次认识侨批。但我知道,大海在让一切事物浮出海面。随着行走的深入,浮出海面的故事越来越多。典型的例子就是海岛女民兵。这是我童年时代的红色记忆。接下来,我就听到她们戍边卫国的动人故事了……在南疆第一哨,我们有幸见到了海岛女民兵杨富丽和她的丈夫刘华强——报纸上说,他们是北仑河口的守望者。这对夫妇除了他们自己,还有三个儿女也在守边或从军,都挑起了保家卫国的重担……不知道边疆有多少这样的英雄儿女,但我知道有一句俗话:“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在这里,戍边竟然就是一种真情的工作。这种工作,便是边陲人民的不同吧?
告别哨所,我们就要结束在防城港的行程了。有趣的是,我们最后一站参观的是京族博物馆,这又让我们感受到了与其他少数民族不一样的京族文化。
就在京族博物馆,天气预报上说的那一场大雨终于如期而至。瓢泼的大雨倾盆而下,哗哗地在博物馆的屋顶上狂奔着,雨一下子就布满了我的眼帘——其时,我突然发觉,这场大雨与我在防城港所感受到的种种不同或者相同,已经共同构成了我对防城港的全部记忆,一个阳光和雨雾混合的边陲城市的记忆。我发觉从一开始,我似乎就怀念这座城市。
左岸
左岸,是一个名词,又不是名词。说不是名词它又是地理概念,说是名词它已然成了一种文化。
较为著名的左岸当是巴黎的塞纳河左岸。那里催生了圣日耳曼大街、蒙巴纳斯大街和圣米歇尔大街,催生了出版社、画廊、大小书店、小剧场、美术馆和博物馆等。又因文化的附着,衍生出咖啡馆、酒吧和啤酒馆……吸引着像海明威、萨特、毕加索、魏尔伦这样的文艺人在此喝咖啡、酗酒、写作、休息或者寻找创作灵感……
在中国,也有一个著名的左岸,就是赤水河左岸。
说起赤水河的著名,首先,是因为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的故事吧?宏大的革命叙事家喻户晓。其次,就是上天赋予这里独特的气候和地理环境。这也是一条流向长江的河。这条河自西向东,经过云南、贵州、四川,便一下子宛若天赐,得天独厚,滋养了高粱、小麦等酿酒的原料,成就了优质酱香型白酒的生产地……一河两岸,酒香醇厚,经年弥漫。缘此,这条河也就有了“美酒河”的美誉。
生产在河边的酒总是美的。想说的还是法国,法国波尔多葡萄酒的产区也在河边。那里有加龙河、吉隆特河和多尔多涅河,河畔丛生的是一片片葡萄种植园。有河自然也就有左右两岸之分,河的左岸生产着梅多克和上梅多克,河的右岸便酝酿出了波美侯、圣埃米里翁等众多的葡萄酒,是葡萄酒的子产区。“左右岸”共同成就了红酒的故乡,成就了波尔多的国际品牌。
与波尔多葡萄酒产区相似,我们脚下这条被誉为“美酒河”的赤水河,一河两岸,也有众多的酒诞生与生长。如右岸的茅台、习酒,左岸的泸州老窖、郎酒……不过与波尔多不同的是,这里生长的都是白酒,酱香型白酒。浓香、陈香、兼香大概是后来的事。郎酒庄园就坐落在美丽的赤水河左岸。
左岸有山。有山峰环绕,壁立千仞。山上有树、有草、有花,丰丰盈盈,蓊蓊郁郁。有了一山的绿,就有一山的花枝招展。花是油麻藤,油麻藤下是郎酒的坛。密密麻麻,郎酒坛摆在那里,就像油麻藤孵化的一堆堆蛋。紫色的油麻藤花掩映着,酒坛一只只、一窝窝,让人弄不清楚是 树多草多花多,还是酒坛多。酒坛敲起来,声音嗡嗡的、闷闷的。明白的知道装的是酒,不明白的还以为一庄园的酒坛都跑到这里,散步或抱团取暖呢!
左岸有洞,洞曰天宝、地宝、仁和。洞似乎是专门为藏郎酒而生。天然喀斯特溶洞,天然的大酒窖。郎酒当然也不客气,成千上万,偌大的酒缸一坛坛、一排排,规则或不规则的,一股脑儿就聚集到这里。它们像秦始皇的兵马俑,但与之不同的是又有着生命的萌动。那些生命,在酒缸里生活、孕育着,又似是闭关静修的老道。看不见生命,能看到的是酒缸上的白。白色绒毛,星星点点。行家说,那是酒苔。酒苔上聚集着几百种微生物,它们是酒的性命,是酒的精灵……这些精灵从酒缸里飞出来,就粘贴在洞的崖壁。可见生命是封不住的,一些生命总要自由地跳跃、奔跑和舞蹈……
左岸有米。这米叫作米红粱,又称糯高粱。大片大片的米红粱,漫山遍野,沿赤水河左右生长。说是每年到重阳节前后,万山红黄,层林尽染。红的是米,黄的是缨,黄红之间,色泽红润的米红粱,就像赤红的沙子,与赤水河相互辉映……都说米红粱皮厚粒小,但谁也不会想到,正是这一粒粒新鲜饱满的米红粱,与搅拌的大曲,通过发酵、蒸馏等工序,就化作了清爽、甘美、醇厚、柔滑的液体,化作了香喷喷的琼浆……
左岸有传奇。不想说二郎神如何像夸父逐日,下海擒龙;也不说二郎神神游至此,见此地山高水急,人民生活不便,便搬石架桥,造福一方,百姓感其德,取滩名为二郎滩,镇名为二郎镇。单说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在这里就有过二渡与四渡,为中国革命荡了个“神来之笔”。开仓放盐,扶困济贫;饥饮郎酒,解乏纾困,清洗伤口……“赤水河呀长又长,手捧郎酒香又香。红军哥哥为穷人,献给红军尝一尝……”这歌声,既是郎酒对自己的信任,更是对中国革命的尊敬。
左岸有庄园。庄园里不仅有酒店,还有品酒、调酒、藏酒的一切设备,且都起了好听的名字。比如,酒仙别院、地之阁、青云阁、敬天台、红运阁等。客人来了,可在敬天台品着郎酒,凝望赤水河,也可在金樽堡调一杯酱香浓香兼香的酒……一园鸟语花香,奇怪的是花香,冷不丁就变成了酒香……比如清早起床,我原想呼吸草木气,充斥鼻间的却是酒的醇香,就让我疑心眼皮底下的草木,是否昨晚也喝了酒,也想“与尔同销万古愁”。
在左岸,喝的当然是左岸的酒。酒曰红花郎、青花郎……喝了左岸的酒,一觉醒来,却感觉酒气早已四散,有一种陈瘀尽除的神清气爽。想起“原汤化原食”“以酒醒酒”的说法,猜想都是庄园里酒香作祟,哑然失笑……突然想起,在我家乡一带,红花郎、青花郎都另有所指。比如说黄花闺女、青花郎,里面就有些处子的青涩的意味。只有新郎官才会被人称为红花郎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说一个青花郎,戴着一朵大红花,迎娶了新娘子,也就成了红花郎……这是多么喜庆与浪漫。
左岸总是容易浪漫的。法国人说,左岸是巴黎作家的天堂,是左岸创造的文化孕育了巴黎。但左岸却从未放过自己品质和思想的培养。如随着巴黎商业经济兴盛,巴黎左岸有意无意就设立了巴黎大学文学院(原名索邦大学)、法兰西大学(原名三语大学)、法兰西学院(原名四国学院)等三所大学,让左岸有了学生、有了老师、有了大批知识分子的麇集。赤水河左岸的郎酒,“生在赤水河、长在天宝峰、养在陶坛库、藏在天宝洞”,他们为此而设立郎酒品质研究院、中国郎·山谷光影秀、金樽堡、酒歌广场……是否也是受此启发的呢?
不知不觉,算来巴黎左岸的历史已有三百多年了。听哲学家们说,三百多年来,人们在巴黎左岸的咖啡里,不但加了糖、加了奶,还加了文学,加了艺术以及种种哲学精神。如此使左岸由名词变成了一个时髦的形容词,变成全世界都知道的一个文化符号、一种象征、一笔璀璨的文化遗产。
那年,游览巴黎的塞纳河,我就写过这样的文字:
塞纳河上,各种肤色的人相聚在一起。夜晚降临,凉风习习。灯火在树林中闪现,两岸辉煌,埃菲尔铁塔直插云霄,巴黎圣母院发出圣洁的光辉……穿过一座座铁桥,桥在灯光的映照下通体透明。水声很大,大家都细心地看着两岸,两岸都是白色的建筑物,粗大的柱石、平面的街道……巴黎的夜晚是迷人的,梦幻而浪漫。无论怎么形容它的美丽都不过分。因为,所有的形容词在这里都在剥落,仿佛让塞纳河的水洗涤一尽。
站在船上,河水哗哗响,建筑物在我面前就像一柄缓缓张开的扇面,一步一景,移动着法兰西的历史……水里的城市,水里的历史。我在心里说。
一晃,这也是多年前的事了。现在,我来到赤水河畔的左岸。想起巴黎的塞纳河,我就想,赤水河的左岸是不是也会像当年巴黎的左岸,正在向中国酒里加注一些诗意,加注一些诸如乡野、哲学、艺术……或鲜艳、激情或寡淡的时髦形容词,加注那独一无二的中国文化的温暖关怀呢?如此这般,我想多年以后,只要人们一提到赤水河,肯定也会沉浸到一种独特的气氛与背景里,自豪地叨念起赤水河左岸的白酒庄园,念叨起永恒的郎酒,或永恒的郎酒文化……
戏乡记
车在山道上穿行,忽高忽低,曲折蜿蜒。窗外,一座座翠绿的山,一丛丛葱茏的树,一条条清亮的山溪,一幢幢崭新的楼房,在眼前一闪而过……时有幽兰或茶叶的香气,沁人心脾。但看不清它们的模样,看到的是开得火红的映山红。远处有一两只鹧鸪在使劲地啼叫,声音此起彼伏。啼声在深山里反复回荡。空灵而高远,让我的心像水洗的一般,显得异常澄澈与明净。
“潜山有座山,山里有个许家班……”有人忍不住,在手机里鼓捣出一首歌。歌唱的是许家班,词也是专门为许家班而写。许家班正是这次要去看的戏剧班社——皖西南潜山五庙许家畈弹腔班。潜山有戏,是戏曲之乡。清代出过名叫程长庚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唱戏,唱成了“京剧鼻祖”和梨园一代剧神,被文宗咸丰皇帝封了个“五品顶戴”,还赐他任京都梨园会令、精忠庙会首长达三十余年。可鲜为人知的是,京剧的母体艺术,京剧的灵魂就是潜山弹腔……高亢、缠绵、激越、苍凉的潜山弹腔,正是在这里翻山越岭,直上云巅,成就了程长庚,也成就了中国的京剧艺术。只是京剧成为国粹,弹腔却成了深山里一曲艺术遗响。藏在深山无人识。人们把它称作戏曲活化石,像挂在崖壁上的一把把风化的老戏骨。
到达目的地,没听到弹腔,先看到的是银杏树。银杏树漫山漫谷,鱼鳞般的树叶,花枝招展,在阳光下一片橙黄,让峡谷变得通彻而明亮。据说,在北京只有两条街道有银杏树,我就生活在其中之一。换句话说,我一直工作在有银杏树的街道。因此对于银杏树,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其喜欢自不待言。记得有一年在皖东,听说有一棵千年银杏树,我还趁着夜色去瞻拜。朋友说,通往许家畈路上,就有一棵银杏树。树寿不上千年,也有八九百年。说话间,我们就到了银杏树下。面前果然有一棵银杏树,枝叶婆娑,状若虬龙,粗壮的树身估计六七个成年人才能合抱,似披一身的铠甲,直插云霄。围着银杏树,我转着圈,诧异的是它在一丈多高时,突然分成两棵,像是孪生兄弟,在山梁上并肩耸立,伫望着山中岁月。
看过了银杏树,到达许家畈已近中午。许家畈,顾名思义就是许姓居住的山村大畈。那里青山如黛,白墙黑瓦,犬吠鸡鸣,炊烟袅袅。只是我们到时,既没有二胡的悠扬婉转,也没有锣鼓的锵咚锵,更无表演者头戴凤冠、水袖云手在戏台上咿咿呀呀——眼前,一处显然是戏台的礼堂,人去楼空,满目苍凉——我心里一咯噔,脸上生出了失望之色。陪同的朋友似乎心里也没有底气,说弹腔班社的班主许开学,因十多年前突然中风,身子偏瘫,腿脚不便,怕是来不了。但话音未落,却有一个清瘦的老人一瘸一拐走来,一同走来的还有一个妇人。朋友低声说:“这是许开学和他的老婆。”我立即喜上眉梢地迎上去。许开学说声“稀客”,那妇人就热情地递上一碟生姜。戏乡人好客,这种待客之道,让我想到,这里不仅生长着弹腔艺术,还生长了茶叶和生姜……也就是说,这里既有优美的艺术遗响,也有丰饶的物质宝藏。
一阵寒暄后,我们边吃生姜边听许开学讲述潜山弹腔。他说弹腔和其他戏曲一样,讲究的也是言传身教、口传心授。从小跟随上辈,他曾演过三十多本弹腔戏,可惜现在记不完全了。弹腔戏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年上级文化部门派人来帮助,已整理出《二进宫》《四郎探母》《郭子仪上寿》《徐庶荐诸葛》《渭水河》等九个剧本,让弹腔艺术重见天日。谈起弹腔艺术传承,他略有些激动,说现在许家班虽然还在,但也只是节日表演而已,仍面临着凋零的危机。另外,唱腔的传承也处于青黄不接之际,比如弹腔的“仄调”唱法,现在的年轻人就唱不出来。他很着急,也很担心,害怕弹腔艺术在他手上失传。
说到“仄调”,我不知所云。他就比画着,一遍遍给我讲解,举着例子唱。很快,我知道这是一种特殊的发音方法。意思是,不打开全部声带,而是尖着嗓子唱。人们说程长庚的嗓音叫“膛音”,即鼻腔共鸣,声音由丹田而出,称为“脑后音”,开口气冲霄汉,穿透力极强……我觉得他说的是这个,但没有向他求证。
“有徐庶在玉堂思前想后,思想起老母亲好不惨伤,自幼儿在家中将人伤坏,黑夜里别老母往外奔走。多蒙得刘皇叔情高义好,收留我在帐下辅助汉邦。今日里思老母珠泪双淌,但不知老母亲身可安康?……”或许因我,他给我唱了《徐庶荐诸葛》里的一段弹腔。
老腔老调,古韵古风,虽然没有乐器伴奏,但他一张口,却让我心里一颤,感觉一阵山风在眼前掠过,似有风吹拂银杏叶,树叶翻卷,发出飒飒之声。风停浪息,转而又有一片阳光,明媚地划过沟壑,风起处,攒动一山深色的绿……声腔哀怨凄迷,舒缓激昂,其中蕴含的知音之感、思念之情、孝心与母爱,让人顿生天荒地老般的一种惆怅。
望着他陶醉的样子,我想起这里的另一个艺人,人称“四和老”的左四和。他的祖父左凤昌是晚清的监生,擅长高腔、弹腔。他的父亲左与贵也是高腔、弹腔和黄梅戏的艺术传人。从小耳濡目染,左四和爱戏成瘾。一家三代从艺,算是一个地道的戏剧世家。特别是左四和,他打通高腔、弹腔、黄梅腔等三个剧种的唱腔艺术,将高腔、弹腔的传统剧目移植成黄梅戏。尤其他将口述弹腔《双救举》,经黄梅戏剧作家王兆乾改编成黄梅戏《女驸马》,由严凤英和王少舫演唱,唱成了名传天下的黄梅戏经典。
“皖水上游,山川蕴蓄融浑,民多俊秀,音中宫声,即农人亦多能高歌者……”这是教育家、考古学家程演生在《皖优谱》里说的。这不是一种夸张。这里人痴迷戏曲的程度任人无法想象。这个人称“四和老”的老头儿,戏在他心里,也在他眼里。无须戏台,他张口能唱;竹筷、脸盆、葫芦瓢、竹筒……他伸手就当乐器。在那个物资匮乏和八大样板戏流行的年代,在山村夜晚,他常常独自有节奏地敲着竹筷,有板有眼地唱黄梅折子戏,唱《小辞店》《山伯访友》,甚至《告曹》这样整本的黄梅大戏也唱。戏一开场,便引来远远近近的乡亲,乡亲们或是端坐,或踮着脚,围得水泄不通。唱到熟悉处,大家此呼彼应,如泣如诉、如梦如幻的旋律在山里彻夜不散。
有风吹来,一阵清凉。
畈里人家,先是一缕炊烟在屋顶缭绕,不知不觉就炊烟一片了。看看天色,我们与许家畈做了告别。
很快,车子又走到了古老的银杏树下,枝叶间忽然传来几声鸟鸣声。仿佛是一种提示。抬头望望银杏树,我突然想起另一个剧种——越剧。
提到越剧,就想到越剧的故乡,浙江嵊州的东王村,也有一棵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大树——香樟树。只是不同的是,那香樟树一直是越剧艺人们心中的图腾。他们只要外出演戏,都要虔诚地到树下给香樟树上香,磕头跪拜。高兴时,有人还要编一段唱词。戏曲的土地,难道都生长着神奇的大树?我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有什么内在的关联。但我相信,在民间戏曲生长的山乡,大树一定是戏曲最热情、最忠实的倾听者与观众。就像这一棵银杏树,千百年来,在深山大坳,看惯了日出日落、云卷云舒,听熟了一字字一句句的戏曲唱词。因为痴迷,或者本就是天地的造化,就将这棵枝繁叶茂的银杏树一分为二,托入云霄,从而告诉我们,这里不仅有咿咿呀呀的弹腔,还有那咿咿呀呀的黄梅腔。
深山戏乡,一棵硕大无朋的银杏树未尝不是充满灵性的生命。
【作者简介】徐迅,安徽潜山人。著有小说集《某月某日寻访不遇》,散文集《徐迅散文年编》(《雪原无边》《皖河散记》《鲜亮的雨》《秋山响水》四卷)、《半堵墙》、《响水在溪——名家散文自选集》等二十部。系中国作家协会第九、第十届全委会委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煤矿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责任编辑 练彩利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