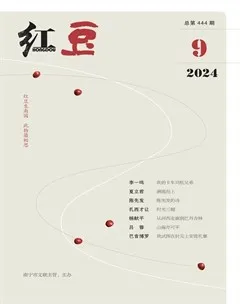从河西走廊到巴丹吉林
2024-10-30杨献平
每一个人的河西走廊
公元七十五年三月,一支三百人的军队出汉代西域都护府治所所在地吉木萨尔不远,即遭到了北匈奴军队三千多人的截击。这是一场兵力悬殊的战斗,也是一场必然失败的还击。仅仅几个时辰,这支三百人的东汉军队就被北匈奴所属军队消灭了。像狼一样善于长途奔袭、大规模野战的北匈奴军队,已经在这一带乃至中亚地区成为一支绝无仅有的战神般的存在。
时隔不久,北匈奴郅支单于又派出军队围攻吉木萨尔附近的金蒲城。这还是一场敌我兵力不均衡的战斗。东汉军队的领军主将,是时为戊己校尉的耿恭。他是陕西扶风人,少小即为孤儿,史书说他慷慨多大略,有将帅才。面对犹如蝗虫一般席卷而来的北匈奴军队,耿恭知道,即便号令全军与之殊死作战也未必能够获胜。思虑之下,他令人在箭头上涂上毒药。这种毒药的名称,没有明确记载。但古人很早就用夹竹桃、箭毒木、朱砂、红信石等植物和矿物质提炼或者直接作为毒药,涂在武器或者投入水中,使敌人中毒死亡。敌人一旦中箭,伤口鲜血喷涌,其状骇人。
北匈奴士兵见汉军武器如此神奇,闻所未闻,个个惊骇。正在此时,乌云奔袭,瞬间遮蔽天空,大雨顷刻而至,匈奴更加恐惧。西北地区干旱,常年少雨。三月,春风不起,草木尚在深蛰之中,天居然下起了暴雨,简直不可思议。匈奴本就是一个以古老的萨满教为主要信仰的大部落联盟,看到这样的情0a2af865be142c2ef4405ef4f796cd5d0ce37d8305606485c2c359a3e8ead80e况,自然心中疑惧大增,随后远遁。耿恭这个人对西北地区的戍守之功是巨大的,他也是以寡敌众,且屡屡取胜,最终使得当时的西域诸国和部落臣服东汉朝廷。
数千年之后,当我以一名军人的身份,到现在已经是一个颇为繁华的丝路旅游点的交河故城,看到耿恭雕像的时候,敬仰之情油然而生。这个少小从军西行,以军功获得升迁的将军,他当年在西北军营建立的功业,是可以灿烂整个东汉时空的。当然,享有无上威名与盛誉的,还有同为陕西人的班超、班固等。站在荒芜的戈壁古迹之上,烈日当头,光芒如剥。遥想耿恭当年修筑城池,被北匈奴围困,旋即又被切断了水道。东汉士兵掘地二十尺之深,仍旧粗砂堆满,不见一丝水汽。正当全军和百姓开始有人渴死的时候,耿恭身先士卒,再度深入枯井,又挖掘三尺之深,清水旋即冒出。将士和百姓痛饮之后,耿恭又命人用桶打水,在城墙上泼扬。北匈奴军队看到,以为天神在助佑汉军,再一次扭头远去。
耿恭和班超等人在西北地区的胜利,其实也是建立在张骞等人的基础上的。从秦到两汉,是世界范围内民族融合的时期。张骞对于西北乃至中亚的探索,军事上的作用只是其中的一个附加成分,真正的影响是使得中原农耕帝国第一次睁开了远眺世界的眼睛。由此开始,从长安向西,经由秦岭、陇右、黄河以西和罗布泊沙漠,翻越葱岭、帕米尔高原的世界之路第一次明朗化。
2608138f435053f526308172aa8f0dd558a52c159d568bdbae24e5bf7db5ecc1差不多三十年前,我第一次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从华北辗转到河西走廊的时候,沿途不由得想起张骞、苏武、李陵、班超、耿恭、李暠、金日磾、沮渠蒙逊、沮渠男成、王忠嗣、哥舒翰、张孝嵩、高仙芝、李白、封常清、岑参、高适、王维、玄奘、鸠摩罗什、达摩、杜环、林则徐、左宗棠等一系列先贤与英雄的名字和事迹。世人所向往的不朽的诗歌、当世卓越之功、青史留名、“死而不亡者寿”,这些人都做到了,而且做得堪与日月争辉。
终其一生,立德、立言、立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古来中国文人的热望与理想;马上天下,“粪土当年万户侯”,“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正壮士、悲歌未彻”。以我一身武功韬略使得寰宇清宁,这是历代志士一生的终极奢望。张骞、李广、耿恭、班超、王忠嗣、郭子仪、岳飞、左宗棠等人无不如此。
其中左宗棠,在收复新疆的时候,曾在现在的酒泉设立行营。我人生的第一次远行的具体落脚点,就在酒泉。尽管我们真正的驻地在金塔县鼎新镇与内蒙古额济纳旗之间的巴丹吉林沙漠西部边缘,但几乎所有的物资和公私事,与之发生联系最多的就是酒泉市。在紧张而又精彩的军旅生活之余,我对河西走廊进行了不规则的探索与漫游。我说的这种“不规则”,即每一次出行都不是正式的,不预先设定目标。凡是预先做好的安排,都是一种设想好了的旅程。真正的旅程,应当是无意中出发的,是对某个区域和秘境的突然闯入,是身心的一次惊奇甚至历险,更是一次大地上的肉身检阅与灵魂修炼。
河西走廊以其地形而得名,祁连雪山衔接和盘踞的,不仅仅是一种地理形态,更是一种文化上的贯通。沿着这条山脉,多少民族,多少热血,多少神秘而蜿蜒的历史往事,都在它周边甚至内部发生。我曾经固执地以为,在祁连山与敦煌莫高窟之间,一定有着一条秘密通道。祁连山以其大幽秘、大寂静和大境界,塑造了人和神的交会点与落足地;敦煌则接纳了诸多缥缈的神灵在人间现身之后的世俗形象。
二〇〇三年夏天,我第一次去张掖城西的黑水国遗址。在那里听到了一个非常离奇且充满想象力的故事。从前,一个牧羊人无意中闯入了一眼黄土的洞窟,看到其中端坐着一个栩栩如生的男人,那男人一手握着一把刀,一手放在胸前。牧羊人吓了一跳,仓皇逃出洞窟。伙同其他人再来看,却发现,那人已不见了,原先的地面上,凭空多了一堆细腻黏手的黄土。这可能是一个虚构的故事。黑水国遗址的最初,可能是乌孙的王汗庭帐,再后来是大月氏和匈奴等。汉武帝的将军们奋力出击,人人争先,与匈奴进行了五十多年的战争,终于迫使这一支骄傲的苍狼军团,以自身分裂的形式结束了对汉帝国的威胁。
这是一条铁血之路,当然也是神话、商业和文化之路,更是一条震古烁今、贯通世界的文明之径。尤其在隋唐时期,诗人、政治家和军事家、探险家、商贾、使者、旅行者的纷纭往来,构成了七到九世纪一道灿烂的人类文明景观。河西走廊的每一座城市和乡镇,都留下了不同先行者的足迹。他们携带了各自的文化、习俗和信仰,在这条走廊上不断往来迁徙、定居、从军、经商和皈依等,其中的杰出者登上了文化艺术的巅峰,军事家则在家与国的大背景下,进行着冷兵器和谋略的对垒与较量。
在武威市及其附近的民勤县、古浪县,附近的金昌市、永昌县、焉支山和山丹县等地,无论是向南还是向北,都是“物极必反”之道家哲学的天然体现,如祁连雪山的高寒、崎岖,蜿蜒与幽秘,巴丹吉林沙漠和阿拉善台地的空旷无际与一马平川,还有丘陵、盐碱地和海子等。多年之后,我逐渐地与当地人在风俗习惯、饮食上发生了根本的趋同,也在相貌上不断接近。气候和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河西走廊的风沙与烈日,巍峨雪山与瀚海大漠,河流湖泊和盐碱的草滩,高悬的明月与恢宏的落日场面,都是一个浑然的整体。
日日沉浸,年复一年,逐渐地,整个西北,尤其是河西走廊,已经成为我生活、内心和精神的一部分。离开河西走廊多年后的某一个夜间,忽然看到军旅作家刘立波老师一组关于他当年从戎西北的影像,那黄色的废墟、铁青色的戈壁、流沙披覆的沙海、积雪中头角峥嵘的岩石、天空中如闪电的大鹰、镜面一般的湖泊、草原上的蝴蝶等自然景观,以及人在其中的点缀和映照,令我意识到,西北地区是刚烈与铁血的,也是广大、辽远的,是一种精神和内心质地的象征。无论是谁,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内心和灵魂当中,既要有风吹露珠、月下花畔、芳草绿树的细腻与优雅,更要有金戈铁马、落日恢宏、大漠孤烟的大气和庄重。
每一个人的生命和灵魂当中,都应当有一个“西部”,也要有一条河西走廊。它是绵长的也是铁血的,是真诚的也是光芒四射的,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于我而言,因为多年在巴丹吉林沙漠从军,河西走廊更清晰得如同手掌的纹路,身体内的某根血管。正如某本书中所呈现的那些奇遇、故事、废墟、地貌、传奇与众多的人生现场,既是早已存在且至今延绵跌宕的河西走廊在今天的一种情境映现,又是我一个人在古老的大地上漫游与探寻时候的偶遇与觉悟。因为在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可以从他物和他人身上,洞察到连事物和他者本身都不明了的秘密和真相。
从酒泉到巴丹吉林
窗户上全是白冰,厚厚一层,其中一些还是菱形的,一朵一朵,高强度黏结。尽管看不到外面,依稀有月亮,硕大、孤独,充满宽广的、旷古的幽怜。它的下面,好像是传说中的祁连雪山以及窄如盲肠的河西走廊,当然还有整个西北乃至中国和世界。大地的一切,都在日月的笼罩与庇护之下,它们是光亮之源,万物的根系与血亲。我想起那首《匈奴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这首歌悲怆欲绝,其中有血,还有着折断的骨头茬子的锋利。祁连山好像是匈奴人命名的,意思是“天”。在古老的史前和游牧时代,人对万物的崇拜出自内心的敬畏与依赖。
而在右侧,不断有零星的灯光涌来,又像散落的火星子一般,被偌大的黑夜和荒漠吞噬了。那是武威市、金昌市、山丹县、张掖市、高台县,这些古老的地方和城镇,曾经作为丝绸之路上最繁华的存在,衔接着辽阔的中亚,一直绵延到欧洲。可现在内陆发展的迟缓使得它们曾经的繁华与重要都变得无足轻重,甚至有些偏僻和落后的意味。好在我是一个热爱大地的人,特别是空旷无垠之处,那种天高地阔与举目千里,那种置身于瀚海泽卤的孤独与坚韧趣味,是其他地域和自然环境不能相比的。
但我没想到,到酒泉下车,迎着零星的白雪出站,我背着崭新的军被,回身看了看根部黝黑、头部积雪的苍茫祁连山,跟着诸多战友,分别爬上了几台大轿车。寒风呜呜作响,车子好像在波涛中摇晃,忽然加大频率的白雪钢针一样持续敲打着车窗。带兵的干部说:“这里是酒泉!”听了他的话,我猛然一惊,迅速想起李白和杜甫。前者诗曰“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后者诗云“恨不移封向酒泉”。还有从军轮台的岑参,他的《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一诗中写道:“酒泉太守能剑舞,高堂置酒夜击鼓。”如此的地方,我想该会停留一会儿,哪怕让我下车,在雪中站立一会儿,我也似乎能够感觉到一种莽苍而又刚烈的古典的边塞气息。
可车子不停,穿过当时还相当落后的市区,从鼓楼一侧绕过,不一会儿就出城了。路过鼓楼的时候,我颇感惊奇。在内地的许多地方,类似鼓楼这类的古建筑,似乎是罕见的,当代人也不怎么愿意保存这样的东西。那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人们想的都是高楼大厦、窗明几净的现代化建筑,对于古人的遗存,多是不在意的。而酒泉能够保留这些,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看到鼓楼四面分别写着“东迎华岳”“西达伊吾”“南望祁连”“北通沙漠”的匾额。我知道,伊吾就是今天的哈密,祁连当然是祁连山,华岳则有种心向中原及王朝核心的忠贞意味在内,而“北通沙漠”是哪里,我一时想不起来。
我抠掉玻璃窗上的白冰,从一条缝里看外面。大地好像很平坦,有一些光着枝丫的大小白杨树,在旷野之间挺立。一色黄土的田地完全是荒芜的,枯燥得令人心生愤懑,一点儿绿色都没有。田地远处,有几座低矮的村庄,若不是涂着白色墙皮,人居之处和漠野便没什么区别。西北之地,居然如此苍凉与贫瘠,这和我想象中的大地迥然不同。而大地总是以其多变的形貌,承载着诸多的事物。然而连这样的情境也稍纵即逝,迎面而来的是起伏的沙丘、平阔的戈壁。雪花在其上敷了一层白,那种名叫骆驼刺的植物一根根地支棱着身子,身上也挂着零星的雪花。一地的缟素,似乎是一种集体的祭奠。
平沙漠漠,寂寥得令人心里发慌。带兵的干部说:“这就是沙漠戈壁。那边是著名的合黎山,当年大禹在这里治过水,漠北的匈奴也曾由此进出,李陵也从这里沿着弱水河出塞,到阿尔泰山下寻击匈奴单于的主力部队。《尚书·禹贡本纪》中说‘(大禹导)弱水至于合黎’便是此地。再向前,便是金塔盆地,现在是酒泉下面的一个县。”听了这番话,我倒是觉得,这无边的戈壁,要是水泽漫漶该有多好,大禹当年为什么要治水呢?唯一的解释只能是那时候的戈壁大漠之间,尚有无可辖制的大水,在其中冲撞、深潜,危害到人和牲畜的安全,方才需要治理。可令人心情复杂的是,数千年之后,西北地区,居然成了缺水与干旱的代名词,甚至是寸草不生、荒芜万里的一种自然存在。
金塔之名,大抵由其中有建于元代的筋塔而得。这是一片难得的绿洲和盆地,人烟虽然也很稀疏,但它是衔接沙漠的最后一站。据说金塔人在酒泉当地有小犹太人之称,其中的意思,是聪慧和狡黠,既会做生意,也巧言令色,极会迷惑人。
在金塔饭店吃了一顿饭,而后又上车。雪花继续,风如兽吼,大致一个小时,车子就又一头扎进了茫茫戈壁。斯时雪花仍在飞舞,天空灰暗,巨大的戈壁上,有些地方白雪刚刚覆住表层,有些地方则仍旧一色铁青。带兵的干部说:“这一带曾经是西汉与匈奴作战的前线,这弱水河边还有很多的烽火台遗址。以后有时间,你们可以到那里去看看。骑辆自行车就可以到了。”他的这番话,令我遐想不已。这漠野黄沙之中,居然有这么多的历史传奇和人文遗迹,简直不可思议。我趴在车窗上,忽然发现,这戈壁滩大得没有边际,看起来特别像水走石出的水底。无数的粗沙和卵石堆在一起,有些平整,有些凸起,看起来就非常坚硬硌人。我还想到,从前村里老人说有过洪水灭世的灾难,也有过剧烈而伟大的地壳运动。这戈壁大漠,在亿万年前,或许是一片汪洋大海,造山运动之后,陆地抬升,海水退却,余下的就成了这苍莽与荒凉的高地。
地球可能真的是不安分的,稳定只是相对的。许多年之后,它还会改换模样。这种运动似乎没有休止,人类和万物大抵是地球运动间隙的产物,包括我们所谓的文化和文明。想到这里,我觉得幸运,又觉得绝望。再次眺望飞雪之中的戈壁的时候,内心充满了悲怆。那些骆驼草真是坚韧,它们在贫瘠之中的生存,显然是一种宿命。还有那些芦苇和芨芨草,在偶尔出现的小水洼旁边,那么惬意而又不知忧惧地活着。尽管这时候,它们的身子都已经成为枯黄的秸秆,但这种的生存,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好像过了很久,我们还在戈壁大漠上,像一叶扁舟于汪洋之中奋力划动,好像永无尽头。我忍不住问带兵的干部啥时候能到。带兵的干部说:“快了,过了这十八盘,再有一个小时。”我再次把脸转向窗外,雪不知何时停了。前面似乎有一座村庄,完全深陷在戈壁之中,若不是因为有楼房和比较密集的杨树,几乎和戈壁大漠没有区别。我看到,一些门店上写着鼎新镇某某饭馆、小卖部等名字。带兵的干部说:“这里以前是县城,名字叫毛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划归金塔县管理。”由此开始,村庄逐渐多了起来,之间的距离也不过三五华里。这时候我已经明确地意识到,我将要到达和长期驻扎的地方,一定和这里的村镇差不多,所有的一切都将被黄沙包围。
果不其然,车子到一座营门前停下,一些老兵分列两旁,敲锣打鼓,欢迎我IzS5ft+i/wQJkrTpDYEH6jl5bUADSCEDz8dgaAsu3W8=们。我背着行李下车,首先看了看四周的环境。营门之外,长着一些枝干极度扭曲的树木,据说名叫沙枣树,还有一些灰扑扑的榆树,剩下的便是枯干的荒草了,一丛丛的,茂密地在风中发出飒飒的响声。我们席地而坐,带兵的干部逐一喊响我们的名字。我和其他战友一进大门,就看到了整齐的杨树,以及掩映在杨树背后的灰色楼房。我想这就是军营了。未来数年的时光,我将在这里度过。我还特别注意到,这里的乌鸦尤其多,在杨树上下,不停地翻飞,不停地呱呱叫喊。
当晚,趁着上厕所的时间,我又站在新兵连的院子里,四下张望了一会儿。只见天空晦暗不明,但显得特别高远和深邃,与我们老家南太行乡村的天空迥然有别。风大得出奇,也很远,吼叫声听起来像是无数的骏马在同时奔跑。我忽然觉得,这沙漠之地,总是有着强烈的沙场的意味。当晚,从连长口中我也才得知,这片沙漠的名字叫作巴丹吉林,出自蒙古语,意思是海子或者沙漠中的湖泊。还有就是因为这里住着牧民,还有七个水波潋滟的海子,因而被称为巴丹吉林,是世界上海拔最高、湖泊最多、鸣沙声最大的沙漠。因其平均日照时间长、视野开阔、无人区面积大等,便于组织试验训练,所以成为我们这支部队的永久驻地。
内心的天空与亮光
某年初冬的一个晚上,电话响了,接起一听,我就知道是赵长宙。他是河北籍战士。他说了一些客气话,赵长宙语气虔诚地说:“杨哥,我还想回部队,有没有办法?”我说:“扯,你小子提前退伍几年了,还想回来,不可能!”赵长宙叹了一口气又说:“杨哥,我觉得还是部队好,更想再回西北……玉门……看看。”听到这里,我也叹息一声说:“兄弟,你的想法我理解,可没有这样的政策和先例。想回来看看,这个没问题,我个人随时欢迎。”
我脑子里出现一个个子稍矮、脸庞方圆、语速很快、富有幽默感的战士形象。
很多年前,一个夏天的傍晚,落日熔金,灿烂辉煌。我正骑着自行车从营区马路回家里吃饭,看到一个穿大裤衩、上身套着一件红背心的小伙子迎面走来。因为肚子饿,我把自行车当成了越野车,闪过去之后,猛然想到,刚才那个小伙子,应该是我们单位新分来的那名战士吧。
果不其然,雷打不动的周五科务会上,我见到了赵长宙。科里有七八个干部,三四个战士。干部分工不同,各司其职,战士大都在文化活动中心和体育馆工作。在七零八落的“肩扛星星”的干部当中,战士的“拐把”肩章显得有些寥落。
科长正在讲话,我瞄了一眼赵长宙。他跷着二郎腿,斜着脑袋,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我心想,这小子,估计很快就会到基层的。
两个月后,我由宣传科到基层连队任职。因为试训任务重,手下有七八十号人,忙了白天,晚上还得看这帮小子睡好没有,遇到有心事和有实际困难的,我这个指导员必须首当其冲。当兵的人走在一起,就是兄弟。一个连队更是如此,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有一天晚上,我照例巡查了一圈。兄弟们都睡得鼻息均匀了,我回到宿舍,正在洗漱,电话响了。是赵长宙,他说他想到基层单位去,可没有熟悉的人。他的意思我也明白,也觉得自己的预想果真没错。我说:“你来吧。我明天给军务部门说一下。”他起初沮丧的口气立马振奋了起来,说:“还是老乡好,杨哥够意思!”我说:“你就别扯了。能不能到我这里来,还要看军务部门和领导的决定。”他口气又沮丧了一下,说:“有杨哥出面,肯定没问题。”军务科长是当年接我来部队的老领导,我电话说了赵长宙的具体情况。他笑着说,那小子有点儿刺毛,在宣传科和其他几个战士闹不来。这个情况我也清楚,就对老科长说:“我觉得,没有带不好的兵,只有不会带的人。”
科长说:“你自己有信心就好。”
我所在的连队,处在巴丹吉林沙漠深处,距离基地机关所在地还有八十公里。一出门就是茫茫戈壁,再远处,是黄沙如金、层层叠叠的沙丘。天空常年湛蓝,幽深得似乎遥迢的通天之路。我趁去机关开会的时机,把赵长宙接了过来。初来乍到,赵长宙很乖。我先是让他去饭堂做饭,又让他跟着老战士上雷达。这小子也非常争气,各方面都做得比较好。政治处下通知要求,各连队找一些文艺骨干,弄几个节目,元旦举办一台晚会。我五音尚全,勉强会唱一些军歌。连队里那些兄弟,百分之八十就会扯着嗓子干吼,要找几个能上台表演的还真难。
赵长宙居然会唱歌,还会说相声、演小品。这是我没想到的。这敢情好,要把他用上,再加上另外两个战士,凑几个节目没啥大问题。赵长宙对我说:“指导员,全是光棍棒子上台表演节目有啥意思?咱得找一点儿姹紫嫣红才好吧?”我说:“你小子异想天开,这兔子不拉屎、鸟儿飞断翅的不毛之地,除了沙枣花有母的,连芨芨草都干支棱着。”赵长宙诡秘一笑,凑近我小声说:“那边‘大漠酒家’有一个女服务员,唱歌唱得特别好。”我一听,瞪着眼睛问他:“你怎么知道的?”赵长宙嘿嘿一笑,说:“指导员,咱四团外面的每一颗沙子我都晓得!”
也算走运,我们连队的节目大受好评。那个叫刘亚梅的女孩子是主力,当然还有赵长宙和另外两个战士。我代表连队上台领最佳组织奖。赵长宙也上台领了奖品,团政委亲自为他发奖。在连队军人大会上,我表扬了赵长宙等三名战士,私下又把赵长宙叫到办公室来,对他说:“你把奖品送给刘亚梅吧。”我话刚出口,赵长宙的脸就成了一朵花,转身出门就直奔“大漠酒家”。
转眼到了次年五月,基地组织篮球联赛,政治处人手少,就让我带队到机关所在地参加比赛。我叫上赵长宙随队打杂。有一天晚上,政委来给球员们鼓劲,我想叫赵长宙去买一些饮用水来,可到处找了个遍,也不见赵长宙的半根毫毛。我气归气,心想:这小子估计又去他某一个老乡那里喝酒去了,每次都喝多,喝多了,即使歪到公厕里,他也睡得呼呼的,说不定半夜醒了,就自己回来了。
忐忑不安地等到第二天早上,赵长宙还是神鬼不见。我气急败坏,和连长商议着如何把这个突发情况上报团里。
正在这时候,电话响了,是甘肃玉门的号码。我接听,话筒里传来赵长宙的声音。他说:“指导员,杨哥,非常对不起,我自己偷跑到玉门来是因为……”我没听他说完,就劈头盖脸骂了起来,说:“你这个小兔崽子,跑出去也不给老子说句话,害得老子和连长挖地三尺找你个小兔崽子。”
我咆哮了一通,赵长宙悠悠叹了一口气,带着哭腔说:“指导员,是我不对,我对不起你和连长。可你们能不能等我回去,再细细给你说?”我看了一下连长。连长也气得满地转圈胡乱吼,正要继续咆哮,我朝他摆了摆手。
两天后,赵长宙回来了。一进门,脸上就挂着两行热泪,眼睛红肿像两只大桃子。
几天后,赵长宙申请提前退伍。我和连长劝了他几次,参谋长和政治处主任也是这个意思。无奈赵长宙去意已诀,办理了提前退伍手续。我去送他。到酒泉市,赵长宙提议再去一次玉门。我点了点头。我们二人灰头土脸到了玉门镇,又找了一辆摩的,狼烟滚滚地去到了一个村子,却没进村,而是转到了一面大戈壁滩旁边。赵长宙带着我,走到一座新坟前跪下,放声号啕。
我也脱下帽子,向那个突患白血病去世的女子刘亚梅的坟墓鞠了三个躬。到赵长宙入伍时的城市,我抱了抱他,低声说:“兄弟,你的心里有一片广阔的天空。”
是的,我的兄弟
他来电话之前的三十秒,我正在成都人民中路三段大步流星,看到一个穿军装的战友正在过马路,脑子里忽然出现了一个个子高挑、浓眉、脸色白皙、唇红齿白的年轻军人。唯一不同的是,眼前的那个军人穿陆军服装,我脑际闪现的却是穿空军服装。我脑子里那个形象还没闪过去,电话响了,一看,竟然就是我一刹那间想到的张汝松。
几年前,我在驻巴丹吉林沙漠的空军某部服役。政治学习大活动开始,政治部主任就把我安排到了专门成立的临时办公室。三四个从不同单位抽调来的干部,每天都要忙到凌晨三点多。其中的张汝松不久前由二团调到组织科当干事,办公室成立后,他直接参与进来。那好像是春天或者夏天刚进行了半个月左右,巴丹吉林沙漠西部边缘的军营内绿树簇拥,花朵盛开,热烈的空气干燥,却含有多种气味混合的味道。临时成立的办公室行使职能要费一番周折,必须由最高首长以开会的名义召集各单位军政主官和部门领导严肃通告才行。四个人里面,我算是老机关,摇笔杆子、装腔作势的时间最长。领导也知道这一点,分工让我主要负责各类公文的统筹和撰写。
相对其他同事,张汝松转政工时间最短,写起来有些吃力。我就对他说:“兄弟,凡事亲力亲为就好写,生拉硬扯确实费脑筋。以后你还是多做协调工作,跟着领导多参与具体活动,这样的话,屁股一落凳子,脑子就有话说了。”张汝松笑着回答说:“还是杨哥你经验丰富!”在场的其他同事说:“姜还是老的辣,兵还是老的牛!”
几个人一阵说笑后,我却发现,张汝松总一脸忧郁,白皙的脸上好像落了一层轻薄的灰尘。很多时候,我的电脑后面总是传来轻微的叹息声。
好像一阵忙乱之后,就“秋风萧瑟今又是”了。骄横的西风横行于沙漠和周边绿洲,一夜之间就把枝繁叶茂的军营与荒芜的戈壁混为一体。这时候,我们临时办公室的一个战友因为调职而离开,四个人变成了三个人,可工作量一点儿没减轻。有一次,上级检查后,认为有些方面需要整改。政治部主任把我们三个叫到办公室说:“明天上午开个会,叫各单位政工领导、股长、干事都来。”回到办公室,我让张汝松通知各单位,并布置好会场。另一个同事起草政治部主任讲话稿,我来写政委的讲话稿和改进措施。三个人到距离办公楼最近的一家小餐馆里一番风卷残云再回办公室。
半夜一点,讲话稿也写得差不多了,张汝松和另外一个同事都困得实在不行。我就说:“你俩回去睡吧,明天早上早点儿来。”一时间,忙碌的办公室沉寂了下来,暖气蒸腾,我敲键盘的声音好像是空谷回声。凌晨三点,我起身去卫生间,走廊灯光稀薄,对面拐角一片暗影。从卫生间出来,我总觉得身后暗影处有一些眼睛在盯着我看。我紧走几步,关上办公室门。再次坐下来写改进措施的时候,强烈的饥饿感如潮水一般冲袭而来。我翻遍所有抽屉,连一粒瓜子都没有找到。再坐下,却发现饥饿竟使得我几乎丧失意志。只好出门下楼,却没想到,一场大雪在我不知觉的时候铺满台阶,并铺展向整个巴丹吉林沙漠。
蹚着黎明的大雪回到办公室,掏钥匙开门,却发现门是开的,快步跨进去,发现张汝松已经来了。桌子上放着一盒方便面和一根粗大的火腿肠。见我进来,张汝松冲方便面努了下嘴说:“这不,就知道你会饿!”好像一眨眼,太阳升起,把满地的积雪照得满地流银,光芒闪烁,似乎是雪白星空。工作告一段落后,我发现,张汝松的叹息更加频繁,忧郁使得他脸上过早地有了皱纹。
我问他怎么了。张汝松皱眉叹息说:“杨哥,我该咋办啊?”
我说:“咋了嘛兄弟?”
张汝松说:“要再不回去,老婆就要和我离婚!”
我知道他和他老婆两地分居,一个在石家庄,一个在巴丹吉林沙漠。这不,他老婆又生了孩子。张汝松不想离开部队,可又觉得老婆无论如何逼他都在情理之中。我完全理解,就对他说,当兵体现男人刚韧铁血,爱老婆也是柔肠寸心,两者缺一不可。
我给他出了几个主意,如调回石家庄,实在不行,只有转业这一条路了。张汝松留恋地说:“最好是调过去。脱军装……唉。”说到这里,他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领花,又在军装前襟上弹了弹。我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第二年春天,我由空军调入原成都军区工作。临走的时候,和张汝松聊了很久。我们都知道,调回去难度堪比登天。可他非常爱他老婆,心疼她一个人又上班又带孩子。更严重的是他老婆单位同事老是在她面前说她们自己的老公是这样那样的体贴和好。不管怎样的内容,对一个丈夫远在西北的年轻女子而言都会饱受刺激、心有所感。
我没想到,张汝松随后转业回了石家庄,很快就参加了工作。他说,把这个消息第一个告诉我,是觉得我是真正理解他的人。我笑笑说:“兄弟,这不挺好的嘛!好好混,你会更好的!”张汝松叹息一声,声音低沉地说:“杨哥,我还是觉得部队好。部队随意。在财政和民政厅之间,我选择了民政厅,而且主动要求到复转军人安置办公室。”我“哦”了一声,似乎明白了什么。张汝松笑笑说:“你出营门都穿军装吗?”我说:“有时候穿,有时候不穿。”
张汝松“啊”了一声,沉默了几秒钟,语气低婉地对我说:“多穿穿军装吧,杨哥!”听了他这句话,我忽然肃穆起来,停住脚步,大声说:“是!我的好兄弟!”
【作者简介】杨献平,河北沙河人。作品见于《天涯》《中国作家》《人民文学》《江南》《长江文艺》《大家》《红豆》等刊。已出版“巴丹吉林沙漠文学地理”系列,包括《沙漠里的细水微光》《黄沙与绿洲之间》《沙漠的巴丹吉林》《弱水流沙之地》《黄沙飞雪:河西走廊之书》;“南太行文学地理”《生死故乡》《作为故乡的南太行》《自然村列记》《南太行纪事》,“成都记”系列,包括《中年纪》《西南记:北纬三十度的河山地理》,以及多部长、中短篇小说和诗集《命中》《谈论》等。曾获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首届三毛散文奖、首届朱自清文学奖散文奖、四川文学奖、百花文学奖等奖项。
责任编辑 练彩利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