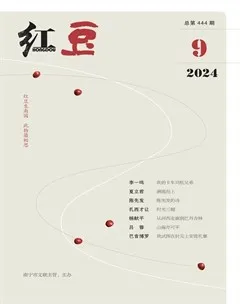剑器行
2024-10-30易清华
那天晚上回到家,客厅里灯光幽暗,母亲躺在沙发上看电视。陈诗然从母亲身边经过时,她没有任何反应,大概是睡着了,倒是父亲从阳台上走了过来,端着一盆刚开花的鸢尾。
“诗然,你回来得正好,等下会有大雨。”
“是吗?爸。”
“是的,气象局刚发布预警,风力五到六级,有雷阵雨。所以,我得把这些花搬进屋里。”
这天晚上,陈诗然约了男友白光和闺密刘雯去看话剧《我爱桃花》,没想到他们姗姗来迟。一个迟到了三分钟,一个迟到了五分钟,理由是堵车。在剧院门口,陈诗然和白光吵了起来。白光认为看话剧不过是看明星,迟到几分钟无关紧要,而陈诗然认为,看话剧如果只是看明星,那还不如不看。刘雯既不支持陈诗然,也不反对白光。最终的结果是,白光和刘雯进了剧院,而陈诗然一气之下回了家。
陈诗然洗漱后,走进卧室,在电脑前点开收藏的网页。这是她临睡前打发时间的唯一方式。她喜欢精致、典雅且带有一定潜在危险的东西。以前迷恋过打火机,先后收藏了上千款图片,并选出十个她最喜欢的款式,但她不抽烟,也从未拥有过任何一只实物。照刘雯的话说,她只是个形式上的恋物癖。而几年后,她又迷恋起剑器。和迷恋打火机一样,她又陆续收藏了上千款图片,对名匠制造的各式剑器了然于胸,且又选出十款她最喜欢的样式,并一一附上标注的文字。
突然“嘀”的一声,陈诗然下意识地拿起手机。是白光发来的微信:“诗然,要是我们再这样无休止地吵下去,我觉得还不如分手。”陈诗然猛地站了起来,迅速换好出门的衣服。就在拉开卧室的门时,她愣怔了一下,反身回到飘窗,拉开双层天鹅绒窗帘,外面果真下起了大雨。
一个小时后,陈诗然打着伞出现在了渔人码头。那是江边的一个夜宵场所,五颜六色的灯光下,数十家夜宵店一字排开。当她拿着两把伞站在一家人满为患的店门口时,看到白光站起来和人碰杯,颇有种开怀畅饮的味道。刘雯坐在白光的对面,一直在玩着手机。那些人她都能叫出名字,是经常在一起聚会的朋友。
陈诗然一直站在白光的视域里,足足有十分钟时间,有一次甚至感觉到他的目光停留在了她脸上,但他仍然无动于衷,仿佛没有看见她。那目光里有一个巨大的空洞,她不过是一粒尘埃。白光豪饮的声音一次次传来,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他的酒杯里。雨越下越大,在自然和人声的喧嚣里,陈诗然选择了离去。
回家后,陈诗然仍没有睡意。她坐在电脑前,打开网页,浏览那些闪光的剑器图片,忍不住网购了一把宝剑。
一个周末,陈诗然收到了快递送来的宝剑。
在卧室里,陈诗然洗手焚香,从一个长条形的花梨木盒里取出她的宝剑。这把剑长达七十厘米,她一手托着剑鞘,一手握着铜锌一体的金属剑柄,认真地端详。剑鞘用上等的金丝楠木制成,鞘上的凤尾纹饰与金色护环流光溢彩。剑柄更为讲究,其上翔龙环绕,是最先进的镂空浮雕工艺。陈诗然不由得点点头,缓缓地抽出剑身,其材质是高锰钢烤蓝,且镏金。她忽左忽右地晃了几下,便将剑插入鞘内,放进了剑盒。
一天,陈诗然接到了刘雯打来的电话。
“你要跟白光分手吗?”
“他是提出来过。”
“什么时候?”
“我想想,大概是一个月前。”
“怎么没听你说?”
“我一忙,忘了。”
其实,陈诗然和刘雯在上个星期还见过一面。在荷糖月色咖啡馆,刘雯送给她一支香奈儿丝绒亚光口红。两人从双方的父母聊到了曾经的同学,甚至还聊到了一只叫黑格尔的猫和一盆玉簪,而陈诗然都没有跟刘雯谈到白光。
“你和白光谈了八年,难道他一条微信说分,你就和他分了?诗然,我觉得你不对劲,你现在连我都不信任了。”
陈诗然能感觉到刘雯在电话那头的愤怒。
“不是,刘雯,你别这样想,我怎么会不信任你?”
“那你在忙什么?”
“我在云上俱乐部学剑舞。”
陈诗然一只手将电话贴在耳边,另一只手还在舞着那把剑,并下意识地挽了个剑花。由于训练的时间短,那个剑花乍看名不副实,但仍然有那么一点儿意思,像蜻蜓点水,将细长的尾巴弯成弓状伸进水中,弹开一圈圈涟漪。
“啊!”刘雯在电话那头惊叫一声。
陈诗然的手臂猛地一抖,咣的一声,那把剑掉到了地上。不说刘雯,陈诗然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学剑舞。
六岁时,父亲曾心血来潮,给陈诗然报过一个少儿舞蹈班。但只学了一个月,就因为一个调皮的小男孩模仿了她的动作——那动作有点儿像鸭子,她就再也不去上舞蹈班了,不管父亲怎么连哄带骗,就是不去。从此以后,陈诗然就与舞蹈绝缘了。无论是上大学时还是在单位,她可以唱歌、拉小提琴,甚至演讲,但只要涉及跳舞,哪怕只需要她浑水摸鱼,躲在队伍后面伸展一下腰肢,她也一概拒绝。作为闺密,刘雯当然知道陈诗然这个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
剑舞班设在云上俱乐部三楼一间不大的教室里,只有八个身着汉服的女学员,和一个穿着绿色教练服的年轻女教练。刘雯趴在窗台上偷窥。舞者们绾着相同的发髻,身着水红或粉红的绸缎宽袖长裙衫,白色的棉麻阔腿裤,动作整齐划一。但刘雯还是一眼就将陈诗然认了出来。她毕竟年轻,和那些舞伴相比,身上仿佛有一种灼人的光亮。
一个小时后,刘雯和陈诗然在荷糖月色咖啡馆坐了下来。
“你突然跳起舞来了,是因为那把宝剑吗?以前你喜欢打火机,有次消夜,林军喝多了,想送你一只镶金的Zippo,我叫他别送,是怕你有了打火机,就开始抽烟。”
“这是什么逻辑?难道有了打火机,就一定得抽烟?”
“你有了一把剑,难道就非得跳舞?”
“如果我不用来跳舞,刘小姐,难道用它来杀人,或者像日本武士那样用来切腹?”
“陈诗然,你还越说越离谱儿,我不跟你讲!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和白光见个面。这样吧,等下我组个局,多叫几个人,就喝喝酒,你想理他就理,不想理就别理,至少给彼此一个台阶。”
“不行,我约了小银教练,我要学会那个剑花,还有劈闪。”
陈诗然说着,顺手抄起手机,把它当作一把剑,在空中唰唰唰地划出几道弧线,紧接着伸直胳膊,像电视中的一个特技镜头般横空而出,然后手腕一百八十度旋转,一个劈闪,笑着将手机的一个角抵在了刘雯额头。
“滚你的。”刘雯一把推开陈诗然的胳膊。
夜晚湖边的沙滩上,一群人围着一尊雕像吃烧烤,喝啤酒,甚至跳舞。她一个人沿着一条白色的小道来到湖边,将所有的喧闹抛在身后。她坐了下来,几道石砌的台阶浸在浅浅的湖水中。没有人知道她来到了这里。
夜晚在五百米外变得漆黑、静谧,且有点儿蓝。那是月光和云层制造出来的效果。她之所以逃到这里,是因为一个留着长发的潮男几次怂恿她跳舞。渐渐地,月亮从层层叠叠的云层中穿出,倒映在不远的湖面,在黑黢黢的湖水中开辟出一条光的隧道。她脱掉鞋袜,将两条腿伸进湖水中。随着双腿的摆动,湖水荡漾起来。在粼粼波光中,那条光的隧道滚动的布匹般铺展过来,停在她的脚下。陈诗然一阵恍惚,仿佛在那条光隧道里穿行。这是她以前从未到达的地方,仿佛灵魂之境。想起小时候,一条落叶缤纷的小径上,父亲牵着她的手,前往山中一个隐士的石屋。那个隐士将为她治疗失眠症。有段时间,她整晚整晚睡不着。那天父亲牵着她的手,她问他:“爸爸,你相信灵魂吗?”“当然相信。”父亲不假思索地说。现在想来,或许父亲的回答并非本意,但想到她面对医生的恐惧,才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两个酒鬼突然冒了出来,陈诗然夹在两具庞大的身躯中间,不能动弹。她发出求救的声音,嘴便被捂住。他们需要安慰,她就得用冰凉的小手轻抚他们宽阔的胸膛。在恐惧中,她一直没有放弃挣扎。一个闻讯而来的男生试图干预,被吓走。紧接着刘雯冲了过来,双手高举着一块巨大的卵石,扬言要砸碎两个酒鬼的狗头。
刘雯搂着瑟瑟发抖的陈诗然说:“别怕,有我在。”从此两个人形影不离。
三年后,ULODc969dP+3KRJIjqB4ZPH/Qt4VGVyhVHFgioaxVmI=她们大学毕业。那年刘雯意外怀孕了。陈诗然是第一个知道消息的人。两个人商量了很久,根本拿不定主意。
林军大刘雯八岁,是一家文化公司的老板,家底殷实。那段时间他频繁相亲,刘雯只是他长长候选名单中的一个序号。结婚后,刘雯终于弄清原因,林军父亲患了肺癌,那场在外人看来无比风光的婚礼,实际上只是一场祈福法会。而她腹中的孩子,是怀着使命而来,为挽救另外一个人的生命。一次刘雯喝醉了酒,带着哭腔说,林涅槃根本不是她的儿子。“那是谁的儿子?”陈诗然差点儿将一口啤酒喷在刘雯脸上。刘雯说她还没有怀孕的时候,他们就给他取好了名字,叫林涅槃。如果那次她没有怀孕,是另外一个女人怀孕,他一样叫林涅槃,一样是林军的儿子,所以林涅槃根本就不是她刘雯的儿子。陈诗然一把夺过刘雯手中的啤酒瓶。“刘雯,你跟我说,你到底想干什么?”刘雯刹那间变得冷静,一字一顿地说:“诗然,我要生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孩子。”
陈诗然见过林军的母亲几次,那是个有着强大气场的女人。自从丈夫病逝后,她不仅将丈夫的公司打理得风生水起,还安排了林涅槃的一切,从不让刘雯操心半分。然而,刘雯没能给林家带来好运,哪怕让公公多活上个三五天。
当时白光是林军公司的创意总监,陈诗然在单位里负责宣传,压力不小,刘雯让白光给她出了不少点子。
二十四岁那年,陈诗然和白光开始筹备婚礼。原打算在当年的国庆小长假结婚,没想到在结婚前两个月,白光做出了人生中一个重大的决定,离开林军的公司和朋友合伙创办了一家新的公司。那段时间,白光忙得不见人影,婚期日近,陈诗然不得不请刘雯帮她去诺门挑选婚纱。
诺门的老板芸娘见刘雯来了,快速打发掉手上的客户,亲自为陈诗然服务。芸娘是个极为精明的商人,她独创了挑选婚纱的水果分类法。这几乎是一个天才的创意,从水果的形状、大小、色泽和质地乃至气味来界定一袭婚纱,甚至尺寸和身材都不重要,完全取决于客户对某种水果的好感。在光线舒适的诺门厅堂,陈诗然先是试了一袭菠萝型婚纱,又试了一袭榴莲型婚纱,这是芸娘给出的参考意见。后来陈诗然觉得雪梨型婚纱也可一试,因为她平素最喜欢吃的水果是梨。
平时挑选衣服,刘雯往往显得比陈诗然更有主意。这次挑选婚纱,陈诗然知道,做出最后选择的,还得是刘雯。但没想到在征求她的意见时,她总是先点头,然后摇头,让本来兴致勃勃的陈诗然在宽大的试衣间里无所适从。最终聪明的芸娘似乎看出了端倪,说更多新的水果还在制作中,请她们稍缓时日再来,到时定有惊喜。
在附近的咖啡馆里,刘雯抿了一小口卡布奇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诗然,白光刚开公司,压力很大,他想将婚礼延迟几个月。”
陈诗然手臂一颤,差点儿将面前的咖啡打翻。
“诗然,别激动,你想想,一个人结婚图什么?无非是图日后有幸福的生活。而幸福的生活,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要是婚后白光生活无着、流离失所,你们会幸福吗?”
陈诗然将目光投向窗外。良久,才扭过目光,凝视着对面的刘雯。
“那好吧,我听你的。对了,记得到时我要穿雪梨型婚纱。”
几年后,陈诗然仍然能清晰地听见自己在诺门婚纱店的声音。那个声音穿越岁月的迷雾与重影,宛若一把利剑呼啸而至,在抵达她胸口时,变成了一朵蓝色的雏菊,在她的呼吸里散发出一缕苦涩的清香。
陈诗然闭上眼,感觉自己的手臂在延长,那是剑的作用。剑舞是刚柔并济的艺术,剑花是莺燕婉转,劈闪是蛟龙出海。这次单独训练,陈诗然重在劈闪,那剑在手臂的作用下变得锋利,仿佛要将她眼前所有坚固的东西刺穿,在层层壁垒中打出一条光的隧道。
二十六岁那年,陈诗然遭遇到了刘雯二十一岁时所遭遇的事情,意外怀孕了。那天陈诗然在医院确定怀孕后,准备在电话里告诉白光,而白光却先告诉她,第二天他就要坐飞机去上海,可能要去三四个月。如果这次顺利拿下那个项目,以后他们的孩子至少可以少奋斗二十年。他雄心勃勃,且滔滔不绝,容不得她插入一句话,而且他还提到了孩子。
陈诗然想,她不能拖他的后腿。
去上海后,白光隔三岔五地汇报工作,每次都让她在电话里插不上话。
一天傍晚,陈诗然和刘雯在沿江风光带散步。走着走着,一轮淡黄的月亮挂在了城市上空。她们坐在一把长椅上休息时,看到对街楼宇上的一幅别墅广告。画面上两只完美的手,明显看得出是一对母子的手,托出一片巨大的海棠叶。随着灯光的明暗,海棠叶片上的脉络渐渐呈现出一层层别墅的倒影。随后,被细致表现出的建筑元素,那栏杆的曲线,墙的造型,从柱子、楼梯到门窗,排列组合和装饰一一展现。刘雯不由得发出感慨:“希望这次白光在上海旗开得胜,到时你们就可以在这样的别墅里结婚了。”这次散步,陈诗然本想告诉刘雯她怀孕的事,而刘雯这个即兴式的感慨,彻底打消了她的念头。
那天她起得很早,去上次检查的那家医院实施人流手术。没想到检查的结果是怀孕超过八十天,医院拒绝手术。走出医院的玻璃转门,陈诗然有一种想哭的感觉,但她知道自己不能哭。一天下午,陈诗然躺在了一家私人妇科诊所的手术床上。她几次想拨打白光的电话,但最终作罢。她紧紧地闭上眼,浑身哆嗦,医生叫她别紧张,但她哆嗦得越发厉害。
此刻,在云上俱乐部的练舞室里,陈诗然舞着剑,脑海里一阵恍惚。继而,抡起剑往空中猛刺。
这不是剑舞。
小银教练微皱着眉头,最后,她示意陈诗然停止训练。陈诗然清醒过来,明白了小银的意思。小银的意思是如果她需要发泄,直接去专门的心理发泄室,没必要跟她学剑舞。不过小银是个善解人意的女孩,她教过的学员无论年纪大小,都会成为她的朋友。两人坐在长椅上喝着陈诗然带来的咖啡,小银伸出一只手给陈诗然按了按肩。
“诗然姐,你最近是不是有些失眠?”
“失眠倒少,就是时常被噩梦惊醒。”
“那我告诉你一个方法,是我发明的,或许对你有用。”小银一边做动作一边说,“睡觉前,你双手合十,让自己彻底安静下来。要安静得像一把挂在墙上的剑,感觉到左手和右手的纹路一一吻合,是那种丝丝入扣的感觉。我把这种方法叫入定。每次十五分钟,形成习惯,就会少做噩梦。”“是吗?”陈诗然半信半疑。“当然,信神者自有神助。”小银爽朗地笑着,同时透着一股神秘。
当天晚上,陈诗然浏览网页到十点,半个小时敷面膜,半个小时洗漱,十一点入睡前,做了一刻钟的入定,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醒来。果然一夜无梦。
那天,白光终于给陈诗然发来了道歉的微信。陈诗然没有接受他的道歉,只是问:“是刘雯让你向我道歉的吗?”白光不再回复。
和白光发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吵,是在引产后的那年。真正意义上的——当时她还没有如此定性。后来再发生几次争吵后,觉得这种争吵的性质在一步步发生变化。已然不是变相的亲昵,更非无伤大雅的胡闹,而是透着一种冷漠。她意识到这一点时,不由得感到后怕。害怕自己对白光的爱,被那源自骨髓的冷漠一点点侵蚀。
有几次,陈诗然都忍不住想告诉白光她曾经引产的事情,但话到嘴边还是打住了。那是一种自我羞辱。如果没有在第一时间告诉他,就永远不要告诉他。而且,要是真的爱一个人,就要燃烧掉过去的自己,从而获得新生。
在跟着小银跳舞时,陈诗然从未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会如此柔韧。
开始,陈诗然要学的其实是剑术,是网购了那把宝剑之后,突然萌生的念头。没想到却报了个剑舞班。她弄清楚状况后,马上要求换班,但云上俱乐部根本没有剑术班。“我不跳舞的。”陈诗然反复向小银教练声明。小银面露难色,说:“退费没有先例。”“这不是钱的问题,是我对跳舞有心理障碍。”陈诗然再次强调。小银立马懂了,说给她三天时间,要么退费,要么给她找一个剑术教练。
三天后,小银打来电话,道歉说财务处不给退费,剑术教练也没找到,其实现在的剑术和剑舞区别不大。言下之意,是要她把剑舞当作剑术来练。反正班上就那么几个学生,且都是她的朋友,她们来学剑舞,也没有什么明确目标,就是大伙儿聚在一起耍个酷。见小银把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陈诗然答应了。
在小银的指导下,陈诗然只练剑花和劈闪。没想到几次下来,就练得有模有样了。小银笑着对她说:“你可以毕业了。”“你就别笑我了,我这人还是有自知之明的。”陈诗然说。小银说:“你如果真要练好剑花和劈闪,还是要有舞蹈的基本功,否则就是空中楼阁。你对舞蹈有心理障碍,这个不要紧,慢慢来,相信能找到克服的办法。”
几天后,父母去云南旅游了,陈诗然将小银请到家里,在卧室里跳舞。只开着微弱的灯光。小银出生在湘西凤凰,从三岁开始学民族舞,舞服是那种叮当作响的银饰服装。到省城上艺校后,她学的是民族舞,但已经改良过,透着一股现代风。陈诗然取出那把闪闪发光的宝剑。小时候的情结瞬间被打开,一个跳起舞来像鸭子的小女孩,如果她手中拿的不是一条彩带,而是一把剑,没有任何一个小男孩敢来取笑她。陈诗然感觉身体某处嘎地一响,整个人仿佛发生了质的变化。
此后,陈诗然的剑舞日益精进。那段日子,她一直沉浸在剑舞的训练当中,直到有一天,她看到了舞室角落里一个男人的眼睛。
沈默然是小银的同乡,从海外归来不久,在江边开了个茶社,叫九歌,不重经营,基本上是他的书法工作室。刚开始时,陈诗然在舞室里见到他,印象并不好,感觉他是个猥琐的花痴,或是一个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直到有一天小银告诉她,那人痴迷于书法,来观摩剑舞,是为了寻找灵感。陈诗然不解,小银说:“你知道杜甫有首诗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吗?”陈诗然点头又摇头,小银往下说,“诗中讲述了一个叫公孙大娘的舞者,她的剑舞出神入化,源远流长。”“这与书法有关系?”陈诗然问。“当然有关系,你知道的,唐朝有个大书法家叫张旭,史称草圣,他的草书,就是在揣摩了公孙大娘的剑舞后发生了质的飞跃。老沈在第一次看你剑舞时,就说你的舞姿有公孙大娘遗风,矫健、飘逸,且超凡脱俗。”陈诗然说:“那怎么可能?我才学多久?”小银顿了顿,说:“这与时间长短没有关系,关键是气质,是天赋,艺术家们都看重这个。”
几天后,陈诗然跟着小银和剑舞班几个学员去了沈默然的九歌茶社,才知道老沈不仅痴迷书法,还是个不折不扣的会享受生活的人。茶社里一色的清朝老式家具,茶叶都装在精致的陶罐里,特别是还有一些自制的蜜饯,是用香草和野果制作的。他带她们参观了他的制作间,并向她们介绍了蜜饯的制作过程。在水边采来江离和白芷的叶子,以及小棵的杜衡草,洗净晒干后,同干酸枣一起入坛,再加以少许蜂蜜和黄酒,要密封一个月。更绝的是,他还给那道蜜饯取了一个名字,叫思美人。这是《楚辞》里一首诗的名字。
那段时间,除了上班,她们几乎都泡在老沈的九歌茶社。除了喝茶聊天儿,欣赏老沈的书法,她们还在二楼的大包厢里跳起了剑舞,并将湘西民族舞融入进来,尝试着编排了一出《九歌剑器舞》。
刘雯几次打电话来,要求见面,陈诗然都以各种借口婉拒,直到有一天,刘雯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诗然,你是不是打算跟我绝交?”
“刘雯,怎么可能?”
“那你为什么不见我?”
“这段时间,我确实比较忙,你晚上有时间吗?”
刘雯来到九歌茶社时,她们正在二楼的包厢里跳《九歌剑器舞》。老沈用红茶和蜜饯热忱地款待刘雯。这一次,刘雯似乎性情大变,没了逼人的气势,还给她们带来了圣罗兰美妆口红,甚至在她们表演时一次次鼓掌。
晚上十一点,就在她们准备离开九歌茶社时,刘雯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说是白光一个人在渔人码头的夜宵摊上喝得人事不省。她们驱车赶到时,果然看见白光醉卧在一把长椅上。她们叫醒他,扶着他入住附近一家宾馆。在宾馆房间,白光酒醒大半,撑起头对陈诗然说:“诗然,对不起,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都没有给你想要的生活,甚至一桩婚姻。”白光哽咽起来,陈诗然将一条空调被盖上他的胸口,欲言又止。她一转身躲进卫生间,打开水龙头,嘤嘤哭泣。
在开车送陈诗然回家的路上,刘雯与陈诗然发生口角。“你和白光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不是因为那个沈默然?”刘雯直截了当地诘问。陈诗然一下子来了气,说:“刘雯,你这说的是什么屁话?白光说要和我分手时,我都不认识沈默然。”“但你现在认识了。”刘雯不依不饶。陈诗然不再理她,低头看起了手机微信。她没想到刘雯会提到老沈,这倒是令她心中一动。是刘雯提醒了她,既然现在已经认识,或许将来就能发生什么。恰在这时,老沈给她发来一条微信:“到家了吗?”
“快到了。”
两人一来一往,皆是简单的问讯。
突然想起在九歌茶社所吃的那道叫思美人的蜜饯,陈诗然的手指在手机键盘上飞动,快速地打出一行字。
“想吃一道叫招魂的蜜饯。”
“我给你做。”
几秒钟过去,陈诗然便收到了老沈的回复。此后两人仿佛达成了默契,都没有往下聊。有此一句,所有的话已是多余。
“诗然,你是在和白光聊天儿吗?”手握方向盘的刘雯终于忍不住问。
“不,是和沈默然。刘雯,你的感觉没错,我喜欢老沈,他让我有一种安全感。这个,你可以告诉白光。”
刘雯一时无语。陈诗然将副驾驶室的车窗摇下。一阵轻风刮进车内,她深深地呼吸,嗅到了一股隐隐的花香。
第二天傍晚,陈诗然来到九歌茶社,刚好最后一拨客人离开。沈默然为她端来了那道精心制作的蜜饯。有切成丝的干紫苏和江离叶,有水堇和蒌蒿的嫩茎,还有花椒颗粒和腌制的桃片,可谓赤橙黄绿青蓝紫,煞是养眼。这是他为她一个人制作的招魂蜜饯。两人在《二泉映月》的乐声里相对而坐。招魂的味道果然跟思美人不同,思美人重在酸和甜,而招魂则重在辣和麻,还透着一丝苦。她胃口大开,不一会儿,感觉到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他竟然从怀里取出一方丝帕,轻轻地替她擦去汗珠。那丝帕带着蕙兰的香气。他举止得体,有君子之风。
深夜,卧室里灯光幽暗。陈诗然穿着乳白色丝绸睡衣,手执那把宝剑,在床上跳舞。是一个人的《九歌剑器舞》。她尝试着舞出一个个剑花。墙壁上光影晃动,有时是一朵大写意的墨菊,有时是一笔幽兰,妙趣横生。
突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电视静音,屏幕上光影不断流动、闪烁。陈诗然没有想到父母会催她和白光结婚。他们选择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刻,是为了更显庄重。“你们都谈了这么多年了,他一直对你不错,而且,也相当努力,如今像他这么有上进心的人不多了。”父母以难得的默契,你一言我一语地劝她。
一天,在九歌茶社喝茶时,白光来了。那一幕又重演,只是换了主角。那一次是刘雯催白光和她结婚。陈诗然一言不发,为了打破僵局,小银提议跳舞,得到剑舞班几个学员的响应。在她们款款起舞时,老沈在书案边写下狂草——今有佳人陈诗然,一舞剑器动吾心。
收下老沈的书法后,陈诗然含着泪光,老沈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当天晚上,老沈和白光喝起了酒,推杯换盏,意兴甚浓。而小银觉出陈诗然的不适,提出到江边散步。三个人走出茶社,刘雯还带着她的狗。一路上,刘雯都在讲她的狗如何幽默、怎么有趣。一开始,陈诗然还能忍受,后来终于忍不住,插嘴问:“刘雯,你这狗叫什么名字?”刘雯勒了一下绳子,让在前面蹦跶的小狗回过头,对着它招手,“来,宝贝,告诉你陈阿姨,你叫什么名字?”
其实,陈诗然早知道这条狗的名字叫刘小刘。她之所以如此问,是想打击一下刘雯。“刘雯,你不是一直想生一个刘小刘吗?属于你自己的刘小刘。是林军不想和你生吗?”刘雯脸色骤变。就在这时,刘雯的电话响了起来。是林军打来的,说家里那只叫黑格尔的猫突然闹腾得厉害,要她早点儿回去。刘雯走后,陈诗然和小银坐在一把长椅上闲聊。
“小银,现在全世界的人都觉得我应该和白光结婚,甚至包括老沈,你觉得呢?”
“你爱他吗?”
“当然,本是生死之爱。不怕你笑话,我是个爱情的理想主义者。”
“他爱你吗?”
“当然,但一切似乎都过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弄成这样。”
陈诗然在浓郁的夜色中抬起头,她坐的正是上次和刘雯坐过的那把长椅,于是又看到了对街楼宇上那幅别墅广告。屏幕刚好转换到那片巨大的海棠叶。随着灯光的明暗,海棠叶片上的脉络渐渐呈现出一个婴孩的倒影,好像是从一栋别墅里钻出。陈诗然不由得惊叫:“我的孩子!”整个人差点儿从长椅上摔下。
那是多次出现在她噩梦中的情景。
小银连忙将浑身战栗的陈诗然搂住,说:“诗然姐,你没事吧?我什么也没看到,你是不是产生了幻觉?别怕,有我在。”小银不停地用手轻抚着陈诗然的脸。
那天,是陈诗然的生日。
傍晚,在九歌茶社举行了一个小型的生日派对。小银带着剑舞班几个学员来了,刘雯来了,白光捧着玫瑰来了,最后一个到的是林军。看到林军时,刘雯和白光同时露出吃惊的神情。陈诗然上前解释。昨天她在林总公司办事,不觉漏了一嘴。林军接口道:“老婆闺密生日,我岂有不来之理?”白光夸张地和林军打着招呼,于是昔日的老板和下属来了个熊抱,颇有种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味道。
晚宴由老沈亲自操刀,不算丰富,但别出心裁。先是唱生日歌,许愿,然后分享美食。酒过三巡后,小银带着她们跳起了《九歌剑器舞》。另外的人一边观舞,一边喝酒。小银和几个学员达成了默契,让陈诗然成为主角,由她一人任意主导着舞蹈的流向。
歇舞后,她们重新回到酒桌。每个人又向陈诗然敬了一杯酒,她又回敬一杯。陈诗然不禁有了醉意,端着高脚红酒杯说:“来,我们来做一个游戏。”大家不约而同地响应。
“是杀人游戏。”
有人发出嘘的一声,露出失望的神情。那是在大学时代就玩的一种游戏,考验智力和耐心,需要清醒的头脑。
陈诗然带来了那把宝剑,她举在手中说:“不是那种杀人游戏,是三个人一组,分别扮演丈夫、妻子和情人。这个游戏很简单的,一学便会。”无疑,这个煽动性的游戏勾起了大家的胃口。随后,陈诗然将游戏规则和台词发在了刚建的微信群里。
游戏的第一组,自然由陈诗然来主导。
陈诗然说:“这里有三个角色,我可以扮演的角色是妻子或情人,至于我扮演谁,则由大家举手决定。”
陈诗然说:“赞同我扮演妻子的人请举手。”
赞同陈诗然扮演妻子的有小银、白光和刘雯,还有剑舞班三个学员。
陈诗然又说:“赞同我扮演情人的请举手。”
赞同陈诗然扮演情人的只有林军和老沈。
陈诗然朝空中挥了挥手机,说:“现在由我来扮演妻子,请大家看看微信群里的提示,我要在你们中间选出丈夫和情人。现在我问一句,谁想做我的丈夫?”
林军举起手机抢先道:“我来。”
最终,陈诗然还是选择了白光。没有谁自告奋勇做白光的情人,于是按规则由陈诗然来指定。陈诗然指定了刘雯。“我不。”刘雯借着酒劲,表示不愿意,理由是她不会玩。陈诗然解释说:“这个游戏,源自一出叫《我爱桃花》的话剧,讲的是一起情杀案。三个人都要被杀一遍,要讲出自己不被杀的理由,才能复活,才能往下杀人。刘雯,你看过《我爱桃花》,这么简单的游戏,你不可能不会玩。”
在热烈的掌声中,刘雯不得不走上前来,同陈诗然与白光站在一起。
小银提着一袋塑料仿真桃花瓣,往白光和刘雯的头上撒下,粉红色的花瓣漫天飞舞,在灯光的明亮和暗影里,交织出一种梦幻和迷离的感觉。音乐响了起来。按照微信群里提示的动作,白光和刘雯坐在了一张沙发上。在众人的嘘声下,两人不得不假装相拥。不一会儿,陈诗然提着那把宝剑,模仿一个醉汉的样子,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在五步之外,陈诗然停了下来,在身边的木椅上发出敲门的声音。白光和刘雯离开沙发。陈诗然躺在沙发上,发出鼾声。这时白光站起身,抽出陈诗然身上的剑,在刘雯怂恿的手势下,白光挥剑将妻子杀死。陈诗然假装倒在了地上。
音乐再次响起,小银走了过来,朝陈诗然的身上撒下一把桃花瓣。陈诗然坐了起来,游戏开始反转。陈诗然对提着剑的白光说:“我是你的妻子,一个愿意嫁给你、为你生孩子的人。我不该死,该死的是她,是她勾引了你,破坏了我们的家庭。”陈诗然用手指着刘雯,白光上前一步,一剑将情人杀死。在众人的喝彩下,刘雯也假装倒在了地上,一脸煞白。
掌声响了起来。游戏再一次反转,小银上前朝刘雯身上撒下一把桃花瓣。刘雯坐了起来,对提着剑的白光说:“我爱你,我一直爱着你,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女人,我不该死,你不能杀我。”或许是喝多了酒,刘雯进入了角色,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抽泣。
厅堂里一片静寂。三个玩着游戏的人似乎都忘记了如何将这个游戏玩下去。按照游戏的进程,妻子和情人都有不死的理由,应该是白光在无奈之中选择自杀,但此时他呆若木鸡。
只见林军举着一杯酒蹒跚着走了上来,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指着刘雯问:“我问你,你这是玩游戏,还是假戏真做?”
或许是嗅出了林军话语里的火药味,老沈和小银走了上来。“今天是诗然的生日,只有她才是真正的主角。来,来,我们继续喝酒。”老沈和小银拥着林军走到了座位上。游戏就此结束。
突然,音乐又响了起来。陈诗然开始了独舞。是她一个人的《九歌剑器舞》。一道道剑光闪过,陈诗然的舞姿矫健、敏捷,且飘逸,她仿佛不是在舞蹈,而是整个身子被那把闪闪发光的宝剑所引导。小银和几个学员忍不住鼓起掌。老沈和林军在畅饮。白光和刘雯各自坐在沙发的一角,默然不语。
陈诗然仿佛进入一场梦境,那把宝剑环绕着她的身体,紧贴着她的肌肤,闪光的剑刃自下至上游走,当那剑身环绕着她修长的颈项时,发出嚓的一响。小银和老沈见势不好,冲了上去。在场的人发出惊叫。第一个发现陈诗然不是自刎的是小银,她拉住老沈,回到了座位上。白光和刘雯面面相觑,几个人都恢复到原有的状态,一边喝酒,一边看着陈诗然舞蹈。她的舞姿仍然是那样矫健、敏捷,且飘逸,那把宝剑与她的身姿融为一体。随着嚓嚓几声,锋利的剑刃割下了一缕缕长发。
不一会儿,只听见打火机啪地一响,陈诗然手中腾起一团火光。所有的人都愣住了,呆呆地看着陈诗然在火光中狂舞。
【作者简介】易清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长沙。曾用笔名易清滑在《诗刊》《星星》等上发表大量诗歌,同时致力于小说创作,在《大家》《山花》《当代》《青年文学》《清明》《天涯》《北京文学》《长城》《江南》等发表中短篇小说,在《当代》发表长篇小说《窄门》。出版短篇小说集《感觉自己在飞》《寒夜里的笑声》,长篇小说《荣辱与共》《背景》等。曾获《芙蓉》文学奖等多种项奖。
责任编辑 梁乐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