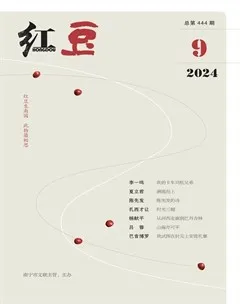陈先发的诗
2024-10-30陈先发
若缺书房
一本书教我,脱尽习气,记不得是哪一本了
一个人教我熟中求生,我清楚记得,在哪一页
夜间,看着高大昏暗的书架,忽然心生悲凉:
多少人,脸上蒙着灰,在这书架上耗尽。而我
也会在别人的书架上一身疲倦地慢慢耗尽
有的书,常去摸一摸封面,再不打开。有的虽然
翻开了,却不再推入每一扇门,去见尘埃中那个人
听到轻微鼾声,谁和我紧挨着?我们在各自的
身体中陷落更深,不再想去填平彼此的深壑
冬天来了,院子里积雪反光,将书架照亮了一点
更多的背面,蛛网暗织。在这儿幽邃纠缠的
因果关系,只能靠猜测才可解开,而我从不猜测
昨天,在天柱山的缆车索道上,猛一下就明白了:
正是这放眼可见却永不登临的茫茫万重山,我 知道
“它在”却永不浸入的无穷湖泊,构成世界的此刻
哪怕不再踏入,不能穿透,“看见”在产生力量
有时,我们要穷尽的,只是这“看见”的深度
【注】若缺:作者书房之名。
优钵罗华
在一个墙角
我看见头盖骨的积水中
长出一朵明黄色的优钵罗华
头盖骨本来洁白,日炙风吹,变成了干硬的灰白
积水本来污浊,慢慢沉淀了,连底层渣滓都这么
干净
几只蠓虫绕着花枝飞舞,留下几具遗体,浸在积
水中
头盖骨中的优钵罗华,是这一刹那宇宙间最炽烈 又最柔弱的一朵小花
五月十九日,十一位诗人在崔岗村的
灰青瓦小院中饮酒打牌,激烈争辩……
初夏的玄思,将积水化作火焰
我们藐视?是的,然后我们失去
互相嗅一嗅气味,才坐在这里
依然存在不计其数的平淡日子
其平淡,正修复我们所损毁的
也依然存在,单一信念下的漫长行走
其单一,将治愈我们所罹患的
但这一b0135edaf09a15ead62c171edf56d0b5490c537e79990d83957eaf3ccce301ef切,不来自任何一个静穆的别处
只发生在头盖骨中这一朵
柔弱的优钵罗华的里面
【注】优钵罗华:睡莲科睡莲属植物。
【注】崔岗村:崔岗村位于合肥北郊,诗人罗亮、红土主理的雅歌诗院位于村内,为本地诗人的聚会之所。
芥末须弥:寄胡亮
五十多岁了,更渴望在自己划定的禁地写作
于芥子硬壳之中,看须弥山的不可穷尽
让每天的生活越来越具体、琐碎、清晰
鸟儿在枯草丛中,也像在我随心所欲
写下的字、词、句、篇的丛林中散步……
我活在它脚印之中,不在这脚印之外
寒来暑往,鸟儿掉下羽毛又长出羽毛
窗外光线崩散,弥漫着静谧、莫名的旋律
我住在这缄默之中,不再看向这缄默之外
想说的话越来越少了,有时只剩下几个字
朝霞晚霞,一字之别
虚空碧空,裸眼可见
随身边之物起舞吧,哪里有什么顿悟渐悟
一切敞开着,无一物能将自我藏匿起来
赤膊赤脚,水阔风凉
枫叶蕉叶,触目即逝
读读看,这几个字的区别在哪里
芥末须弥,这既离且合的玄妙裂隙在哪里
我被激荡着、充满着,又分明一直是空心的
月满时
有那么几年, 你们总说我病容满面
其实是我的内心塞满了乌托邦崩塌的声音
崩塌之后的废墟,堆积在心里
堵得太满了,有时我说不出一句话来
废墟又长出仿佛会吞噬一切的荒草
跟江水、旧船坞、落日在一起
越来越接近我们的本心了
当我们成为彻底的弱者
原本晦涩的废墟之歌
许多人一下子就听懂了
我越来越倾心于废墟就这么充分赤裸着
一轮满月,从它身上升起来
云团恍惚
距离地球六十七亿公里的虚空之中
旅行者一号探测器曾接受人类的
最后一条指令:回望地球一眼,并
拍下一张照片。这一瞬后,它没入茫茫星际
我记得古老的一问一答:
“若一去不回?”
“便一去不回。”
也见过这张照片:
状如一粟,行于沧海。云团恍惚
只有造物主能布下这么艰深的静谧……
世上有人如此珍爱这份静谧:
傅雷和朱梅馥上吊自尽时,担心踢翻
凳子,惊扰了楼下人的睡眠
就在地板上铺了厚厚一层旧棉被——
遗体火化,老保姆用旧塑料袋,装走了骨灰
我时常想,是谁在密室向旅行者一号
下达了指令?将恒河沙,由无限减为一粒
又为了什么,有人竟炽烈到,以一床旧棉被
来焐热这颗孤寂的星球——
潮汐过后,一切却在继续冷却
夜间,我常到附近的公园散步
每闻笙箫隐约,就站在那儿听
一直听着……直到露水把额头打湿了
宋人有诗云:
“不知君此曲,曾断几人肠”
也许这世间本无笙箫,更无回望
埋掉我的,只是长风的一去不还
而湛然星空,又在谁的楼下?艰涩的
云团恍惚。生前,他为书房
命名“疾风迅雨楼”
【注】疾风迅雨楼:傅雷书房名号,位于上海市江苏路284弄5号其旧居内。
登燕子矶临江而作
下午四点多钟,登高俯瞰大江
今天是个细雨天
水和天
呈现统一又广漠的铅灰色
流逝一动不动
荒芜,是我唯一可以完整传承的东西
脚下山花欲燃,江上白鹭独翔
这荒芜,突然有了刻度
它以一朵花的燃烧来深化自己……
江水的流逝一动不动
坐在山间石凳的,似是另一个我
诗人暮年,会成为全然忘我的动物
他将以更激烈的方式理解历史
从荒芜中造出虚无的蝴蝶,并捕捉它
王维与李白为何老死不相往来
世界将以哪一种方式结束?
已从灰烬中捕获清凉的人
怎么会喜欢
依然骑在光线上的人——
敬亭山、《郁轮袍》,都只是精致的面具
如何咽下,这夜色中的星星点点……
两个低烧的诗人为何
非得去敲对方的门?
对话,时而连乌有乡的墙壁都听不见
更何况,隔绝带来的美妙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已没几个人能懂
肩并肩,紧挨着站在我的书架上
但也像两个盲人
一碰就碎的
泛黄的书页
令人心碎的诗的壮烈远景……
安静飞往体内的苦寒之地
我们共同的面相,只能是孤立无援
现象是有限的光源
晨起,绕着湖水跑步
湖水清冽,更深地浸入
一棵枯树,在轻霜中放射着光泽
一声鸟鸣,在听觉和视觉上留下双重的划痕
一阵风过——哪怕
是微风一缕,宇宙的秩序也随之变化
位置、角度、情绪的样本
每个瞬间都在转换
更何况一个词、一些句子、一种
空白,在内心大汗淋漓地运动……
我的心如此敏感,怎么办?
一颗过于敏感的心,又怎样做到大无畏呢?
“现象喂给我们什么,
我们就吃什么”
的生活显然垮塌了
——怎么办?
五十岁以后,渐渐懂得逝去之物
顺着崩散的光线,跑向有限的光源
风
坐火车穿过蚌(埠)宿(州)一线
向着豫东、鲁西南敞开的千里沃野
地图上一小块扇形区域
哺育生民数以亿计
高铁车窗外圆月高悬
圆月即是
他人之苦
是众人之苦的总和,所有的……
秋天的田野空下来
豆荚低伏、裂开,种子入地
黝黑的平原深处,埋着犯人
路上,新嫁娘不紧不慢
在摩托车队中……上辈子在骡队中
她并不完全懂得自己要
担负的三样(或是一样)东西:
追溯、繁衍和遗传——
高铁车窗外秋风阵阵
我一直纳闷儿,在此无限丰饶之上
那么多的生死、战乱、迁徙、旱灾
那么深的喂养、生育、哭泣
那么隐秘的誓言、诅咒、托付……
最终去了哪里,都变成了什么
为何在这大风中,在这块土地上
三百余年没有产生哪怕是
一行,可以永生的诗句
云游
寒流之后
真正的冬天的树来了
干干净净,一动不动,带着苦味
我头顶的枝上,一只灰鸟站着
我脚下的枝上,一条小鱼睡着
中间泥巴路板结,渠水清澈见底
是同一棵树
默默分身于我的两侧
都干干净净,一动不动,带着苦味
更多深渊之上,也一定曾映出另一个我
脱身云游去了……
我愿他抛名弃姓,翻山越岭,一去不回
在灰鸟和小鱼的硬壳中如果
有什么,仍是醒着的
愿他们以此刻的我、长椅上的我为参照
来确认一下,这是不是一个虚无的世界
癸卯年腊月记事
月光从窗户烂掉的部分漏进来
月光的照临,只有入口
没有出口
有幽灵的乡村是慢慢耗尽的
“一个生命,怎么可能一下子就
没有了呢?”……
我父亲的死亡曾长达十年
一点一滴地离开
到了最后,医生也不想再去拯救他
每年临近除夕,总有人在小桥头
在空了一半的菠菜地里
在井栏边,见到他
一句话也不说,但有脚印,有影子
“你住在城里,哪能理解这一切?”
荒野月亮长着暖暖的羽毛
“而你顶上,是纸剪出来的,一枚假月亮”
“一个生命,怎么可能一下子就
回得来呢?”……
我父亲的死亡曾长达十年
复活,也将是一点一滴的,需要更漫长的时光
我当然相信这死而复生的奇迹
但必须发生在恒久、淡漠的乡村风格之中
在震耳欲聋的噪声中席地而坐
没有噪声,就没有水仙……
夜里。水仙花开了,一座无声的
世界。更像是一座被消声的世界
耳蜗仍时时发热,那些训诫声
呼救声、低泣声……贮存在每一根神经里。当雨滴
滑下小区灌木和防雨棚
排队的少女只露出一双眼睛
黑瞳仁,悬停在冰冷又透彻的深水中
在水仙花的超低音中我席地而坐
听见体内凹槽中
残存着
有人夜半砸锁的砰砰声
冬夜锁孔里安放着
永不为人知的远处
“……我只想出去。”锁柄上,血迹像青黑的
几分钟后就要熟透的浆果
在持续低烧的
人的呓语之侧
在一切果实之中,而非这些果实之外,我
听见无数榨汁机抑制而接续的轰鸣声
“只此一种,足以
让当代史震耳欲聋”
雨:喑哑之物
“这场雨落在迦太基庭院里”
微小的积水被花枝掀翻
整个夏季
炎热使孩子从梦中脱身——
仿佛一个哑谜,把无知的时光隔断
仿佛我痴心的远眺
只不过抵达了风景的一半
而在另一侧
去年盛夏,当雨水滑下碧绿的葡萄架
发亮的铁轨在桥上交叉
河水慢慢聚集
发亮哦无知的时光
仿佛镜中之河,就要找到大海
爱情之夜就要筵席散尽
回忆里的面容,停在变幻中
仿佛墙上的两块砖:
焦躁的我和这场雨,偶然被砌在一起
一宿的自言自语就能使它倒塌
每年的夏季
雨漫天落着,从迦太基到西藏
从石廊、修罗花到牛头和草场
稠密的雨点一串银白
仿佛把十三省孤独的小水电站连成一片
在我和远方之间
又仿佛鸿沟不曾有过
发亮哦无知的时光
当这场雨落下,雨中之物
草木的喑哑
就要飞起,就要唱出烈火的歌吟
我8748eb4ae2022eff119ca7d544a0e3ac的灵魂将随她无声远走
脸
新月像一张脸被榛树丛吸住
布满阴影的脸苍白、坚定
这是谁?谁的脸
敛尽了我早衰的童年气息
沃尔科特,还是奥梅内斯?
斜靠在加勒比老家的蘸银柜旁
当松林中,虫声密织
众星汲取了海峡的凉气,在闪亮
同是这涛声喂养——
夜半的闷罐车“突突”冒烟:
烂醉的游子回乡
曾是他们?盲目浸透的肉体在眩晕
长笛呜咽曾是那孤驱之心趋于对应
废矿区的矮灌林片片贴地
像绵绵呜咽,沿着旧铁轨涌向海岸
这张脸无言中一秒一秒正下沉,变苦
“怀揣隐疾生活二十余年而
光和影一缕未漏——
这秘密才是那事物的根……”
她照临皆因生活愈加枝繁叶茂
她微笑只因我根基已死她全然不晓
看啊!
这落在黎明草尖上,清新雨滴中
怎样的轮回正愈来愈急?
直至遍地,都是她宁静的席卷和涌出
拉魂腔
从瓦砾中你会找到一些夹棍、烧焦的
惊堂木,或虎头铡的残片
夜间耳贴断墙,你还能听到地底的拉魂腔
布鞋在戏台轻移的飒飒声。你
会害怕吗?——
一个农民快饿死了但他仍要看戏,并
幸福地抹着眼泪,直到他真的被饿死。这些
赤脚坐在门槛上、墙头上、炊烟上的
人,看戏是
他们清算因果的大事业。“两丈黄绫捆住
的锰钢铡刀,断阴阳,斩龙袍
脸上抹着草木灰,十步内铲除奸人”,他们像真的
杀了人一样龇着牙,抖动身子笑着
戏中有个香皂般的人吸引着农妇的假鼻子
她们甚至被垄上的蝴蝶乱了心,“命苦的
祝英台——”她们恨着,想起自己的少女时代
举着锄头好一阵子惆怅
年年春尽,每个村子都会有
一个跟戏子私奔的少女
欲望的乳头像红军舰劈开世俗的风浪……
每个村子也建一座必将被大火烧毁的戏台
农民唯在戏的牛眼中,见到善恶必报的天堂
有时我想,他们大病似的沉默,仿佛
在等一剂曲终的良药
对于骑在楝树杈上的儿子们,一句台词凝固成了
他们教科书的洁白大厦
在牛尿般流畅的城市大街上他们内心的
气味从蹩脚西装中散出来。我爱这种气味:
“Eppur Si Muove!”
(它仍在转动着。伽利略写于一六三二年)
戏中断头台流出了真血的气息和
风吹桦叶般鬼魂的笑声
散了哦,都散了——
唯有寒风中看戏的、父亲们的枯骨久久不肯倒下
【作者简介】陈先发,一九六七年生于安徽桐城,一九八九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当代代表性诗人之一,现任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副主任,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主要著作有诗集《写碑之心》《九章》《陈先发诗选》,随笔集《黑池坝笔记》(系列)等二十余部。曾获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十月文学奖、草堂诗歌年度诗人大奖、英国剑桥大学银柳叶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2022春季大赛翻译大奖等国内外数十种文学奖项。二〇一五年与北岛等十名诗人一起获得中华书局等单位联合评选的“百年新诗贡献奖”。作品已被译成英、法、俄、西班牙、希腊、波兰等多国文字。
责任编辑 蓝雅萍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