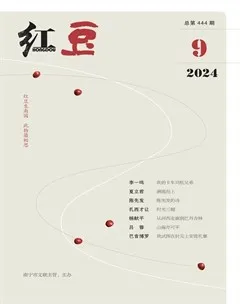溯流而上
2024-10-30夏立君
我从乡下来到城市之初,不论心里有什么狡猾的念头,表情和眼神都是呆痴的。我这个农民只有站在田间地头或自己的庭院里才会变得满足、生动起来。人以及一切生灵,都有属于自己的栖息之所。鬣狗用尿液和气味向动物界宣告自己的领地,仰起头来也看不了多远的蚂蚁一定要回到它的窝巢里去——那里有它们劳作的意义。
在二十世纪末,我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不断进行或长或短的漂泊。来自各绿洲的居民挤在同一节破旧车厢里,从这一片绿洲奔赴另一片绿洲。绿洲之间是令人生畏的沙漠戈壁。一道道沙梁如大漠探出的饥渴长舌,以吞噬一切的姿态,悄悄接近并进入它能触及的一切——草地、庄稼、道路、河流。绿洲里的居民,如果听见一夜风声,清晨起来,他们会匆匆跑到自己的田园,看看那珍贵的禾苗是不是又被沙漠吞掉了几尺。在漫长的岁月里,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们顽强地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和生存方式。汉子们的表情大都质朴平静,女人们则鲜亮生动。我根据对他们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有限认知,一直企图更多地理解他们的现实生存,理解那流动在他们喉头的幽咽或欢快的歌声。不论生活在哪里,生命、生活信息的沟通愿望,是亘古的主题。我只能用心体会生活在绿洲的人们在独特环境中的栖息。
我的所见无不陌生,但似又无不暗合于昔日的想象——我童年时代的想象。我总感到又返回了我的童年、我的乡野大地。我是在溯流而上,是在童年的曾经的精神状态中穿行。这时,我再次迷恋上了汉字的古老形体,陶醉于那植物根芽般的造型——那是汉字的童年时期。很久以前,我刚刚登上中学讲台时,常常有意将某个汉字的甲骨文或篆书的模样在黑板上描画出来,学生觉得有趣,我也觉得有趣。那时对蕴含在初始汉字中的更多信息,我还无力去感受与觉察。现在我在细密的沙地上以手指描画出一串又一串古老汉字的形体,它们在沙地上的模样比在纸上或黑板上的模样应当更接近于它们原初的模样。肯定是这样:祖先在刻写甲骨文之前,早已习惯于首先在沙上、土上或泥沙制作的陶器上画来画去,形成了各种符号及汉字的祖形。一种文字在蹒跚学步,正如一个稚子在蹒跚学步。汉字或人群在一种象形符号即文字里找到了栖息方式,形成了族类。这个民族一直在接受着这一种古老文字的滋养与限制。汉字的古老形体,必定蕴藏着打动我们、规训我们的东西,并指向我们的宿命。相传,汉字初制之时,鬼神都在哭泣。古人有将大事件、大人物加以神化再神化的习惯,何况是创造汉字这么大的事。符号一出,鬼神不能不惊恐——一种使用符号的生灵出现了。数千年后,在玩味汉字从生根发芽到枝繁叶茂的过程中,我听到了欢歌或呻吟。
在揣摩玩味古老汉字的同时,我看见了我的童年,看到了我之为我的原因。一些似乎隐没于时光深处的生活场景仿佛又呈现了一次。按照某种学说,个体的童年可以看作民族的童年乃至人类童年的缩影,就像胚胎浓缩了数百万年的人类发展史及更漫长的生物发展史一样。合欢树那美丽的叶片在黄昏将临时闭合,黎明到来时又打开,叶片是在完成大树的呼吸,又是在参与宇宙的合唱。我的体验与一枚叶片对大树的印证相似。我翻动古老汉字中的几枚叶片,寻找它们潜隐的信息,看到了独特的风景。或许因主观色彩的浓烈而影响了表达的准确性,乃至歪曲了曾经赋予它们的内容。这并不重要。我的本意是为了表达,而不是为了使表达多么准确。

几十年前,十多岁的我就要经常和众人一起参加人民公社的艰苦劳动。那时的气氛,使我对所有劳动包括田间劳作抱有巨大的敬意。在老师布置的作文中,我以那时少年特有的热情和忠诚,赞颂了我和父母、兄妹所在的那个生产队的队长。他是公社舆论所关注的人物。当村中央树杈上的高音喇叭播送表扬他的稿子时,他就满脸严肃,总是更加起劲地发号施令或更加有力地挥动手中的劳动工具。农忙时节,他总是最早起床,嘴里咬着一只铁皮哨,以尖锐的哨音将睡梦中的社员唤醒,然后带领他们到田里进行日复一日的近乎原始状态的劳作。他那副苦巴巴又勤勤恳恳的样子是很能打动大家的。田间小憩时,我拖着疲惫的双腿去远处的苇丛方便,却见一个人躺在苇丛深处鼾声如雷——他是队长。我站了片刻,首次凝神看了看他的嘴脸,在距他一段距离的地方十分愉悦地方便之后悄然离去。社员们分散在相隔很远的数块田里劳作,队长是唯一有权巡视各处监视他人的人。也就是说,他是众人头顶上的眼睛,众人却不是他头顶上的眼睛。艰苦劳作中的社员们人人都有这么一种心理:队长说不定啥时候就会出现。的确如此。我见酣睡过后的队长又精神抖擞地来到我们中间发号施令。对他避开众人偷偷在苇丛里睡觉的秘密,我始终守口如瓶,这源自对他的畏惧。不但我每天干活儿多少、活儿的轻重、得几个工分由他说了算,而且我能不能继续上学,他都有发言权。养成对权力的适应能力,不是一件难事,而是一件必须做到的事。
我在玩味“众”这个字的古老形体时,心头立即呈现了少年时代的这一幕。众人头顶上的眼睛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但一旦有了就顽固地笼罩着不肯离去。你看,甲骨文Ⅰ,“众”字头顶上是一轮红日,不是眼睛。“众”的意思就是太阳底下有很多人。遥想我们那些聪明的祖先在创制这个字时一定考虑了许多,最后确定以这一形象表达“众”这一意思。太阳底下有很多人就是“众”。这是一种多么好的命意。他们很久以来就崇拜公平普照万物的太阳。他们或许还没有多少思想,但已孕育萌生了丰富的良知和道德感。你听,他们边劳作边哼起了《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统治者的绳索勒得还不是太紧,他们还可以表达对王对监视者的蔑视。可是,监视的眼睛不由分说地降临到了他们的头顶。金文Ⅱ,一只铜铃似的眼睛悄然代替了那轮温情的红日。统治者对汉字这一符号系统有可怕的自觉,他们不肯放过任何一个令人联想到平等的字眼,不惜野蛮地予以篡改。小篆Ⅲ、繁体字Ⅳ,众人之上仍是一横“目”。简化字Ⅴ将头顶上的“目”轻轻抹去了,虽然那仅仅是为了书写时少写几笔,却无意中与现代潮流暗合。
众人应在被赋予特权的眼睛的监视管制之下,这是很自然的统治逻辑。谁在监视我?谁派他来并给他这一权力?有没有采纳过我们的意见?谁制定法律?谁执行?……众人心中可能有过类似的疑问,可是监视者在监视之前采纳众人建议这一前提流程肯定要存在的,单向监视的眼睛不可能经由协商契约途径产生。
一只眼睛代替了太阳,可是太阳仍在天上。崇拜太阳是世界性的现象,许多民族童年期都曾有过。人们崇拜太阳永恒的温暖和公正,可是监视的眼睛对众人宣布道:“我是太阳。”暴君夏桀以太阳自比,他将自己看作太阳神在大地上的对应物,为自己在人间的统治寻找天上的根据。他宣布:“日亡我乃亡矣。”饱受夏桀蹂躏的夏人喊出了这样惊心的话:“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既然连公正的太阳都会被人利用结出丑恶的果实,那就让我们一同灭亡吧。
我们常常希望自己能暂时处于无人地带,与所有目光隔绝。适当的私人生活空间是保持精神健康的保证。一个相貌姣好的女子,可能会乐于从他人的目光中获得对自身美好的印证,但有个前提:他人的目光必须是与她的目光平等的,是能为她的目光所感知的。如果你告诉她,在她看不见的角落,有许多只眼睛在监视她,她的好心情将不复存在。单向监视实施之时,就是人性扭曲之日。揣摩一下人们脸上经常呈现的表情,就知道他们时时处于趑趄不前嗫嚅又无言的状态。你为什么举手?众人举手我也举手。你为什么这样说?众人这样说我也这样说。聪明的人早已发现,无个性随大溜不露锋芒不思考,是一种最安全的生存之道。你行动的对错由头顶上的监视者说了算,监视者为了监视的容易和方便,不会培养你判断是非的能力。你害怕与监视者的意见不一致,便只剩下畏畏缩缩看他人脸色行事这一途径了。你和大家一样举手和说话的时候,既不认为人家是对的,也不认为自己是对的。没有自我,上哪儿去寻找思想与行动的出发点?

我的家乡有一条河傍村流过。村里的人家在河道里放养鹅鸭,丢失鹅鸭的事情时有发生。村民差不多一贫如洗,几只鹅鸭就是家庭的重要财产,关联着全家的生计。我的一个同龄伙伴家又丢了鹅鸭,上一年他家已丢过一回,这一回丢得更多,一只都不剩。我去找伙伴玩,见他母亲正用一点点油在锅里炸一个小面人。我称呼她为大婶子。大婶子看看我,笑一下,又用手中的筷子去翻动那个小面人,嘴里念念有词。那小面人有头有身子,似乎有腿,其他的全都省略了。但毫无疑问,那确实是个用一点点和好的面泥,草率捏成的小面人。许多事情都是如此——起到象征或符号作用就行了。草率的象征也是象征。那个小面人大约有大人手指头那么大,颜色已经变黄。一股幽微的香味弥漫开来。我马上明白大婶子在干什么——炸小面人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一件比吃更重大的事情。我早就知道村里从前就有类似的事发生,但这是第一回亲眼见到。一想到这个小面人所承担的特殊使命,我就意识到天底下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就建立了某种无法拒绝的联系。小面人被从油锅里捞出来,放到碗里,大婶子叫着我们的乳名,说:“香味还不小。来,你俩分着吃,一人不够一口。唉,要是知道三华来,俺就炸个大一点儿的。”她又朝我们笑了,是慈祥的笑。伙伴掰开小面人,要将一半给我。虽然我是个有名的馋虫,但还是不能不念及眼前这一仪式里所建立的“吃面人”与“吃人”之间的关联,感觉多少有点儿瘆人,就灵机一动,说:“你都吃了吧,两个人吃,那还不得把两个人的馋虫都勾出来呀?”大婶子仰天大笑了起来,笑过,骂开了:“这天底下什么坏蛆都有,连只鹅鸭也养不住。”骂了又骂,“这种贼心可够狠的,一只也没给俺留。”大婶子用一种奇怪的法术,惩罚那个偷走她家鹅鸭的人。将小面人放在油锅里炸,按巫术通行法则,偷走她家鹅鸭的人,就会遭受油炸般的痛苦,并得病甚至死去。有些村民对此深信不疑。我说:“大婶子,这法管不管用?”大婶子说:“管用不管用我不管,我先解解这恨。”
生活里被强行塞入了一件不想要的事件(如被偷窃),便设计另一事件(如炸面人)来进行想象中的对抗或平衡。巫术作为一种现象,之所以不易完全消失,既有人们的心理根源,亦有现实根源。一定时空下的现实,就是一定时空下的心理。反之亦然。
“炸面人”这一场景大约发生在我十二岁时。再小一些的时候,我对村妇的巫术或准巫术深信不疑,并常常担忧在我所不知的地方有人会以类似的法术加害于我。一生不曾走出那个闭塞村庄的母亲对我最初的教育,就是向我申明各种禁忌并要我严格遵守。雨后天空出现虹(山东沂蒙山区人将此字读作jiang,轻声),母亲立即告诉我不要用手去指。用手指虹会有何后果她也不知道,但她接受了世代相传的禁忌,只能以敬畏的眼神注视虹。后来读到《诗经·鄘风·蝃蝀》中的句子:“蝃蝀在东,莫之敢指。”我才知道这一禁忌仅被形诸文字的时间,就已有大约三千年了。这真是一个十分漫长的禁忌。蝃蝀即虹。从字形可推知,祖先把虹看作上天借以对芸芸众生显示某种意志的可怕大虫,一种肩负天帝使命的动物神,类似龙。前面已提及一个人的童年时代可看作民族或人类原始时代的缩影。我相信,如果童年的生存环境不发生变化,我没有被送到文明生长的摇篮——学校,我或许也会有实施某种巫术以达到某种目的或满足某种需要的行动。
巫师统治人群是完全可能的,并且那是历史曾有的现实。
甲骨文Ⅰ ,就是龟甲上或横或纵的裂纹的形象,金文Ⅱ、 篆书Ⅲ与之近似。
占卜是古代的未来学。产生占卜思想的根源在于,人已经知道了自己不但有过去和现在,还有未来,却看不见未来的样子。窥知未来便成为人们的一种强烈冲动。动物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意识,所以它们不可能有占卜的愿望。占卜是古人的宗教,他们将一切交付占卜。他们钻灼龟甲查验其上裂纹时怀有的虔诚与神秘感情,是可以想见的。那是一个遍生禁忌的时代。看,龟甲在钻灼之下爆开了裂纹,主持占卜仪式的巫师将裂纹的意义予以揭明,人们便依之而行动。处在与自然若即若离状态的人类,其在生存意识上无法与神灵分割开来。人们以为与生命绝对无关的事物是不存在的,世上所有事物都被赋予了生命力和神性,各种神灵都有特定的形态、性能、生活方式和处所,天上地下、人的周围神灵无所不在。从神灵方面讲,无论其居于何方,都可以自由地毫无阻碍地降福或作祟于人类,就是说神灵不存在接触人类的困难,但人类却有接触神灵的困难。人若想逃避或解除神灵的惩罚或祸祟,获得福佑,就必须依赖巫师通过占卜等巫术形式去实现与神灵的沟通。巫师是最有权威的人,是唯一能请神下降到人间的人,是神意的宣示者。在古史及传说里,夏禹就是一个很有权威的巫师。王权和巫师的结合曾是较早的权力表现形式。
占卜,可看作古人对信仰的外在操作。信仰无不从灵魂出发而复归于灵魂。不论采取多么简陋的形式,其内容和情感都是庄严的。人的神性和愚昧性在信仰这一行动中结合为一体。人因脱离动物的自然状态而为人,但为人的状态远不是自觉的、自由的。知道了自己有灵魂,却对这个神秘又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无法处置,只有将其交付于更有力量的事物,这个事物必然是神。占卜的目的就是期冀以非逻辑的方式,通过仪式与手段,破译神灵的密码,以分享本应属于神灵的秘密和智慧。占卜行为以及针对占卜结果而采取的相应行动,可以看作这种干预愿望的反映。人交出了灵魂却仍想对神灵有所干预,以实现功利目的。
《史记·日者列传》载:“昔……产子必先占吉凶,后乃有之。”意思是,从前,生孩子时必定要先占卜是吉是凶,然后才决定是否养育那个婴儿。那些刚刚脱离母体的婴儿,还要过一道更为凶险的门户。占卜者口中说出“吉”这个字,孩子就有了生存于世的权利;占卜者口中说出“凶”这个字,那么这个孩子就要被抛弃。脆弱的生命一来到世上就是前途未卜的。现在已没有占卜者站在母亲的门户之外决定我们的生死,但我们的明天仍然是前途未卜的。除了人之外,谁有能力有愿望去看顾人类呢?拥有无数河外星系的宇宙难道会留意渺小到无以复加的地球以及地球上的这些“蚂蚁”?或者宇宙有没有一股力量像占卜者决定婴儿生死一样,用类似掷骰子的办法决定人类的命运?在西方许多国家里,占卜行业竟会以某种“发达”的方式运作。可见,科技文明并不能必然地照亮人类灵魂的所有角落。
卜。前途未卜。可以断言,“卜”的意识在人类的未来中必定仍会有顽强的表现。

“弃”所指明的乃是一件从前常有的事实:将死婴抛弃。甲骨文Ⅰ上部是“子”(婴孩)形,围绕“子”的三个点表示婴尸上残留的胎液,中间是“其”(簸箕之类)形,下面是两只朝上的手,表示两手端“其”将死婴抛弃。金文Ⅱ、小篆Ⅲ的形态与之类似。Ⅳ是繁体楷书。老子曰:“出生入死。”意为出生即是踏上赴死之途。生存是生与死之间的一段距离,出生时即死亡的婴儿,则连这段距离也不存在,是真正的“出生入死”。
古人常采用从一个事件或故事中抽象出某种意义符号来造字,是一种形象化的抽象。人类理解和把握世界的冲动达到某种程度时,符号的诞生便成为必然。人不可能将那至大至巨或至微至细的事物一一翻动指认,便只好借助抽象与符号。哲学家卡西尔提出了“人是符号的动物”这一命题。符号使人类如虎添翼,思维从大地上起飞。古汉字就是中国古人对世界的一次巨大的符号化活动。一个民族就以这次符号化运动凝聚起来,她的全部辉煌和重负都可从这一中心和源头上予以解说。“弃”这一符号在现代常表示放弃、告别、摒弃或超越等意义。可是数千年来,“弃”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从一开始“弃”就是一件悲伤无奈之事:扔掉死婴。这表明,在这一古老文化系统里,在其源头与漫长的流动中,“弃”与生机、进取、超越无关。
我现在回到故乡时,村民那很少变化的表情很容易将我引回到童年生活里去。那些村童的额头依然像我儿时一样布满皱纹,他们以一种陌生的眼神打量着我这个他们所不熟悉的人。我想,我儿时熟悉的那些故事,不知还在不在他们中间流传。
我再次走进那片村民墓地的那一特殊角落时,便一下子掉进了童年生活的氛围里去——那里曾经是个扔弃死婴的地方,叫“舍林子”。“舍”即弃。在婴儿死亡率较高的时代,差不多村村都有这样的地方。在这个角落里,散乱的坟地中间有一个比其他坟高大得多的坟,大人总是严肃地告诫我们:“那是咱老祖的坟,谁要是敢到上面乱跑,老祖就伸手把谁拉进去。”数百年前或更早的时候,坟中的祖先第一个完成了在一片荒地“殖民”的任务,他把庄稼的种子播进泥土时,也把他和后裔的骨殖播进泥土。固定在一片土地上的人生就这样百年千年地延续着,一直到我来到世上,看见属于我的风景。从事简单艰苦劳作的父母到公社的田里去了,很放心地将我扔在街头,我便和其他村童与狗一同到处乱跑。我第一次看到婴尸时是几岁已难以确定,反正是在村小学肯收留我以前。我们在这片墓地捉迷藏。数百年间排列在一起的众多大大小小的坟丘,差不多就组成了田野上的一个迷宫。我以那座祖坟为隐蔽窥探四方时,猛然有一个重大发现:坟前有一具婴尸,一条狗正试探着想把婴尸叼走。我的出现使狗不得不退却。我大呼:“快来呀,这里有死孩子!”那一刻,我本能的反应就是盯紧那具婴尸。我不能逃跑,我若逃跑,婴尸会轻易追上我,并攀到我背上。我做过这样的梦,还做过掉进墓穴里的梦。我、我们都知道这个地方是村民扔弃婴尸的地方,亲眼看见婴尸却是头一回。我的吆喝,令伙伴们立即忘掉正在进行的游戏,怀着只有我们才能有的心情,朝婴尸靠拢。一块破布包裹着婴尸,婴尸的脚和头顶露在外面,头发粘成一片——后来才知道那是胎液的缘故。我们这些乡间孩子,每天能见到无数活物,也会见到许多尸体——鸟兽虫鱼的尸体。我们留在野地里的每个脚印中,可能都有尸体。可是这是婴儿尸体。对于我们来说,婴尸自然具有不可思议的能量,给予我们面对任何尸体都没有的震撼。我们敢于蔑视任何动物的尸体,就是不敢蔑视这具尸体。我们本能地理解了婴尸与我们的联系。我们离婴尸越来越近。终于一个大胆的伙伴用一根树枝挑开那块破布,在闻到一股怪异味道的同时,我们看见了婴尸的全貌,看清了婴尸的满脸皱纹、变形的五官及腿间的性器官。那只狗在远处等候,它盼望我们快快离开。
古人给“弃”限定的本义就是抛婴尸于野而不加掩埋。即使时光已流逝数千年,村民仍恪守这一古老的规则。他们将婴尸弃于祖先的跟前,让祖先亲眼看见狗把婴尸吃掉。村民以为,只有这样处理婴尸,那个小小的灵魂才能及时地参与新一轮生死轮回,在祖先的安排下及早投胎转世——所有新生命都装着旧灵魂。或者说在民众的观念里,生命从来就不是新的,它一落地就带着历史赋予它的所有皱纹。
看婴尸竟成了我们的一项充满恐怖、刺激又富于诱惑的活动。我们相约主动寻找看婴尸的机会。有数年时间,看婴尸是我一再重复的精神历险。迷茫幼稚的童心,在人世与地狱之间往返。时常有婴尸出现的那个地方,亦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有时我成为一具卧于荒野的婴尸,有时我被婴尸追赶。有一天,我的异常令母亲担忧:“老三这样,八成是丢了魂。”夜幕降临了,母亲与奶奶走出家门,走出胡同,走到那片墓地边,一路叫着我的乳名,呼唤道:“回家哟,回家。回家哟,回家。就沿着这路,别走岔路。”这是为我叫魂。回望这一系列童年往事时,我仿佛能回到祖先的岁月里去,似能看见祖先创制“弃”字时的情境。祖先是面对被弃的婴尸而创制这一符号的,婴尸上还淋漓着从母体带来的胎液。这几滴胎液浸染开去,我闻见了强烈的腐败气息。
古代典册里,触目皆是“弃市”这一概念。“弃市”是将有罪之人处死后暴尸于街市,是一种很残酷的刑罚。除了“弃婴尸”“弃市”,我们还弃过什么?“弃”这个字的古老形体以及以后历史所添加上去的内容,击中了我的灵魂。“弃”总是与死亡腐朽相联系,而与生机、进取无关。有一些圣者或贤者,他们的智慧总是向后看,总是忽略所有曾经的血腥,看到一个不断向未来发出召唤的古代社会。有的圣者或贤者不认为这只是他一个人的幻想。他告诫人们无须抛弃、超越、进取,只须恢复到古代就行了。他以为走向未来不是个不断扬弃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丧失的过程,未来不一定比古代更美好。我们追求的是尽量少丧失一点儿,如能将老祖宗的好东西全背在背上,就是对古代的接近,就是完美社会的实现。
没有一棵大树会将所有枯枝败叶全都背在背上。世界早已是打开的世界。“弃”这个汉字中所包含的“决绝”意义到了得到正确体现的时候了,它不应只与死亡、腐朽相联系。“弃”烙印在我们灵魂里的伤痕理应得到抚慰与治愈。

甲骨文Ⅰ“牧”字,其左是手执鞭子之形,其右是迎面而来的牛头之形。金文Ⅱ与之类似,只将左右位置颠倒了一下。这个字的本义就是放牧。
这个字足以令人类骄傲。在远古,它是最能够体现人类力量的一种行动,它表明人类对自然的一次超越和把握。将野兽驯服并予以放牧这一事实,同时也证明人类对自己兽性的征服是一件更为久远的事。兽是不能驯服兽并放牧兽的。一个人、一根软软的鞭子,就可以对成百上千的牲畜实施管控。具体的牧者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低贱的,但在他放牧的牲畜中间却是至高无上的,甚至胜过王在人群之上的感受。牲畜们对他喉咙里的每声咕噜都要留意,它们怕他,却永远依附他。它们全都认为,离开他它们自己不可能找到草地、水源。它们迅速将天生具备的能力丢失了,并完全忘掉。牧者手执鞭子梭巡在它们中间,他可以将鞭子随便抽在它们任何一个的身上。它们永远只有单个疼痛,不会有集体疼痛。它们只知觳觫躲闪,既不反抗,也不逃跑。牲畜是最完美的奴隶。它们的状态表明,它们需要这样一个在它们之中又凌驾于它们之上的王。
很多童话或民间故事与牧者有关。里面牧者的生活被认为是最接近于真实与朴素的生活,人们赋予这种生活优美的诗意。人们幻想能成为一个牧者那样的王,不接受来自地位更高的王的指令。现实的发展令人绝望。君王从牧者的生活中发现的不是童话和诗意,而是凌驾之乐、统驭之术。他羡慕那牧者在牲畜中所拥有的至尊,羡慕那卑贱者的高位,渴望复制那牧者与牲畜的关系。牲畜看上去没有什么东西非捍卫不可,它们只需要一点儿青草。这正是君王对臣民的希望。君王摇身一变,让自己成为那牧者,他放牧的是广大臣民。在此,不能不引出与牧这个字密切相关的另一个字:民。民,金文写作 。周代统治者或奴隶主,有权将奴隶的左眼刺瞎以作为奴隶身份的标记。“民”的本义就是奴隶。奴隶连保存自己眼睛的权利都没有。你看,锐器刺进去了,眼珠没有了,只剩下空洞洞的眼眶。在上古,“民”是被统治者,统治者才是“人”。统治者看中了“牧”和“民”这两个字所包含的居高临下以及镇压之意,堂而皇之地将它们放在一起,形成一个含有强烈行动趋向的词:牧民。统治者与民众的关系也就是人(牧者)与畜的关系。像真正的牧者要懂得放牧牲畜之术一样,历代君王都悉心思考“牧民”之术,他们幻想着能在牲畜一样的臣民之上建立至尊。我们的悲哀在于,君王公开宣布自己是牧者之时,我们并不知道他是企图让我们最好只有牲畜的智慧,或者直接就是牲畜。愚民政策为古代统治者所屡试不爽,他们的企图几乎总是能够实现。民众将至尊和光荣献给他,将卑贱和屈辱留给自己,默默地“吃草”,默默地献出“皮毛”和“奶血”。那牧者高举着权力的鞭子,望着他的畜群微笑。
马、牛、羊等牲畜在牧鞭的啸叫声里很快忘掉了自己的野性,忘掉了它们从前的自然状态。牧者宣布土地山河是他的,它们吃着草时就要这样想:这是在接受恩赐。它们索索地向前移动着,卷起弥漫的烟尘,形成壮观的景象。这是虚幻的,它们几乎没有什么力量,它们是一连串的零。荷马《伊利亚特》第六章中这样说:“树叶,一些被风在地上驱散的树叶——这就是人类。”君王是乐于这样看待民众的,也希望民众实际上就是这样。君王只须将手中的鞭子挥动几下,民众就会在鞭影里瑟瑟发抖。
接受着牧者的指令,民众将天赋的东西遗失于时光的深处,民众眼前再现的仅仅是牧者的辉煌,民众相信草和树叶是牧者的赐予。牧者宣布自己是救世主,民众就毫不怀疑地相信。民众仰望他时,确实感到他俯视的眼光里有无所不在的威严和温柔,就像父亲。民众哪里还有揭示自我、表达自我的愿望?将自己完全交给那至尊的牧者吧,只有他清楚哪里有民众赖以活命的“草”。牧者能让处在不幸之中的民众产生幸福的感觉,能让一无所有的民众产生无所不有的感觉。牧者反复对我们说:“民众的王是最好的,你们的生活是最好的。”牧者还说:“我会把更加美好的生活赐予你们。”牧者搅起满天的泡沫,被牧者因这泡沫而欣喜若狂。没有对生活之绝望,也没有对生活之爱。

甲骨文Ⅰ“臣”字是一只竖起来的眼睛,金文Ⅱ与之类似,只是方向相反。眼睛为何违背自然状态而竖起来?原来这个字是在描述奴隶的形象。眼睛竖着,也就是说,眼睛所在的头脸应是侧向一边低下去的。在古代,奴隶是不能抬头正面看主人的。奴隶主为了对奴隶实施最彻底的剥夺和镇压,连他们的正常视线也要予以扭曲。用扭曲的角度看世界,一切都立即改观。渺小的变高大,高大的变渺小。这正是奴隶主所期望的。
一个事实越来越鲜明。在对有限的几个汉字的追溯中,我的笔常常无法摆脱“眼睛”的纠缠。“众”人在铜铃似的眼睛的监视之下,“民”的空洞的眼睛中被刺进了一柄锐器,“臣”的视线被扭曲了。几个字的简单原始的形态无情地揭露了统治者的残忍和无耻。我们从中看见了鲜血,听见了呻吟声,比历史更为真实。统治者为何总是尽力抹杀扭曲乃至摧毁臣民的眼睛呢?我不得不去考察一下眼睛这一动物器官。
最原始的生命是没有眼睛的,现存的许多低等生命仍然如此。眼睛是光(可见光)创造的。没有太阳,没有光,就不会有大地上的所有眼睛。这是生物进化的一个简单事实。眼睛的产生是生物进化史上的飞跃,由动物的眼睛进化到人的眼睛,是又一次飞跃。眼睛是每个人的太阳。生与死的界限可以说就是有光和无光。眼睛的基本功能是观察判断周围环境,以决定自己的行动。它在各种器官中最灵活最重要。人的眼睛还能表情达意,可进行审美活动,可对一切事物进行观察。在这个意义上,眼睛实际上是心灵的显影,是透视心灵信息的唯一隧道。生活经验告诉我们,眼神与眼神的对视只能是电光石火的一瞬,即使情人之间也是如此。人无法忍受灵魂长时间的裸露。对眼睛的摧残正好表明统治者对眼睛的恐惧。统治者不敢保证自己在与他人的平等对视中获胜,所以要实现统治,必须先取消平等,让自己的眼睛君临众人之上,让众人以低垂扭曲的眼神看自己。这样统治者就能以伟大的面目出现。
君王与臣民之间拉起了一道黑幕。君王的眼睛可以长期透过黑幕俯视臣民,臣民却不能,臣民已被扭曲或摧毁了。一开始是被动的痛苦的,久而久之,眼睛、躯体、心灵取得了默契,臣民自以为选准了角度,找到了最恰当的角色。臣民努力去做的就是取消自己、抹杀自己,活着的目的就是把自己忘掉。一只戴着锁链的狗、一只眼睛被摧残的狗,会更无条件地服从主人。君王很少采纳臣民的意见。君王在目光扭曲的臣民面前,对自己的力量必然产生放大的感受:他是唯一的和最重要的。他是世上最大的支配者,是正邪、善恶、真假的仲裁者,赐福降祸者,他与神、太阳同等。他还让众人相信,除了他有这种能力,任何人都不可能有也不会有这种能力。君王很像一堆无序燃烧的火。臣民小心翼翼地看着这堆火,希望它能持续燃烧又不至于焚毁一切。但臣民的努力常常如飞蛾扑火。被王者确定的唯一优秀品质是忠,而做到忠就意味着臣民思想行动的唯一方向是那位王者。但臣民是忠的表达者而不是忠的判断者,判断者是君王。盲目使臣民狂热,臣民一再上演竭诚尽忠的故事,君王却常常以不忠的名义拒绝臣民的忠乃至将臣民处死。高处不胜寒的处境决定君王对忠的依赖。这种依赖造就了许多向极端方向发展的“忠臣”:吮痈舐痔之徒所在皆是。在这一权力关系的笼罩之下,牧者与被牧者,一个自然的自由的人都不可能存在。
当俄狄浦斯亲眼看到宿命里的悲剧一一应验后,他刺瞎了自己的双眼,以逃避本质上无法逃避的与世界的沟通。俄狄浦斯成为艺术史上的彻底悲剧典型。眼不见为净,这是一种幻想与自欺。它忽视了这一事实:眼是心的直接呈现。心眼,这个词意味深长。
脆弱的眼睛像一个微型的人,或者说是灵魂派到门口的哨兵。统治者选择它作为打击对象,无疑具有策略上的正确性。扭曲摧毁这扇窗口后,才能进而扭曲摧毁整个人。统治者的愿望总是能最堂皇地实现。
几个汉字的古老形体所透露出的历史内涵和血淋淋的事实是惊人的。我在玩味那些古老文字时,常感到它们是一些从东方泥土中生长出来的幼芽。它们一直在生长着,并成为后来诸多事物的源头。事实就是如此,一开始是流,后来便成为源。在现实中有顽强表现力的现象一定不是临时产生的,稍一思索就会发现它由来已久,它的根扎根于历史的幽深隧道里。
符号的指示作用一开始是明确简单的,后来便有了暗示和象征的力量,具有了生命力,具有了行动和表达的能力。几个关键的符号就足以给一个社会提供重要的规范。在适合这些符号生长的土壤上,它们一度变成了称霸的恐龙。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被它们笼罩压迫却浑然不觉。
新的符号在纷纷出笼,旧的符号却还在远处张望。
【作者简介】夏立君,生于山东沂南,现居日照,作家。已出版散文集《时间之箭》《时间的压力》《时间会说话》等,出版小说集《天堂里的牛栏》。散文集《时间的压力》获鲁迅文学奖,另获泰山文艺奖、钟山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责任编辑 蓝雅萍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