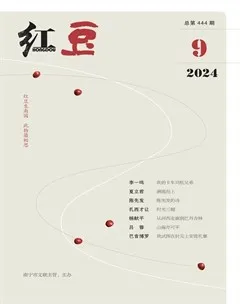我的卡车司机兄弟
2024-10-30李一鸣
一
群山连绵,苍莽无涯,一辆大卡车在崎岖的山路上攀爬。那山路如一道长长的绳索,一圈一圈缠绕着山,从山底盘向山顶,环连环,环复环,如捆粽子,愈往高处去,绳环愈缩小,最终仅余一个小环。不知不觉间,环路滑向另一座山的峰顶,而后一环环盘下来,越来越粗,越来越鲜明,逼近山脚时,尾巴一甩,没入山丛深处。
“二哥,我这开车跑运输,要说死,也死里逃生好几回了。那一次憋在山里,就差点儿!”他说。
他低下头,我第一次发现他的脖颈处密密白白的短发,如冬天霜打的草丛,分外扎眼。每每想起他,浮现在我眼前的总是一个瘦瘦小小的小伙子。可如今一算,他也五十多岁了。
“活到今天没经历过这种大险,大雪加冰冻,几十年不遇!”他抬起头,额头上现出三条叠合交叉的皱纹,深深的,仿佛积着灰尘。
我眼前飘起了大雪,大雪笼罩住逶迤的群山。转眼间便白了山头,铺满山路。雪不是飘下来的,而是砸下来的,一团一团砸到大卡车前窗上,层层堆积起来。
卡车嗯哼嗯哼喘着粗气,左右摇晃着前行。路旁无数树梢一齐向后斜过去,路上随处散落着折断的树、横七竖八的乱枝,新鲜的茬口闪着黄白色的光泽。时有滚落下来的石头,巨大的,碎块状的,横亘在路上,令人惊心。
车窗紧闭,但还是能听到风声——呼呼,嗡嗡,轰轰。他的手开始感到刺骨的冷,然后是麻,是木,是无感觉。
峡谷在向车后闪去,右方,是连绵不绝的一座又一座山头的剪影,一晃而过。有一瞬间,他的脑子里如落了雪,一片空白。
猛地一惊,像从梦中醒来。路上落下的雪很快结成了冰。卡车一侧被山壁推拥着,挤压向另一侧,那里是万丈深渊。车轮切着崖沿,其间仿佛只有韭菜叶之距。车轮打滑,歪歪扭扭地吱吱叫着,眼看就要溜下山谷。车已经完全掌控不住。心悬起来,晃晃荡荡,要从嘴里冲出来。
卡车呼叫着摇晃着避开险处。路过一个深坑,车子一沉一弹,崖下浓雾涌上来。
急刹车。车轮摩擦着地面。车滑行了一段,停下来。
深山,天黑透了。
卡车就像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白色玩具,遗落在浩莽的山壑底处。
“困在山沟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手机根本没有信号,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看着南墙上的悬窗,眼睛里一片空洞。
早就忘了饿。
“饿”上来了。卡车上仅有一袋方便面和半壶热开水。水喝光了,就从山坡上捧一捧雪塞到嘴里,靠嘴里的热量化成水。面吃光了,等“饿”再次来袭,满车厢翻过来倒过去地找,连一粒面屑也没找到,只有躺着喘气,冒着虚汗。
沉沉的暗夜,山里隐隐传来不知是什么动物的叫声。冷不丁醒来,蓦地发现一只灰白色的什么东西在啃车轮。他声嘶力竭边喊着边使劲按喇叭,才把那野兽吓退。
第二天晚上,一辆载着三十多人的客车倾覆到山谷中。地方政府救援了一夜,结果还是有二十人死亡,十三人受伤。有关部门连夜开展对滞留山里的其他车辆的救助,散落山道上的十多辆车才脱离危险。
“因为客车没准点抵达,接站的家属们急了,他们在网上求助,事情一下子成为热点。不然,我就真埋在山里了,不饿死也得冻死、吓死。我看明白了,人这一辈子,不知道要经历多少生死挑战。死和生同时‘活’在人身上,向左一点儿就是生,向右偏一步就是死。”他噘起嘴,叼上一支烟,点着火。
我张了张口,又合上。
二
一九九二年,他十九岁,初中毕业。那两年与老家相邻的油田基地成了一个大工地,塔吊林立,机器隆隆,热火朝天。他父亲带着CBKhiEhy6gEZIkO2zrwDYVAxBIz125VnJNzB8CyQ6S0=一百多人的建筑队伍承包了几个工程。他赶到工地想出点儿力。
他像根麻秆站在那里,他细细的胳膊上隐隐透出的血管像青色的小草梗一样。他父亲过后找了市交警队熟识的一个老乡,把他塞进驾校学了一个月。他拿到驾驶证后,他父亲又想办法让他进工商联办公室当了临时工,拿报纸、送文件、烧开水、打扫卫生……他腼腆老实,话又不多,眼里有活儿,大家都喜欢他。
后来工商联主席担任了政协副主席,配了专车,让他过去当司机。他除了接送领导上下班和参加公务活动外,还把领导家里的活儿都包了,换灯泡、修锁、买菜、扔垃圾、接送孩子……每天忙忙碌碌,领导表扬一句,他也只是羞涩地笑笑。如此下来,似乎有个好前程等着他,领导也有暗示。不料事情有变,上边要求彻底清理机关临时工。尽管领导费了好大劲儿,最终还是没办法留下他,希望像被一针刺破的气球一下子瘪了,他低头耷脑回了老家。
就是那年,他和我堂妹结了婚。我从外地赶回老家参加婚礼。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他父亲挥着手,大着嗓门儿招呼着进进出出的客人,安排着一应事务。而他穿一件看上去有些肥大的黑呢子大衣,立在新房门侧,浅浅笑着,两眼弯得像细月。
我返程时,他骑一辆自行车送我去镇上。坐在车后座上,我总感觉前轮要抬起来。我跳下车,抢着带他。他紧攥车把,歪扭着身子,紧闭着嘴,坚决不让。十五里的乡间小路,坎坎坷坷,晃晃悠悠,好不容易才到镇上。我挤上客车,透过后车窗,看着他瘦小的身影渐渐变成一个黑点。
后来,他就开起了大车搞运输。
那年,他家里不顺。他父亲在工地上突然病倒了。后来才知道,他父亲高血压已经好多年,一直挺着不吃药,以为顶得住,一年到头揽工程、筹资金、找工人、购原料、忙施工……工程建设的事,凭他的施工经验、管理能力能应付得了,最难的是处理各种关系。甲方对工程严格要求,那都还不算啥,让他挠头的是常常有怀着恶意的人,以各种理由三天两头儿来打扰。长年累月折腾,他父亲终于撑不住了,脑血管爆了。虽然他父亲在重症监护室治疗了一个多月,好不容易把命扯回来,但多年积攒的钱也基本花光了,还落下个偏瘫失语。
全家的顶梁柱塌了!
俗话说父病子立。一夜间,他成熟了。
说起来,这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再到后来,经济搞活了,市场红火了,乡镇企业蓬勃兴起了。镇里建了油棉厂、轴承厂、化工厂、地毯厂……各个村也跃跃欲试,几个人一吆喝,就成立了一家建筑公司,一二十家厨房设备厂在村外路旁冒出来。经济流通起来了,运输业也随之发展起来。他没钱开厂,也买不起车,就想先给企业开车拉货,练练身手。一是提高提高驾驶技术,二是熟悉熟悉运输业务,三是挣点儿钱养家糊口,也好积攒一点儿用于发展的资金。主意打定,他四处打听需要司机的厂家,联系了好几家,最后他避开了本村的,怕邻里乡亲之间有些事不好办。最终他决定给邻村的一家厨具厂送货,有厨具业务就拉厨具,没厨具业务也干点儿别的,每月工资一千五百元。开始他主要还是跑短途,从博兴去滨州、东营、淄博、潍坊、临沂、日照、青岛、烟台、威海等省内地级市和北京、石家庄等邻近城市。当天来回,尽管累,身体还撑得过去。干了一段,他感到了压力。“主要是精神上熬不了。”他感叹。
那些年,跑运输的车超载的多。别的司机说,车不超载基本不赚钱,但话说回来,超载了是要受到处罚的。有一次,他从寿光拉了一车菠菜,规规矩矩捆绑好的,没想到检查站以菠菜叶尖露在车厢外为理由,认定超载。他低着头嘟囔了几句,就被指挥着把车停到站旁的空场上,让他把菠菜全部卸下来。正是六月天,一车鲜嫩菠菜卸下来,放不了一天两夜,肯定就成了烂菜泥了。自己不卸?那人家就让民工爬上车往下卸,他不仅要交罚款,还要交卸车费、占地费、环境污染费、卫生费、清理费。那天,他一个人背靠车头坐了一夜,直到凌晨弟弟送来罚款费用他才离开。
在路上,一切都会发生。
那天我接到电话,急急忙忙乘上同事的车赶往广饶出事地点。
现场一片狼藉。
据说,他驾驶卡车由北向南正常行驶,右边被玉米地遮掩的乡间小路上突然窜出一辆三轮车改装的小货车。小货车一头扎到公路中间,驾驶员脸上的胡茬儿越来越清晰,副驾驶座上一个孩子扭过圆圆的呆萌的脸蛋看过来。他赶紧往左打方向盘,期望能从货车与路间护栏中间穿过。小货车司机似乎蒙了,向着卡车掉过车头来。卡车猛地向左前方冲去,一列隔离栏像面条一样扭转起来,失去平衡的大卡车轰然翻倒在左侧路上。他的头撞到车窗上,在倒下的一瞬间,他在朦胧中看到一辆枣红色的油罐车呼啸着从南边疾驰而来。
三天后在县医院的病床上,他醒了过来,头上缠着绷带,左胳膊打了四根钢钉,左腿吊在支架上。当时,坐在副驾驶座上的老福已经躺在太平间冰冷的尸箱里,他是当场被甩出车门的,头撞到了路牙石上。
交警判定双方各负百分之五十的责任。小货车车主是个光棍,除了这辆不值钱的改装车,只有三间土坯房。乘车的小孩全家盯住他不放,因为出事后孩子受了惊吓,连续半个月发烧说胡话。孩子的爷爷奶奶每天去光棍儿家要赔偿,光棍儿急了,撂下一句话:“你看我家里啥值钱,就拿走吧!”堂妹夫这边主家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一下子垮了。当初为省钱,卡车保险不全,如今一死一伤,死的要给一次性赔偿,伤的要出医疗费、误工费等一大堆费用。虽说定责是双方责任均担,但对方车主穷得指望不上。经过反复调解,主家给了老福家十六万元补偿金。堂妹夫这边医院不停催款,主家说实在没钱了,最终放话:“车是你开的,事故是你造成的,老福的赔偿不让你管就便宜你了,自己伤自个儿管!”可怜他几年披星戴月挣来的“毛毛”,只勉强够自己的医药费。
三
妹夫在医院住了仨月,又在家里养了仨月,也盘算了仨月。这辈子绝对不开车了!摸也不再摸一下,看也不再看一眼!他说下定了决心。刚出车祸的一两个月,他说一闭眼,就是那孩子的圆圆的呆萌的脸蛋、扭成麻花一样的护栏、枣红色的油罐车正面冲过来。一次次惊醒,心脏扑腾扑腾的,汗水湿透了被子。可他思来想去,自己没啥手艺,挣钱没啥门路,老人有病,孩子还小,责任田里的庄稼要施肥、要浇水、要打药,处处要用钱。他一想起来,胸口就像压着一个沉重的车轮,心脏像被一根绳索勒得好紧好疼……思来想去,最后一咬牙,他还是决定买辆大卡车跑运输。
买车的十几万块钱从哪里来?出院后,他一瘸一拐到亲的和不太亲的亲戚家、熟的和不太熟的朋友家,吞吞吐吐、一遍一遍、难为情地诉说,指天跺地发誓,忙不迭地表达着感谢,核心就是求大家帮忙。跑了半个月,凑了不到两万块钱。正当他急得满屋子乱转,感到绝望之际,住在县城的同学传来一个信儿,说刚下来政策,可以贷款买车啦。听到这消息,他突然发现天是蓝的,风是暖的,田野广阔,路面反射亮光,一切美得如梦一样!他骑上自行车,五十里的路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赶到县城。立马让老同桌领着,扑到县城仅有的三个汽车销售点,跑到四家银行打探消息。又连夜回到家,顾不上喝口水,马上找亲戚、托朋友,开了信誉、担保等一大堆证明。往县城来来回回七八趟,终于办好了手续。又过了三个多月,他家的大门口外、大街旁,停上了一辆闪闪发光的崭新的一拖一挂“大解放”!
“要说那时候政策来得真及时,咱胆子也真不小。敢贷款买车,全村的人都来看。”他好像回到当年,沉浸在往日的满足中。
“车这么大,货源能保证吗?”
“只要用心找,总能找得到。”
全镇每个村每个企业,他一家一户去找,运输价格被压到最低,他也干,少挣点儿,建立起固定客源最重要。货物送到指定地方,不能空车返回,他到当地的配货站寻货主、找货源。也曾经贴小广告,把自己个人和车辆信息印到三十二开的纸片上,到企业扎堆的地方散贴,结果都不理想。后来他发现了一条捷径,通过中介搭线找厂家,按比例交上中介费后,签订三方协议,达成长期合作关系。就这样他在四五个城市建立了稳定的货源联系点,虽然利润又被分去一块,但毕竟不拉空车返回了。
每次发车前,他都会帮着装车,本来主家雇了装卸工,可他不参与总放心不下。货物全部置放入车厢后,他再把货物捆牢。那情景往往是这样的:燃烧的大太阳在天上翻滚,空气像滚烫的液体浇在身上。他弯着腰,在卡车一侧,固定住绳子一头,然后憋足劲,靠着瞬间的爆发力,抡起膀子,将十几米长几十斤重的粗重的绳子高高抛上去,绳子如长蛇飞起甩到卡车另一侧。他健步跑过去,粗糙的双手像钳子一样,用绳索紧紧勒住挂钩,健硕的胳膊上鼓起椭圆形的古铜色的肌肉。他再一次将长绳从高耸的车顶掷回去,如是几番,把货物横三匝竖三匝捆牢。之后他像一只手脚并用的壮熊,臂弯里夹缠一角下坠的篷布,爬上三米多高的车顶,将硕大的篷布用力地一点儿一点儿拽上去,然后一点儿一点儿扯展开,把货物严丝合缝覆盖上,再打个对折,盖上第二层,最后用绳子把篷布捆得结结实实的。他的衣服湿透了,头发像在水里泡过,眼睛被汗水浸得眯缝着,眼白通红。“力气不值钱。”他感叹道。
卡车上路了,车轮滚滚。迎着夕阳,没入群山;向着朝霞,穿越田野。河流在车旁流淌,无数人影在大地上起起落落……到了休息区,他方便后,顺带在公共洗手池边,把头埋在水管下的水池里冲洗头发。用毛巾将上身擦洗几遍,然后把衣服、毛巾洗了,挂在半开的车玻璃窗上晾晒着。他在树荫里吞一包泡面,擦擦嘴,登上驾驶室,继续前行。困极了的时候,他将车停在服务区,躺在车后座上,顿时响起撼山的呼噜……
冰雪事件后,他一个人再出门,全家的心都悬着。堂妹下狠心把刚刚断奶一个月的孩子交给婆婆,和丈夫一起踏上运输的长路。堂妹帮不上多少忙,但换轮胎时有个人递扳子,加油时一个人守车另一个人能跳下车付个油钱。饿了他们就在服务区用随身带来的柴油炉子炒个菜做个饭。那些年,饮食没有规律,长期睡眠不足,他得了高血压病、胃病、颈椎病,得了大车司机基本都有的职业病……一塑料袋子西药、两袋子中药伴随着他们。饭后,她用带着的砂锅熬煮好中药,滤出一小碗药汤让他喝下。车子发动前,他们再一次用双手拽拽绳子是不是松了,用脚踩踩车胎是不是饱满,仔细查看轮子纹路里有没有石子、钉子,摸摸轮毂温度是不是过热。数九寒天,他们戴着厚厚的手套,顶着刺骨的寒风,拿着撬棍,敲打篷布上的冰凌,把绳索再次紧固。遇到冰雪路,他们小心翼翼地把防滑链扣牢、装紧。疫情期间下不了高速,漫长的时间里,只有她陪着丈夫聊天。
疫情过去后,他们的心彻底放开了,第一次出发的路程贯通南北西东。从博兴带货出发,一路向东北到了黑河市,卸货后再向南五百七十多公里到达哈尔滨,装上新货,向西奔行两千多公里跑到银川,又带货跑三十多个小时到南宁,之后又到了深圳、宁波、临沂。车窗外的风景次第变幻:星空下静谧的平原,冰雪覆盖的原野,烈日下无垠的草原,暮色里荒寂的沙漠,月光照射下的崇山峻岭,灯火阑珊的小镇,地平线上与太阳一起升起的树林般的高楼……
这几年,网络发达了,他们加入了几个卡车司机微信群,也知道全中国像他们这样的卡车司机有一千七百多万人。在群里,大家因共同的职业、经历,在彼此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大家诉诉苦,叫叫累,喊喊痛,发发牢骚,也骂娘,碰到好事,如儿子升学了,高兴地吼一嗓子;婆娘做了一顿好吃的,也拍个视频发上去;市场竞争太激烈了,货运成本太高了,主家压价太低了……谈到这些难事,大家七嘴八舌,出主意的、劝慰的、跟着叹气的……相互获得一点儿抚慰,心暂时也不那么揪着了。群里有才的人也不少,有的写诗,每天写一首;有的唱歌、唱剧,京剧、吕剧、评剧、川剧、黄梅戏、河北落子、东北二人转、信天游……听,蒙阴的一个小伙儿在唱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沙哑的声音分外苍凉: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
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
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
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
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
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
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
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
因为我不在乎 别人怎么说
我从来没有忘记我
对自己的承诺
对爱的执着
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跟着希望在动
…………
朋友圈里泉涌般闪出点赞和流泪的表情。天南海北的兄弟姐妹们,在网上找到别于跑车的生活。
今年春节,堂妹一家过了一个不一样的年。大年二十九他们才灰头土脸回到老家,大年三十早晨还没起床,银行的业务员就来敲门了:“我来了好多趟了,总是扑空,这回算是碰上了。你家去年车贷本息还没缴,你们可别耍赖,不然我在你家过年了!”女业务员进门就盘腿坐到床头上,看上去不急不慌,大有长期驻扎下来的势头。她语速不疾不徐,声音不高不低,但话里的意思也让堂妹夫坐立不安。“您把心放到肚子里。我一定还。您知道这两年有的小企业不够景气,俺跑车的也要不来运输费。我再去求求他们,您也宽限宽限。争取正月十五前还上。”好不容易刚刚送走银行要账的,老福一家老的少的七八口人哭着喊着冲进了门。“老福跟你车,走的时候好好的,突然就没了。年纪轻轻的才三十二岁啊!我那苦命的儿啊!”老福娘鼻涕一把泪一把,哭着说着,突然瘫坐下去。老福媳妇则滚到了天井里,说:“老福,你这狠心的,丢下俺娘儿俩,咋活啊!”正哭喊着,突然没了声响。“哎呀,这是咋了?翻白眼啦!”于是有跪在身旁按人中的,有急得团团转的,有跑出门找大夫的,一个孩子口里不断叫着“娘”,鼻涕、眼泪挂在脸上、嘴唇上、下巴上。堂妹夫妇也跪在人群里,眼睛通红,胸前衣服上濡湿了一片,裤子上沾着泥土。“他爹,这是咋了?”堂妹婆婆疯了一样跑到天井里,冲着妹夫大声地喊:“快看看你爹咋回事,只有出气,没有进气,脸都紫了!”堂妹和堂妹夫一听,一下子爬起来,三步并作两步冲进西屋,大声喊道:“爹,爹,你醒醒,你醒醒啊!”咣当一声,什么东西掉到了地上。也不知什么时候,天井里安静了下来。
四
大年初六,他们又一次起程了,和这块土地上的一千多万兄弟一起。“天那么大,地那么广,人那么小,就像卡车一批批产出,一辆辆报废,一茬茬上路,咱老百姓还是要一车车地跑,一天天去过生活。”
车轮旋转、旋转,一直转到大陆的边缘。地球也在旋转着,旋转进星云密布的浩瀚的银河……
【作者简介】李一鸣,山东博兴人,教授、作家、文学评论家,现居北京。
责任编辑 蓝雅萍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