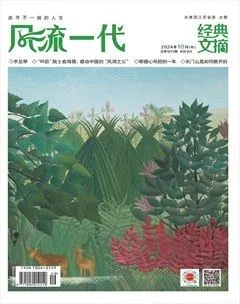弗里曼·戴森:科学家中的“青蛙”
2024-10-30浅草
在著名的物理学家中,弗里曼·戴森经常被描述为一个不安分的角色。他最早对量子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不像其他人一辈子株守一隅,而是像青蛙一样,不停地从一个领域跳到另一个领域(有时跨度还相当大),而且在每个领域里都特立独行,有所建树。这种全才型的科学家在当今是越来越罕见了。
做一名物理学家
戴森于1923年出生在英国。他自小就是个数学神童。戴森后来曾开玩笑说,他在摇篮时就理解了无穷级数的概念。他还很早就对科学产生了兴趣,贪婪地阅读科普(科幻)书籍。8岁那年,他模仿凡尔纳,写了一本有关月球探险的科幻小说。
在当时的英国,在小学和中学阶段,科学这门课程都不受重视。为了满足旺盛的求知欲,小戴森就和几个同学创建了一个科学社团。社团成员定期阅读有关的科学书籍,并相互解释各种科学概念。所以,中学毕业时,戴森的科学素养已相当出色。
完成高中学业后,戴森进了剑桥大学学数学。他只用了两年时间就毕业了。
当时正值二战。离开剑桥大学后,戴森到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工作。他的任务是负责用数学来计划更有效的轰炸,譬如计算轰炸机以何种密集队形能把相互碰撞的概率降到最低。
戴森长期以来一直在数学和物理学之间徘徊,还在轰炸机司令部的时候,他就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挑战,即证明数论的一个猜想:如果成功,就去成为一名数学家;如果失败,将从事物理学研究。结果是失败。于是1946年戴森回到剑桥大学,继续攻读物理。
物理学中崭露头角
由于当时剑桥大学没有合适的物理学导师,1947年,戴森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在理论物理学家汉斯·贝特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
就在第二年暑假,戴森在美国旅行时,解决了理论物理学中的一个紧迫问题。
当时,康奈尔大学的年轻教授费曼发明了一种新方法来描述电子和光子的行为,即著名的费曼图。但是与此同时,另外两位物理学家朱利安·施温格和朝永振一郎,也各自找到一种非常不同的方法。这两种方法都能满足量子力学和狭义相对论的要求,但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呢?这个问题一时让高手云集的粒子物理学领域陷入僵局。
戴森此前也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在那次旅行中,有一天坐在巴士上,他头脑里灵光一闪:这两种方法在数学上是等价的!他很快将这个想法写成了论文。戴森的证明,促成了现代物理学的最伟大成就之一——量子电动力学(描述电磁现象的量子理论)的诞生。费曼、施温格和朝永振一郎凭此在1965年获得了诺贝尔奖。有人说,戴森也完全有资格获奖,只因为该奖项一次最多只能颁给三个人,他才被刷了下来。
但戴森本人并不在意。他说,如果一个人想赢得诺贝尔奖,应该长期集中注意力,深耕一个领域,并坚持10年以上,但那不是他的风格。
在美国待了两年后,戴森连博士学位也懒得拿,就回到了英国。此后,他一辈子都没获得过正式的博士学位,但全世界名牌大学的荣誉博士帽却争先恐后地戴到他头上,所以人们还是叫他戴森博士。
不久,戴森又回到了美国,先是被康奈尔大学聘为教授,但他发现自己不适合教学。1953年,他被聘为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终身教授。最初,他还继续物理学研究,但几年后,他觉得是时候跳到另一个池子了。
戴森的太空梦
20世纪50年代,戴森加入了新成立的美国通用原子能公司,这是一家开发民用核技术的公司。他在保留研究所教职的同时,利用暑假为该公司工作。
戴森的第一个贡献是帮助设计了一个小型安全的裂变反应堆,用于科学研究和核医学。该反应堆可以快速关闭,无需人力或机械干预。这种反应堆在世界各地相继建造了66座,其中一些至今还在运行。
然而,戴森在通用原子能公司最感兴趣的是猎户座项目,其目的是建造一艘核动力载人宇宙飞船。最初的计划是建造一艘4000吨的宇宙飞船,由2600枚核弹驱动。当时的想法是,在飞船下方引爆一枚核弹,利用核弹爆炸产生的巨大冲击波将其送上天。在飞船回落之前,从飞船上投下另一枚核弹并引爆,如此反复。虽然这样的计划在今天听来异想天开,但当时他们却十分认真地对待。
戴森和他的同事必须回答的主要问题是:这样的宇宙飞船能否在不把自己炸成碎片的情况下飞行?如果飞船没问题,那么如何保护船员免受核辐射的冲击?
戴森和他的同事设计了一个理论上能解决上述两个问题的飞船模型。通用原子能公司甚至建造了一个直径为1米的原型,并在1959年使用常规爆炸进行了测试。他们打算在1970年前把飞船送到土星。但猎户座项目在1965年就被终止了,一个主要原因是1963年几个核大国通过了禁止在外层空间核试验条约,这使得引爆核弹测试该飞船模型变得不可能。
但戴森的太空梦并没有终止。今天,我们大多数人之所以知道戴森这个名字,是因为他提出的另一个著名设想“戴森球”的缘故。
戴森是在1960年提出这个想法的。当时他在思考一个技术先进的文明的演变。他估计,这样一个文明随着发展,其能源消耗会越来越大,直到超过其星球所接受的恒星辐射。戴森受他读过的一个科幻故事的启发,提出这样的文明可以用一个围绕其母恒星的巨型太空设施来收集能源,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求。他推测,未来的地球人也将走到这一步,届时可以通过拆解木星并重新组装其碎片来实现这一目标。
戴森球的想法很受寻找地外智慧生命的天文学家的重视。因为戴森球的存在将会使我们所观察的恒星光谱往红外端移动,而这是可以从地球上很容易观察到的。
科学上的反派角色
现在,戴森这只“青蛙”又跳到了生命起源问题的“池子”里。
我们知道,生命的最重要的两个特征,一个是能新陈代谢,另一个是能自我复制。那么,最早的生命先具备哪个特征呢?传统上,大家都认为自我复制优先。戴森是提出“代谢第一”假说的第一人。这个假说不需要生命分子一开始就能准确地自我复制,而是着眼于解释对生命至关重要的化学反应网络如何出现,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何增加其复杂性。
很有讽刺意味的是,像戴森这样一个以其工作的准确、严谨而闻名的科学家,却并不认为准确性是自然界所固有的。
这不是偶然的。事实上,戴森称自己为科学上的反派角色,并警告人们不要把数学上的抽象概念与终极真理混为一谈。他对任何数学模型都抱着不信任的态度。早年,他曾对核战争可能导致核冬天的预测提出质疑。后来,他又对气候模型表示怀疑,这导致他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与科学界的共识相左。他还对物理学中“万有理论”的必要性持怀疑态度,认为自然是复杂的。
戴森一生最关注的是多样性的重要性。他把保护和促进多样性视为一项原则。在他自己的人际关系中,戴森总是非常乐意与持不同意见的人做朋友。事实上,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流行着这样一个“戴森定理”:如果你想让戴森同意你的观点,就不妨让不同意你观点的人在他面前说你的“坏话”。
戴森的思想一直燃烧到最后。当他88岁时,还撰写了一篇关于囚徒困境的论文,这是一个对理解人类行为和进化的本质非常重要的数学概念。
弗里曼·戴森于2020年2月28日去世,享年96岁。
(刘谊人摘自《大科技》202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