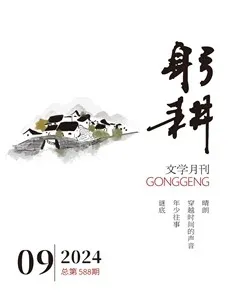人性与野性的生命邂逅
2024-10-30杜森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不断扩张,环境恶化、物种灭绝等生态危机日益凸显,“生态文明”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和省思的重点。在文学创作领域,“生态文学”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学思潮:“生态文学认为生态危机实际上是人性危机的反映,生态失衡本质上是人性失衡的表现,因此,生态文学致力于先拯救人的失衡的灵魂,进而拯救衰败的自然。”“生态文学”旨在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统御,把生态和自然重新置于世界的中心位置,呼吁人们重视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将人文关怀推广到自然生态之中。在生态文学的创作领域,“生态散文”的创作又是极为突出的重要部分。有学者对生态散文有如下总结:“这一门类的散文不仅包括生态环境保护题材的作品,还包括站在深广的人文关怀的立场上,以对生命价值形态的审美观照为本,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和谐共生的一大批作品。”生态散文作家以人文关怀观照自然生命,并从自然中寻求人性的返璞归真,以期达到天人亲和的艺术境界。河南南阳的祖克慰就是这样一位伫立在原野之中笔耕自然生态的散文作家,他用朴实自然的笔触描画了山间野外的动物生灵,构建起一个属于野性生灵的艺术世界。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动物系列散文试图从野性之中呼唤人性的回归,在他笔下,无论是豹子、老虎这种猛兽,还是家犬、麻雀这种小动物,都带着一种“人情味”,蕴含着一股“书卷气”。在笔者看来,他的动物系列散文正是人性与野性的一次生命邂逅。
一、《动物映像》的人性内蕴
生态自觉只是完成了生态散文写作的第一步。第二步则是作家的田野经历。若缺少田野经历,最动人的感性细节就无法确立。作为一个出身于乡村原野之中的作家,祖克慰的创作既体现着强烈生态自觉意识的引导,也有着丰富的田野经历作为支撑,乡村生活的痕印常常自然地显现于他的创作之中,人与动物的故事是他动物系列散文的重头戏。野猪、豹子、孤狼、狐狸等多种多样的动物通过他的文字跃然纸上,在字里行间与读者相遇。他的散文集《动物映像》就记叙了他亲身经历的一则则与动物邂逅的故事。这些故事虽然题材和内容各不相同,却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基调:敬畏生命的写作伦理。
面对飞禽走兽,祖克慰始终心怀敬畏,他笔下的动物们是一群身居深山野林之中的精灵:原野里游荡的一匹孤狼、山谷中穿梭的几只红狐、枪管前平静的怀胎母兔……这些顽强生存的动物身上折射出生命的灵光,令人肃然起敬。他在《敬畏老虎》这篇散文中直言道:“我们要学会敬畏,敬畏大自然,敬畏生命!”这句话正是贯穿他的动物系列散文创作的要义。祖克慰之所以对动物心怀敬畏,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他在动物身上看到了人性的内蕴。有学者指出,与古代书写动物的散文比,中国现当代散文的生态意识明显增强,具体表现在:“涉猎的动物更加多样化;人与动物之间多了些和谐共处、平等交流、彼此包容、相互学习;人性因素明显增加。换言之,在生态意识下的动物逐渐取得与人同等甚至高出人的地位。”祖克慰的生态散文便蕴含着这样的生态意识,表现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颠覆。他所书写的诸多动物是拥有着自主意识、怀揣着真挚感情的类人形象。他在一些作品中常常把人和动物作比较,得出的结论则往往是人不如动物:人不如动物有情,不如动物重义,我们人类应当摒弃高高在上的姿态,向动物学习。如在《狗殇》这篇散文中,作者借写狗的忠诚反思到人性的弱点:“可我们有些时候,还不如一条狗,狗通人性,狗知道感恩。”在进化程度远不如我们人类的飞禽走兽身上,却可以见得有些人们业已忘却的可贵品质,实在可悲可叹,或许,这也正是祖克慰倾情于动物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动物映像》这部散文集中,很多动物都带着一种身处末路之中的悲剧色彩,而把它们逼上绝路的往往是手持武器的人类。以《怀念最后的野猪》为例:这篇文章记叙了一次乡人围猎野猪的故事,祖克慰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细致描写了野猪在无路可逃之时的绝望。
被围猎的野猪在绝路之中展现出了强烈的求生欲,从它的愤怒的长吼与圆睁的眼睛中,作者看到了一条生命为了活下去选择顽强抗争的求生欲,也看到了动物在人类手中的刀枪棍棒之下的无奈与悲怆。走上末路的野猪最终成为了人们口中难得一遇的珍馐,野猪之死的悲剧最终变成了人们“幸福的喜悦”。据文章所述,这则人类与野猪的故事发生在1983年,乡人们在那时围猎野猪,也是为了给贫困的生活增添一点儿馋人的肉香。人们为了口腹之欲捕杀野猪的这一事实虽然在今天看来是残忍无道的,但在当时却也是为了生活而做出的无可厚非的行为。猎人与猎物双方都在为了生存而挣扎。这样看来,这头“最后的野猪”的末路也就被赋予了一种时代与命运悲剧的色彩。但祖克慰生态主义的反思立场是坚定的,他在《最后的豹子》《与一只野兔对视》《邂逅一只红狐》等作品中都表达了对受到人类迫害的野生动物们的深切同情,呼吁人们尊重生命,保护动物。
在祖克慰的动物系列散文中,动物并不是唯一的主角,各式各样的人物也颇有意味。他笔下的一些人物与动物形成了一种映照,由此产生了人与动物之间“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微妙关系。如《孤狼》一文中的狼与柴金锁,一人一兽之间可谓同病相怜。狼本是群居动物,这匹孤狼是被群体抛弃的被遗忘者,成了山林里最后的一匹狼,独自游荡,夜夜哀嚎。柴金锁则是一个长期生活在村庄之外,无人相陪,只有狼狗鸡鸭为伴的人,他就像被村庄抛弃了一样,离群索居,孤独无依。柴金锁这一人物形象正如山林里游荡的孤狼,人与狼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映照,二者之间发生的故事也因此更加耐人寻味。又如在《黄鹂:自在娇莺恰恰啼》中作者对儿时玩伴蕾的追忆:“我突然觉得,一袭黄色衣裙的蕾,是那么的娇小可爱,笑靥如花的脸,清纯明净的大眼睛,黄莺的声音,多么像一只美丽的黄鹂鸟。也许,蕾的前世,就是一只美丽的黄鹂。”祖克慰的其他散文中也多次提到了蕾这一人物形象:蕾是作者少年的玩伴、后来的恋人和未满的遗憾,蕾也是作者心目中善与美的化身。动物们承载了作者与蕾一同经历的闪烁回忆,也正因为有蕾这一人物形象的参与,祖克慰笔下的蛇、黄鹂、大苇莺等动物被赋予了一种感性的美,流露着作者对过往恋人和少年记忆的追怀。美好的人性与动物的灵性是相同的,都是生命之美、自然之美,正是在对这种美的欣赏与追求中,人与自然得以达成和谐统一。
无论是于动物身上显现的人性光芒,还是动物与人类之间的相互映照,都说明祖克慰在创作中极大地淡化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建构了一个内蕴着人性的动物世界,并借由动物世界观照人类世界,进而阐述自己对人类社会的一些思考。他的这类作品皆是取材于生活的真实体验,却又不乏浪漫的想象、大胆的揣测与传奇性的叙说,可谓打破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分隔。他的散文实写的是动物的生活习性与万千姿态,虚写的则是作者追求天人合一的美好遐想,既是借实写虚,亦是以虚衬实,给人以平凡感动的同时引起读者深切地思考。
二、野性生灵的文化观照
作为一个长于描写动物的散文作家,祖克慰对动物的观察不可谓不细致全面。他的散文除了呈现动物身上的“人情味”之外,还解读了许多动物特有的“书卷气”,他把笔触伸向历史和文化之中,纵向深入挖掘了动物们的文化内蕴。如在《敬畏老虎》一文中,开篇就写“虎从《诗经》里走来”,把虎这一动物从一个生物学名词引入了文学与历史的范畴。作者在文中说老虎是“神圣”的,我们的祖先曾把老虎视为王者之兽,因此敬畏老虎,也是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祖先、敬畏我们人类本身。“虎从《诗经》中走来,又向《诗经》中走去。”这句话正是对人类的深刻警示:我们的祖先懂得敬畏自然,因而千年间与动物在天地之间和谐融洽地共生共存,而现代人渐渐迷失了自我,忘却了敬畏之心,因此越来越多的动物离我们远去,回到了历史之中,空留无尽的遗憾。祖克慰从文化映照的角度去解读动物,也体现了这种敬畏动物、敬畏自然的写作立场。
我国古代的诗词书画对动物多有涉及,是动物文化的重要体现。祖克慰在他的散文集《观鸟笔记》和《画中读鸟》中的作品就对我国古代的一些花鸟画作和诗词多有提及。著名作家二月河评价他的《观鸟笔记》是:“一部人与鸟,人与自然的文学精品,一部重新审视人与鸟的关系的特色之作。”这部散文集用科普性的语言介绍了麻雀、大苇莺、伯劳、云雀、黄鹂等性情各异的诸多鸟类,同时还从文化渊源的层面上追寻探索文化艺术中的鸟。写到麻雀时,就介绍了北宋画家崔白的《寒雀图》和历代诗词中出现的鸟雀。写到绣眼则是从北宋皇帝赵佶的《梅花绣眼图》入文,从画中的绣眼写到自然中的绣眼。写到伯劳,就对伯劳鸟名字的演变作了一番文化解释;谈到画眉,则讲到画眉与西施的渊源……祖克慰通过在作品中恰到好处地引用诗词歌赋、讲述文人轶事、介绍花鸟画作、考据文化渊源等方式,把自然中鸟的形象延伸到了历史文化之中,拉近了鸟与人的距离,增进了人对鸟的文化认同感。
《观鸟笔记》中的作品虽然以散文为体,但在表达方式上却是超越了散文的限制,既全面介绍了各种鸟类,又兼以对动物的历史文化意蕴的透视和挖掘,同时讲述了人与鸟耐人寻味的故事。他的另一部写鸟的散文集《画中读鸟》则更为鲜明地展现了画中之鸟和自然之鸟的对照。通过唐寅的《枯木寒鸦图》、朱耷的《双鹰图》、吕纪的《榴花双莺图》等历代画鸟名作,祖克慰看到了作画者与鸟类的生命邂逅,并由人与动物的关系切入展开了丰富的想象。《画中读鸟》题名中“读”一字颇具匠心:这里的“读”是品读的读,读的并非文字,而是一种欣赏自然之美,与动物为友的意趣。朱耷、唐寅、吕纪等书画家有这样的意趣,今人如祖克慰者也有这样的意趣,于是,历史的壁垒被文字打破,一声鸟鸣,跨越百年之隔,在审美中得以长存。在祖克慰的笔下,自然世界中的鸟与文化艺术中的鸟相映成趣,前者被赋予了艺术的审美价值,后者则获得了盎然的生气,古典美与自然美交相辉映,取得了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
祖克慰把文化考释与书画品读融入散文创作的努力,或许正是在传递这样一种观念:动物与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动物与人休戚与共千百年,在人类的历史文化中留下了无数动物的痕印,通过这些痕印,人类的命运与动物早已产生了紧密的联系。祖克慰对文化历史的回望,丰富了散文表现内容,增强了作品艺术张力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当今社会文化心态的反思。在《古松迎风立 孤鹤向青天》这篇文章中,他想到“八大山人”观赏着白鹤飞舞,饮酒吟诗作画的情景,又想到现如今因为自然资源的萎缩和人类的过度捕杀,白鹤已难得一见,不禁感叹:“现在的文人,似乎没有那么多的闲情雅趣,游山玩水,饮酒吟诗,赏鸟作画,怕只是梦想了。”可见,祖克慰的生态意识不仅体现为保护环境、珍爱动物,也体现为对欣赏动物之美的“闲情雅趣”,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散文表现出生态主义与文化寻根的巧妙结合。
古人从飞禽走兽身上发现了诗情画意,用文字和笔触记录下动物的美,而反观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利欲熏心的人们只看到动物的价值而忽视了动物的美,过度捕杀和无节制地开发导致了动物种群的加速灭亡,过去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美好不再重来,这正是祖克慰所叹惋的悲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虽然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却也将人们拉出了田园牧歌的精神家园。祖克慰在创作中对动物文化的回望,也是呼唤人性回归的努力。
三、天人亲和的想象空间
有学者指出,中国新时期以来的生态散文所建立的是一个天人亲和,充满了大地情怀的意义世界,这个世界所给出的是散文家对天地造化的无限敬畏和由衷赞叹;还有对受欲望“促逼”而被“摆置”在工业化链条上的现代人的深刻反思与批判。这一特征在祖克慰的动物系列散文中也有明显的体现,他的散文中时常描摹过去记忆中的乡村图景,试看《麻雀:短翎瘦影亦横空》中的这段文字:
我一直认为,一个村庄,是由人、麻雀、树、炊烟组成的。人是一个村庄的主宰,没有人就没有村庄;麻雀是村庄的歌手,没有麻雀的村庄,是沉寂的,少了一些灵动;树是村庄的风景,村庄里没有树,村庄就显得枯萎,没有生机;炊烟是村庄脸上的胭脂,炊烟把村庄打扮的虚幻、缥缈、隽秀、美丽。
这段话描摹了祖克慰心中的村庄,他笔下的“村庄”,正是天人亲和的想象空间的具现化。在这个想象空间中,人虽然居于主宰地位,但并非是唯一的独角,麻雀给村庄以灵动,树木给村庄以生机,炊烟装点了整个村庄,如果村庄缺少了鸟和树,就会变得沉寂枯萎、死气沉沉。这样的想象空间从小处着眼是一处村庄,从大处放眼则是整个世界——世界便是由人与动植物共同构成的生态空间。村庄若缺失了鸟和树便不成其为村庄,世界如果失去了生物多样性也就不成其为世界。祖克慰的动物系列散文正是立足于人与自然和谐与共的生态理想上展开书写的,从狼、野猪、狐狸、豹子,写到麻雀、黄鹂、斑鸠、鸽子,形形色色的动物在祖克慰的笔下活灵活现,众多的动物、人物与山间流水、乡间炊烟、日月风云等景观一同建构了一个令人心向往之的自然空间。
作家的痛苦来自人要与天地相沟通的主观愿望,这种愿望越强烈,痛苦就愈甚。这大概是所有生态意识觉醒了的诗人作家所具有的一种精神体验。祖克慰的散文中常常透着一种淡淡的苍凉和悲哀,这种苍凉和悲哀来源于现代社会对于原野乡村的冲击与解构。随着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发展,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人们渐渐淡忘了从前那一方绿水青山的精神故土,祖克慰在创作中也对此流露出无限的惋惜之情:“我心中的那个由人、树、鸟和炊烟构建的村庄,在几十年的飞速发展中,灰飞烟灭。”(《麻雀:短翎瘦影亦横空》)“狐狸做过巢穴的无名坟冢,已被夷为平地,那些生长了多少年的迎春花,随着坟冢的消失,成了某户人家灶房里的柴禾,化作一股青烟,飘散在无边的天空。”(《灵狐》)“在我家乡的山坡上,我长时间地寻找我熟悉的鸟,但是,令我失望的是,很多鸟已从家乡消失。其实,当我走近家乡的那一刻,看着长满荒草的梯田,看着光秃秃的山坡,我就知道,我将带着希望来,伴着失望归。”(《伯劳:雀中雄鹰性凶猛》)正因为祖克慰成长于生机盎然的乡村原野,才会对无迹可寻的鸟语花香怀有如此深沉的怀念与追忆,他的遗憾与忧愁在作品中化成了月夜的声声狼嚎、林间的阵阵鸟鸣,给人的灵魂以强烈的震撼。
祖克慰的散文在语言上并不十分精致,他的散文常常是信笔写就,鲜见作家才情的肆意铺陈,唯有伫立于自然天地之间的沉思与慨叹。但他的语言不同于一般的大白话,又是耐人寻味的,于直白浅露的白描中得见深沉蕴藉的思考,是祖克慰散文语言的一大艺术特色。他的散文一方面在语言上不重修饰,直白浅露,就像与人拉家常一样随意叙说,把诗意更多的留给读者;另一方面,祖克慰在语言中寄寓了深沉的思考,虽然是写动物,却不仅仅是写动物。如前文所述,祖克慰以动物为视角,看到了人性、文化、时代乃至整个世界。祖克慰把自己对生态和文化的思考融入作品之中,但多数是点到为止,不以长篇累牍地过度抒情破坏散文的自然与真实。然而文风的随意放达既是祖克慰散文的个人特色,也在艺术表现上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小小的遗憾,由于行文完全依照心灵的意识流书写,一些文章的表现内容过多,就导致了表意松散,不够集中深入的瑕疵。但这些问题毕竟是少数文章的问题,总体来看,祖克慰的动物系列散文不失为当代河南作家生态散文的扛鼎之作。
祖克慰的动物系列散文在生态文学创作立场的基础上融入了文化寻根的思考,深化了生态散文的表现主题,增强了生态散文的艺术张力。透过作品,我们可以读出的是祖克慰深沉的人文思考与生态忧虑,人性与野性在他的笔下完成了一次生命的邂逅。祖克慰的散文创作体现着一种“生态人文精神”,他以个人深沉的生态人文关怀,在乡村原野之中寄情动物世界,不懈呼唤人道主义精神回归自然、回归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