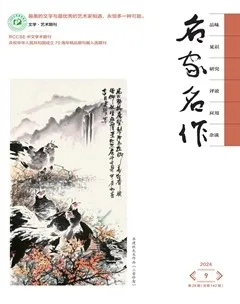“自我画像”——当代中国女画家作品中的自我意识
2024-10-21李柔佳
[摘 要] 在漫长的美术发展历程中,“自画像”几乎是所有画家都会尝试表现的题材,这也成为学界探索画家精神世界的重要依据。而随着绘画艺术的发展,女画家也逐步挣脱传统思想对女性的束缚,尝试在绘画中更多地彰显女性独特的魅力。“自我画像”与“自画像”有所区别,与单纯描绘自我的外在形象不同,画家尝试在作品中借由意象来传达内在自我和当下女性共同的生存现状。以当代中国女画家绘画作品为研究对象,梳理我国女画家绘画中“自我画像”的发展历程,并通过剖析当代中国女画家的代表性作品,揭示她们如何通过自我画像的方式,展现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自我意识。作品中不仅描绘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多样化的“角色”,还彰显出艺术家作为女性的自豪感、幸福感与社会责任感。通过分析绘画作品的创作题材与绘画语言,讨论当代中国女画家通过自我画像所展现出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以期为女性绘画中的自我艺术传达提供启示。
[关 键 词] 女性绘画;自我画像;发展历程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逐渐出现了女性文学、女性绘画、女性艺术等词汇。思想解放为当代女性画家的艺术创作插上了翅膀。她们从漫长的历史中走来,在探索内在自我的同时,也心系着社会发展。她们将自己的命运与时代的发展紧紧相连,在作品中诠释着多样的社会角色,从而展现出当下生活的真实状态。本文归纳当代中国女画家“自我画像”的代表性题材,通过解析绘画中的内容与表达方式,探究当代中国女画家“自我意识”的表达方式。
一、形与神的执着追寻——自画像与自我画像
自画像是艺术家最常见的绘画题材,学界对自画像与自我意识的研究也不胜枚举,包括对自画像功能、自画像绘画语言、自画像的精神内涵等内容。随着美术教育的发展,甚至是天真的孩童也会被要求画一幅“自画像”。自画像成了画家探索自我最常见的手段。
在詹姆斯·霍尔所著的《自画像文化史》中,将自画像分为旁观式自画像、群像式自画像和独立式自画像。而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说中将自我画像分为潜意识自画像、伪装式自画像和替代式自画像。二者分别讨论了形与神不同的“自我形象”的描绘手段。在欣赏潘玉良、丘堤、夏俊娜、喻红、闫平、萧淑芳等诸位当代中国女画家的自画像作品时,笔者意识到画家除了将自己的肖像作为“自画像”外,其所忠爱的花草、生活的场景也都被赋予“自我”的意识。
因此,笔者综合了学界对“自画像”的概念界定,以“自我画像”为研究主题,一方面包含画家对镜写生而作的“自画像”,分析其外在“自我”“形”的描绘;另一方面也包含藏匿于画面背后的,画家内在情感、生存现状的表达;以及画家借由物象隐喻的内在精神、“神”的描绘。“形神合一”既是中国传统绘画长久以来所追寻的,也是自画像创作的重要方向。
二、失落与创造的历史——女性自画像的发展
受到身份、性别、社会角色、地位的影响,在自画像的发展历程中,女性画家长期处于“失语”的状态。与男性画家笔下自画像中展示技巧、炫耀地位、致敬大师、宣扬信仰的画作不同,女性画家的自画像更内敛。但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差异也使得中西方女性绘画的发展特色、绘画题材、语言呈现不同的面貌。
(一)西方女性自画像的发展
正如琳达·诺克林所说,在19世纪以前,女性艺术家被关在了艺术学院的大门外。社会思想禁锢了早期女性画家的绘画表现。在文艺复兴与巴洛克时期,尽管女性画家较少但已经有女性画家尝试自画像创作。她们的作品不仅展现了女性细腻的情感,也受到了盛行的宗教、神话等题材的影响。
19—20世纪,西方社会女性地位的提升与女性主义的思想兴起,给女画家自由表达自我意识与独立精神创造了条件。作品的审美风格也不再受限于传统的审美标准,更注重内心世界与情感体验的抒发。
进入现代艺术时期,女艺术家开始对技法与风格展开更大胆的尝试,涌现出了一批表达自我、探索身份的女画家。弗里达·卡罗就是西方女性自画像的代表性画家。她的自画像不只是对自己形象的描绘,更是其内心世界与人生经历的写照。她的“一字眉”和上唇的胡子不只是她自画像中的“符号”,亦是她对自我的认同,浓烈的色彩也抒发着对生活的热忱之情。
在当代艺术时期,西方的女性自画像已不仅是内心的真实写照,也成为艺术家讨论身份、性别、情感以及社会问题的艺术载体,这使得女性自画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二)中国女性自画像的发展
中国女画家的自画像发展与西方相比则更不易。不只是在“自画像”这一题材,据文字记载最早的女性绘画出自三国时期吴王后赵夫人之手。在漫长的历史中,女性绘画都只以少数的文字被记载着。也许此时充满“遗憾”便是女性绘画历史的特色。直至五代、宋元时期,女性绘画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元代赵孟頫的妻子管道昇的作品流传了下来,成为研究女性绘画的宝贵图像资料。画面中极富文人气息的竹石彰显了“巾帼不让须眉”的气魄与格局。明清时期,闺阁画家与青楼画家受到身世境遇的影响,形成了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一批优秀的女画家逐渐涌现出来。在闺阁画家中,尤以文俶(文徵明的玄孙女)与仇珠(仇英之女)的作品最出色。当我们将其父辈的同题材作品与她们的作品进行对比赏析时,女画家内心高洁的志趣与独立的品格可见一斑。正是前辈女性内心蕴藏的“山河”之气与笔下书写的“英雄梦想”才为当代女画家铺就了艺术发展之路。
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女性也从绘画作品的描绘对象转变为描绘作品的主人,这也使得对女性绘画、女性自画像的相关研究丰富了起来。当代中国女画家喻红、闫平、夏俊娜都大胆地运用自画像表达自己的社会角色、对女性身份的认同;记录生活的阅历并传达自己对社会生活的思考。她们的作品多了一份社会责任感与幸福感。
尽管我国女性绘画的发展历史有些曲折,但当今绘画题材的突破、作品数量的增多、女画家群体的建立都鼓舞着女画家队伍的士气,也使她们的画作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量。
三、灵魂与内心的对话——女性自我画像的代表性题材
(一)自我观照——自画像
“自画像”不仅是当今美术院校学生入门的基础课程,也是大多数画家艺术创作的“第一课”。无论是外在形的描绘还是内在神的传达,都离不开“自画像”这一主题。画家终其一生都在绘画中记录“生命痕迹”、捕捉“真实自我”。
民国才女画家潘玉良被誉为“中国印象派第一人”,她的自画像也别具一格。不论是拿书或执扇的自画像,还是正襟端坐的自画像,她总是皱着眉。她看向画外的双眼似乎也在审视着自己与世人。但在她众多的自画像中,1963年的《半裸的自画像》与其他的作品大相径庭。画中的潘玉良面颊微红,袒胸露乳地坐在桌旁,放下了原本的拘谨。据文献记载,这是她唯一一幅微笑着的作品,也是最接近其真实面貌的一幅。她在这一系列自画像作品的表达中逐步寻得了真实的自己,完成了其人生的“蜕变”。从青楼女子的悲惨身世中走出来,成为大学教授、成为享誉世界的女画家,是艺术赋予她第二次人生的选择。
在作品中,她不刻意规范自己的面貌,无论是紧锁眉头、收起笑颜的凝视还是双颊微红、含笑静思,与一众男性画家笔下性感妩媚、忧郁懵懂的女性形象不同,她的作品中多了率性、独立与自由。她在创作中探索自己,也通过作品向世人传达新时代女性不该被定义的美。
(二)格物精神——花卉静物
中国文人喜欢“格物”,喜欢在自然事物之间探索自己、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喜欢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在中国早期的绘画史中,女性受到社会地位、文化、角色等的束缚,而无法自由的表达自我,因此有许多女性借由诗词传达内在的情感。
“花卉静物”题材是女画家借以抒发情感、展现个性的独特符号。这与当下人们赠送花卉、室内插花的出发点相似。花卉的寓意与使用场景十分重要,女画家在描绘花卉时不会随意将就。在结合女画家的身世赏析时,笔者注意到画家常喜欢选择具有美好寓意或与自己性格相称的花卉加以表现。正如娇艳美丽的才女陆小曼以设色艳丽的花卉表现自己绚丽多彩的人生,而画家何香凝则以一株梅花来传达自己独立、高洁的品质。
(三)窈窕淑女——女性美与女人体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女人体为描绘对象、展现女性曲线美的作品往往出自男性画家,而女画家则更多地表现花卉、静物、风景等题材。画家常玉的“裸女”享誉世界,他笔下的女人体都是线条婀娜、搔首弄姿的女性,仿佛不问世事、悠闲自在。而第一位大胆画女人体的女画家潘玉良却饱受责难,因为她笔下的女人更真实。乳房下垂、腹部隆起,全然没有女性的细条美感,却使得许多女性潸然泪下,世人对人体绘画的态度差异也侧面展现了社会文化、传统思想给女画家带来的创作压力。
与表现女性的娇美和迷人不同,喻红选择记录女性的一生,她以自己为描绘对象,展现了女性从女儿、妻子到母亲的角色切换,随着岁月流逝的不仅是青春与美貌甚至是健康。她的作品更多了女性精神的力量与生命的厚度。她放弃了在作品中直白地表达“曲线美”,而选择表达生命真实的美感。她在《目击成长》系列自画像中引导世人思考如何定义美,以及女性的美是否该被定义等问题。
(四)生命叩问——女性精神世界与生存写照
女画家不仅从闺阁逐步走入社会,也从自我的世界中走进了人群,走入了火热的生活中。或许是女性本就拥有敏锐的神经与细腻的情感,女画家的作品并没有停留在孤芳自赏的层面,而是将目光投向社会生活,发挥艺术育人的属性。许多画家尝试在作品中反映女性的生存现状、思考人与时间、社会和自然的关系,诠释自己对生命理解的同时也发人深省。
画家闫平连续数年的《母与子》系列作品,画的是旁人,亦是自己。在她的笔下,母子的平凡日常愈加温馨。她的作品刻意回避了人物面部的描绘,而选用具有概括性的色块与具有“冲突性”的色彩。凌乱的画室、缤纷的色彩与母子画像传达出生命真实的感动。画家笔下描绘的母与子大多是温馨的场景,孩子在母亲的怀抱中看书、嬉闹或是安睡,母亲永远是温柔地注视着。唯有一张画带给笔者不同的感受:蓝灰色的画面中蕴藏着忧郁的情感,一位中年母亲端坐在画面中,一旁是抱着玩偶熟睡的孩子,孩子的头枕在妈妈的腿上。与孩子平静的面庞不同,母亲的表情有些凝重。画面的背景是著名的《格尔尼卡》中的场景,笔者猜测画家想借《格尔尼卡》反映母亲因外部纷杂的社会而担忧孩子的成长。这与中国式的父母十分契合。“中国式”的父母总是担忧孩子的未来,孩子无忧无虑的童年背后是父母为其“负重前行”。
画家不仅在作品中记录自己的人生体验,也借由作品展开对生命的思考。作为女性,社会生活赋予她众多角色的同时,也给予她许多责任。作为母亲,她们不仅要工作,更要承担抚育子女的责任,画家将自己对当下女性生存现状的思考注入作品中。
画家在自我画像的过程中审视自我、叩问生命。这些发问来源于闫平在柴米油盐中的生活所思;来源于喻红在人近半百时的生命回望;来源于张忆周在繁华都市中的顾自清醒;来源于张钰在现实与虚幻中的内在觉醒。艺术家在绘画创作中不仅要看到自己,更要看到众生;不仅要思考自身生活中的意义,还要肩负起世界未来的责任。
四、值得我们骄傲的时代——由女性自我画像引发的思考
“自我画像”的创作过程既是画家对外在自我的描绘,亦是对内在自我的挖掘。本文之所以将“女性”的自我画像单独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是在所有“自我画像”的作品中,女性画家的作品依然在少数;另一方面,对女性自我画像的欣赏与解读也是艺术创作中重要的一环。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中不断地探索着自我;大众则在欣赏作品的过程中解读作品并找寻自己的“答案”。
笔者梳理女画家笔下人物肖像、花卉、女人体等题材的“自我画像”作品,感受到中国女性画家群体蓬勃的创作热情。中国女性画家的作品流露出的不是对生活压力的不满,也不是对人老色衰的惆怅,而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对真实自我的追寻。女性自我画像作品的丰富是如今时代所赋予的,能够不避讳地在作品中流露真实的生命体验是世人值得骄傲的。艺术不分国界,更不应论性别。在对西方美术史的大师“倒背如流”时,许多优秀的中国女性画家却鲜为人知,这无疑是令人倍感遗憾的。在倡导文化自信的今天,以女性画家群体的作品作为专题赏析,以期在未来可以形成更包容、更多元的艺术观。
参考文献:
[1][英]弗朗西斯·波泽罗.女性自画像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
[2][英]詹姆斯·霍尔.自画像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
[3][美]文以诚.自我的界限:1600-1900年的中国肖像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作者单位:长春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