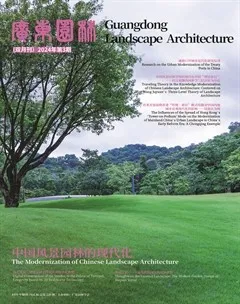叠园之思
2024-10-20方北辰翁子添





摘要
20世纪60年代,随着杭州城市与公园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杭州“玉泉鱼跃”景区进行了一次公园化改建。项目在既有历史遗址上改建,吸收传统造园手法,又结合了现代空间操作手段和新型材料工艺。以玉泉改建项目为研究对象,在梳理项目建设背景与实地测绘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其对空间序列的重组、对游览路径的重构,以及参考自古典园林的空间操作手法,重新梳理建筑和自然的关系。并将该项目与不同时期的造园案例进行对比研究,论证玉泉改建项目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其空间操作和建造语言等造园意匠所体现的现代性和创新性。
关键词
玉泉鱼跃;现代性造园;现代建筑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志码: A DOI:10.12233/j.gdyl.2024.03.007
文章编号:1671-2641(2024)03-0045-08
Abstract
In the 1960s, driven by the need for urban and park modernization in Hangzhou, the Yuquan Yuyue scenic area transformed into a park. The project, situated on an existing historical site, integrated traditional gardening techniques with modern spatial manipulation methods, innovative materials, and craftsmanship. Taking the Yuquan renovation project as a case study and based on the review of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background and field survey data,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reorganization of spatial sequenc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visitor paths, and the 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chitecture and nature using classical gardens as a methodology. Furthermore,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gardening(garden design) cases from different era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modernity and innovation embodied in the spatial manipulation and construction language of the Yuquan renovation project within its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Keywords
Yuquan Yuyue; Modern gardening; Modern architecture
文章亮点
1)在古建筑遗址上建设新的公园,既满足现代公园的需求,又回应了遗址场地的文脉;2)玉泉鱼跃景区在设计手段上既结合了设计师对于传统造园手法的理解,又运用了自由流动、相互联络的现代建筑空间手法;3)玉泉鱼跃作为1960年代设计师对现代主义建筑的理解与尝试,呈现出几何控制的简洁平面和新材料仿制的传统建筑构件,准确表意,与古为新,并作为今天进一步探索与创作的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城市公园的兴建作为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提上日程,而杭州作为中国园林特别是公共园林营造的典范城市,在探索传统园林与现代公园相结合的路径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杭州传统公共园林向现代公园的转化至少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之后的“西湖入城”都市计划①[1]。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杭州已完成“西湖十景”、灵隐寺、六和塔、净慈寺、岳庙和湖心亭等风景点的修缮保护,以及数十个传统名胜的公园化改造[2]。在此次西湖公园化运动中,出现了将英国自然风景园与中国传统山水园林结合的花港观鱼公园②[3],同时也不乏将传统庭园与风景名胜相结合、探索现代空间与材料的佳作,玉泉景点的改建即为其中一例。不同于花港观鱼公园受后来学者系统研究并获得里程碑式的地位,稍晚改建的“玉泉鱼跃”的相关研究则相对匮乏。本文基于对玉泉景点现存建造的实地测绘与文献整理,尝试浅析设计师在20世纪60年代的改建中“古”“新”叠合的操作手段,辨析其中园林营造的具体路径。
回顾玉泉改建前后的时代背景,1952年10月,“西湖风景五年规划”[4]提出了“采取民族形式为主,同时在色彩上力求明丽愉快,在布置上力求广大开朗”的设想,由此开启了这场新的西湖公园化改造运动。从提倡“全面学苏”到“民族形式”的探索,在这场改造运动中,现代与传统如何接洽无疑是最重要的课题。作为当时西湖园林建设的主要实施者,时任杭州市建设局局长、杭州市园林局局长的余森文先生提出“在空间设计方面要打破古代庭院的封闭性,把风景名胜区与园林庭园结合起来”的设计构想。而园林庭园具体为何,又应该如何继承,已经是当时公园管理者与建设者研究的普遍课题。自1953年刘敦桢先生领导的中国建筑研究室对苏州园林展开系统研究起,至20世纪60年代初,对传统园林的空间分析已经趋于系统化,特别是对视线和路径的结构性分析[5]。与此同时,“园林”作为一种特殊的空间经验也逐步在公园建设中被作为方法运用,其中又以广州市建设局设计科集体创作的一批与现代建筑结合的园林小品最为典型[6]。不同于岭南园林小品锐意创新的实践路径,1963年的杭州园林建设者所面对的玉泉改建项目叠加了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文化内涵,摆在他们眼前的还有“何以玉泉”的课题[7]。本文以20世纪60年代玉泉改建项目为研究对象,尝试探讨其在空间操作和建造语言等造园意匠方面所体现的现代性和创新性。
1 何以玉泉
位于仙姑山青芝坞口的玉泉,于20世纪50年代被纳入杭州市植物园,成为植物园内一处园中园。作为西湖景观群的组成部分,玉泉最早见于南宋《咸淳临安志》:“玉泉,南齐建元末,灵悟大师昙超开山说法,龙君来听,为抚掌出泉。今龙词前有小方池,深不寻丈,清澈可见,异鱼数百,泳游其中”[8]。五代后晋天福三年(938年),始建净空院,而后历代皆有重修。至清代康熙年间,皇帝临幸赋诗并赐寺名“清涟寺”。雍正年间高官李卫疏浚西湖重整寺院,再修洗心亭,并录“玉泉鱼跃”入西湖十八景。清末至民国,玉泉周边建筑得到进一步改扩建,原先独座“洗心亭”及回廊被更替为连贯的亲水建筑,辟为公共茶廊。1964—1965年,随着杭州植物园的建设,玉泉在原有遗址上进行改建。2001年,玉泉再度进行修缮扩建。此次建设在拓展南部山水风景园的同时,较好地保留了20世纪60年代修建的北部庭园,为本次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场地考察基础。
根据学者汪艺泽对玉泉鱼跃景区历史变迁详尽的梳理与复原的相关研究,大致可以窥探景区前身清涟寺的旧观。汪艺泽指出,清代清涟寺的相关图像属其引用的吴门画家郁希范所作的《西湖胜景图册》最为可靠[9]。关于20世纪60年代的改建,目前所保留的文字记录寥寥,主要见于施奠东主编的《西湖风景园林1949—1989》中《玉泉鱼跃景色新——玉泉的改建设计》一文[7]。文章简要回顾了实践过程中的思想原则和构思,为本次研究提供了一手的文献资料。由于当时多为集体创作,具体参与项目的设计师并没有留下详细的记载,从该文中可以大致了解作者王品玉曾深度参与该项目。另外,在吴婧一关于建筑师何鸣岐的专项研究[10]中亦能发现,1961年何鸣岐曾参与玉泉风景点规划设计,并绘制过一版仿古建筑风格的鸟瞰图方案。虽然落地方案与何鸣岐的方案相去甚远,但何鸣岐前期所秉持的设计原则似乎对后期方案颇有影响,对本次研究亦有参考旁证作用。
根据目前所能查阅得到的方案图纸,结合现场实测,形成玉泉鱼跃功能布局沿革(图1)。从清涟寺布局来看,玉泉一直作为独立的庭院出现,由北向南直接进入。玉泉作为清涟寺的一部分,从硬山殿南向伸出一条廊道,包围寺院第一进,专设洗心亭正对泉水,并借此区分出主次关系,形成寺院一侧静态观赏和围绕玉泉一圈动态观赏的对望格局。
图1-c平面图是对20世纪60年代改建方案的改绘。改建围绕着“鱼乐国”“珍珠泉”和“晴空细雨池”3组泉景的位置和尺度展开,并以场地原有的百年古树立地环境作为基轴进行精细安排——东北角是现状入口,经过折廊往南通向鱼乐国,珍珠泉和晴空细雨池在西侧依南北分列。方案以泉水本身的游览体验作为重点,由院落所形塑的流线来表达递进关系。下文即以此平面为参考,结合文献资料和现场体验,从3个方面对玉泉鱼跃如何实现场地“古”“新”信息的叠加进行分析。
2 旧园更新的三重要素
2.1 重组空间序列
从寺庙格局到现代园林格局的转变,决定了既有轴线转变的必要性。原先玉泉作为寺院的附属部分存在,在进香或者游览游线的一侧出现,与参拜行为本身的关系也不甚紧密。故在宗教因素被革除之后,对于景观的重新塑造决定了玉泉被改造成为现代公园后的呈现方式。
首先,入口向北调整偏移。较之原有入口与寺庙内部轴线的联系,改建方案入口位置向北偏移约6.5 m。隐于密林的玉泉入口以低调的方式激发访客探索的欲望,而比邻的山水园深受英国自然风景园风格的影响,开阔畅朗,两者形成空间“旷-奥”转换的对比。另外,入口的北移对于庭院内部而言,拉长了从入口抵达高潮空间鱼乐国的路径,为丰富游历体验提供了契机。
其次,确立鱼乐国的主体地位。东北角的主入口和西北角的次入口的互相牵引,串联起3组被泉池所定义的庭园,并形成近似于“品”字形的格局,其中又以鱼乐国及其院落所占的比重最大。从平面上看,珍珠泉和晴空细雨池可以被看作一个完整序列内的2个部分,两者共享一处出入口,将其与由主入口单独通向的鱼乐国作为区分,也保证了鱼乐国的独立性。与之相对,晴空细雨双池作为原本仪式性轴线的主体——大雄宝殿的前庭的景观要素,占地与鱼乐国相当。为了避免喧宾夺主,设计通过将大空间化作小空间的处理手法,化整为零,并赋予庭院、连廊、敞厅和花架廊等要素,在丰富空间体验的同时,对感知尺度做了更细化的设计。
再次,消解既有轴线。回顾清涟寺场地平面,寺庙主要由东西进深方向的轴线所组织:主轴线自东北侧山门进入,依次串联作为寺庙仪式性空间的主体建筑,其中晴空细雨池的两方泉池处于第二进院落,作为其景观要素之一。经幢、佛像等要素位列轴线中心,建筑统治轴线主体。新设计选择以3个泉池为中心的院落作为玉泉的主角,轴线和游线的布置,将3个泉池联系为一个整体的园林,并以观鱼和品茶为主要的体验。此时,场地的轴线或游线转而自北向南,指向了体量最大的鱼乐国,也将是3组泉池中的高潮部分,空间之“旷”者。不破不立,原有的主轴在失去礼佛的主体殿堂建筑后,空间序列在新设计中被一系列南北方向的要素所截断——或是入口正对的树石小院天井,或是2道长度超过10 m的实墙屏风;原先清涟寺法堂的建筑体量,也被南北狭长的花架廊、连廊和1个敞厅所取代。
2.2 重构游园路径
改建后的玉泉鱼跃围绕着3组泉池院落展开,其内部主要游线由3条洄游式的动线串联而成。与此同时,主入口的偏移带来的是一段“涉门成趣,得景随形”的行游体验。北部侧入口的开辟则形成1条视觉与触觉分离的副轴线,呈现出空间深远不尽的意象。
访客从主入口经过三折进入玉泉:迎面的空窗天井,饰以粉墙树石,为入口玄关装点出一幅写意图画;玄关南折,角接了另一个过渡性的“房间”,与南向的连廊衔接;南向连廊直通鱼乐国,该路径尽端处以2幅对称落地的冰裂花窗夹合出中间框(指水中的经幢画框),结合亲水的美人靠坐凳,将路径收束于如画的静景中。这一从偏狭入口行进至开阔山水园的方式,在1961年何鸣岐先生的规划构思中早已呈现,并得以贯彻落地。不同于传统寺庙的仪式性轴线,这种布局构想似乎能在传统园林中找到更多关联性,其中就以20世纪60年代多位学者对留园入口的关注和阐释最具代表性。
次入口开辟于全园北侧,为原清涟寺北侧配殿所在。较之主入口婉转成趣,次入口为一月洞门,正对晴空细雨两方泉池,同时连接其左右环抱的回廊。回廊尽端又构以月洞与次入口遥相呼应。视线穿过这方似窗似门的月洞后,越过后侧2层空窗,直达珍珠泉的院落群,形成一条纵贯南北的副轴线(图2)。不同于视线的深远,身体行走的路径却被眼前的泉池所阻隔,需沿池两侧连廊绕行,游历庭园的周长。这种视觉与身体相分离的游历方式,使得空间的感知被拉长,配合轴线上多重的空窗透景,加强了观者在迂回的游线中对空间深远的感知。
与此相配合的是游线尺度的差异化。根据实际测量,入口折廊在南北向的宽度约为2.7 m,与晴空细雨池院的2处檐廊宽度相同。而珍珠泉院的侧廊宽度为1.8 m,主廊为3.6 m。通过这些实测数据,或许可以猜测,0.9 m是整个景区改建的平面模数。这些廊道在鱼乐国4个方向都被不约而同地放大为5.4 m,从而形成一个足以停留聚集的敞厅。设计通过模数的差异化处理,使3处主要庭园之间的联系各有疏密,并完成了对路径等级的区分。
2.3 以庭园整合建筑群
在《玉泉鱼跃景色新——玉泉的改建设计》[7]中,作者曾提到“在整个庭院内,天井与厅室之间,不设隔断与门窗扇,在天井内除水景外,均处理成不同的花木山石小景,使室内外景观互相渗透、融成一体”的设计手段,以达到“压缩空间规模,妥善掌握尺度”的作用。从建成效果看,取消传统园林的门窗装折,随之带来的是庭园之间透景线的营造;而花木山石小景不仅为院落置入了丰沛的自然意趣,同时也重新定义了建筑与自然的关系。
设计借由庭园间的透景线串联起建筑群内部空间。叠加于场地之上的玉泉改建方案,以一座寺庙的建筑群为基底,3组方池泉景为依据,在平面上呈现出清晰的结构。这种院落组合的结构又通过内部庭园之间的长透景线被访客所感知,呈现出通透敞朗的空间效果,与传统江南园林的“曲径通幽”大相径庭。首先,前文所述的南北方向副轴,沿次入口借居中的不同类型的开窗依次串联了4个院落。沿副轴两侧对称分布的是由晴空细雨池和珍珠泉四周连廊、门洞串联的次透景线。而其中,晴空细雨池东侧的连廊直通鱼乐国庭院,也形成贯穿南北的动线。东西向的透景线主要存在于晴空细雨池院和珍珠泉院之间的过渡院落,经由鱼乐国北侧的敞厅消隐于东面的自然山林。这些或长或短的透景线在室内外间形成明暗交替的诱人景深,同时也整合了对建筑之间的顺序、气质等结构性感知。
配合视线的经营,庭园的介入弱化了建筑空间的边界,使自然景物流动于建筑空间——整个玉泉庭院或可被理解为一组带有不同自然意趣的“房间群”的组合(图3)。
以珍珠泉院落为例,这组院落本着“小巧、多变”的设计意图,被处理为3个不同意趣的空间小品:北部庭院与晴空细雨池相邻,隔以带四樘花窗和花格月洞的粉墙,庭中种植了樟Camphora officinarum和大量木樨Osmanthus fragrans,光影斑驳;中部泉院简洁朴实,剔除繁复装饰以突出一方古泉;南部庭院则高砌松石花台,凭一方空窗,向中部泉院投以树石画意。从平面上看,这3个院落尺度相仿,沿副轴线对称布置,中部与南部两庭更近乎镜像对称。然而流连其间,树石林泉透过差异化空窗不断复现,深远不尽的透景传递出别院诱人消息,庭中之景无分内外、远近,也大大提高了其中仅有的花木山石景物的利用效率。通过3个小庭院的并置与联系,原本体量最小的珍珠泉也获得了丰富的体验方式。
另一处带自然意趣的“房间群”位于原清涟寺法堂所在。场地南北横亘的砖雕照壁,将空间隔断为类似“鸳鸯厅”的东西面向:面西一方敞厅连缀两端的见方树庭,面东一方横庭覆以花架密梁。如果说敞厅旨在通过照壁隔断出面向泉院的空间姿态,东厅(即敞厅东侧)则借由C型粉墙围合出的藤荫凉庭,独立于主要序列之外。不同于花架休息廊平面的窄长比例,横庭进深6 m有余,满覆的藤荫密梁滤下内部柔和的光线,呈现稳定而匀质的空间品质。被雨水与藤蔓侵蚀的混凝土密梁呈现出废墟常有的粗粝表面,与光影斑驳的粉墙、地坪对比出自然与人工判然特征,勾勒出此地曾经的空间体量。藤荫南侧的粉墙开四樘花格空窗,与南面的鱼乐国敞厅相邻。敞厅的设计深谙《园冶》“北牖虚阴”的借景智慧,在坐凳与粉墙间嵌入一狭长的夹墙竹庭,借南向的自然高光将高耸的粉墙映照出一片氤氲的水墨竹影。3组并置的“房间”面向各异,或幽或敞,意趣迥然。
不同于自然与建筑图底的二分法,“房间群”的组合方式,不是在自然山水中布置园林建筑,也不同于利用建筑的剩余空间置入自然,而是在“房间”单元中考虑自然意趣,并通过房间之间视线的联络,共享庭园的花木景致,从而整合为互相渗透的整体庭院。
3 与古为新:空间营造的形意对话
3.1 几何与意趣
在20世纪60年代的改造里,玉泉做到了一方面规避宗教氛围,另一方面在保留泉池建筑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发挥场地的观赏价值。这有赖于设计师借古典园林设计方法对空间进行的一系列再创造。如果“涉门成趣”的主入口游线能让人联想到苏州沧浪亭翠玲珑角的行游取景,那晴空细雨池与珍珠泉序列轴上几重相间于花木山石间的窗洞,则令人忆起杭州名园郭庄的一处经典取景片段:景苏阁外的回廊,3个叠加的扇形空窗同样相间于天井花木之间,明暗交替间将视线导向湖面的光影(图4)。
然而游览之余复盘场地平面,却一时间难以将其与传统园林相联系。不同于传统园林平面的“自由”,玉泉的平面呈现严谨的几何、轴线关系。首先,新旧两园的叠合是基于场地原有的寺庙空间关系,同时旨在尊重遗留的几何泉池、古树和基本标高。其次,不同于传统园林中“截溪断谷”的山石景象,以方形泉池为核心景象的玉泉庭院将空间本身的演绎发挥到极致——“天光云影共徘徊”的方池本身不占据视线的焦点,仅作为空间观想的对象。再次,玉泉庭院作为公园在空间尺度上与传统宅园的差异,也是对时代与功能需求的回应。
即便如此,几何也无碍于玉泉的园林意趣:两两相邻的院落,旷奥、明暗判然,又通过门窗透景互相联络,隔而不断;环形嵌套的游线,每每让人心生遍览贪恋,既不至于迷失来径,又拓展了空间的感知。这些体验,正如学者周仪在对照留园石林小屋与红砖美术馆方庭所指出的:“几何形态并非园林经营所要避讳,只要它不是园林经营的目的”[11]。玉泉对传统园林营造方法的继承,旨在几何间营造意趣,这不仅表现在场地内轴线与视线的准确经营,也可从平面所隐藏的模数关系中推测出其理性的设计方法——通过差异化的模数运用,完成空间与路径等级的划分,以及通过弱化装饰表达来着重于空间以及氛围的塑造。这些无疑都是现代主义所提倡的设计方法。
3.2 语言与表意
除了结合平面理解玉泉方案在空间上的操作,其形式与建造上的语言,对空间表意有着同样重要的影响。根据1961年何鸣岐先生参与此项目所绘制的早期方案,鸟瞰图上呈现为一组复古样式的建筑组合,保留了明清时期繁复的形式与装饰。最终落地的玉泉庭园简化了诸多古典建筑语言,同时运用了新材料、新技术进行形式转化:整体建筑群采用了钢筋混凝土结构,在屋顶部分仿江南民居木构表现其梁架搭接关系,并利用预制混凝土梁的特性,构造屋顶两坡“曲面”;装饰方面删繁就简,大方清新,取其材料自身色泽和质感。除开历史环境与经济条件等原因,也可从设计语言与表意等视角对玉泉的建筑形式与风格试作探讨与反思①。
玉泉建筑群在形式与风格上受到了建工部建筑科学院的支持与帮助。20世纪60年代,建筑科学研究室开展了针对传统民居的系列研究,其中又以《浙江民居》最具典型。根据赵越、沈攀等[12~13]的研究,《浙江民居》将现代主义“空间”“环境”等概念引入传统式样的建筑实践里,首次将建筑与环境、建筑室内外视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这些研究深刻影响了参与民居系列研究的建筑师尚廓,并在其于桂林的一系列风景建筑实践(20世纪70年代)中得到转化与运用。而建科院在玉泉设计过程中提供的指导,或许也影响了玉泉的建筑语言与空间表意。
以吊顶为例,玉泉的连廊及部分敞厅为钢筋混凝土平屋面,其余坡屋面则被统一为平棋天花,将整体室内净空控制在约3.3 m。一方面,室内吊顶隐藏了混凝土不擅表达的屋顶内部架构,仅在建筑的山墙或檐下挑出梁头以示其构造关系;另一方面,平棋天花与混凝土平屋面一道,勾勒出玉泉院落内部相对匀质化的空间,进一步模糊天井与厅内的空间边界。加之混凝土构造带来的长跨度、细柱径和大开窗,视线足以在室内外之间平滑游移,回应“广大开朗”和“打破古代庭院的封闭性”的任务需求。
此外,项目在细部构造上的语言也颇具巧思,其美人靠及栏杆尤具代表性(图5)。两者借助现代简练的设计与构造,与建筑对古典语言的灵活转译相得益彰。美人靠由包漆钢构件支撑,构件从座位背侧伸出,外侧线条硬朗,内侧则较为圆润,交于美人靠上下2处木质横架上,使构件尾端低悬于大理石或者水磨石台面。此外,美人靠构件的位置与长椅落脚柱位置相同,不难看出这在设计上即为一体考虑,便于模数化复制。玉泉外侧的栏杆更具特点,栏杆整体刷成深灰色来消解铁质的金属光泽以适应场地氛围。每个栏杆单元分成上下两段,上段相对较窄,中间不设竖向杆件,顶部扶手较宽,微微向内延伸,便于抓握;而下方则均匀布置竖向杆件,作为支撑。栏杆接地长杆中间较粗部分为方柱,连接下段,两头较细部则为圆柱,在相交处就以弧面收束。上方圆柱连接顶部长杆,下方圆柱则在距离地面5 cm处戛然而止,以更细的铁杆接于地面。栏杆构件以直角和弧面的变化使其横向线性更突出,与几处窗洞的装饰框景相呼应。除了与地面相接,栏杆还利用水平向铁杆与柱子相接,以最低程度的干预来避免对其他材料造成破坏。
4 结语
玉泉鱼跃作为20世纪60年代的实践作品,呈现出设计师对传统园林、现代公园、现代性空间等命题的独特思考,其价值历久弥新:1)玉泉项目改建旨在新旧之“叠”,与古为新——在原有清涟寺历史遗址上再造新园,既满足新园作为公园的需求,又在细微之处继承场地文脉遗韵;2)玉泉项目在设计手段上既结合了设计师对于传统造园手法的理解,又运用了现代建筑空间的操作,打破传统庭园格局的封闭性,其空间自由流动,互相联络,又不失山水意趣;3)在设计方法与建筑语汇上,玉泉项目的平面呈现出几何控制的理性结果,其细部又以新材料模仿制作传统建筑构件,服务于空间的准确表意。这些都反映了玉泉项目设计师对现代主义建筑的理解与尝试,并在多年后的今天,作为进一步探索与创作的来源。
回顾20世纪80年代,中国建筑界曾出现了一批以民居、园林为建筑创作源泉的杰出实践,包括习习山庄、方塔园、武夷山庄和阙里宾舍等。学界一般认为这些建筑实践的思想依据可追溯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中国建筑研究室为代表的民居和园林的研究,而1960年代完成的玉泉改建项目,正是这些研究成果较为早期的一次实践转化。玉泉鱼跃对传统的借鉴,展现了设计师对现代主义空间、构造等理念的追求。本文对玉泉的再思考,试图丰富中国前辈建筑师在追寻传统道路上所呈现的图景,亦是对中国现代建筑经验的反思,或为当下实践提供启发。
注:图片均为作者自摄自绘。
参考文献:
[1]王欣,何嘉丽. 杭州西湖“公园化”历史及文化变迁研究[J]. 中国名城,2017(3):48-55.
[2]何嘉丽,王欣. 20世纪50年代杭州西湖风景园林建设历史研究[D]. 杭州:浙江农林大学,2020.
[3]柯鑫鑫,王欣. 杭州近现代公园发展研究(1912-1993)[D]. 杭州:浙江农林大学,2011.
[4]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西湖岁月:新中国建立以来西湖风景区治理保护工作纪事[M]. 杭州:杭州出版社,2008:44.
[5]鲁安东. 隐匿的转变:对20世纪留园变迁的空间分析[J]. 建筑学报,2016(1):17-23.
[6]董书音,黄全乐,翁子添,等. 狭缝之间:1958-1985年间的广州园林小品建筑[J]. 建筑学报,2022(11):82-89.
[7]王品玉. 玉泉鱼跃景色新——玉泉的改建设计[M]//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 西湖风景园林:1949-1989.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8]汪艺泽. 方潭塔影,杭禅遗珠——清涟寺玉泉观鱼复原研究及意匠初探[J]. 华中建筑,2022(1):155-161.
[9]汪艺泽. 杭州玉泉观鱼景区历史变迁与研究文献初探[J]. 园林,2019,36(10):40-43.
[10]吴婧一. 何鸣岐建筑实践与建筑教育研究[D]. 杭州:浙江大学,2022.
[11]周仪. 红砖美术馆庭园三识[J]. 建筑学报,2013(2):52-55.
[12]沈攀,林广思. “布扎”与现代主义的融合:从《浙江民居》看一种中国民居研究方法[J]. 新建筑,2022(5):34-39.
[13]赵越. 走向民间建筑,探索另一种传统——对中国建筑研究室(1953-1965)之住宅研究的研究[D]. 南京:东南大学,2014.
① 即1911—1914年,政府拆除湖滨旗营城墙,进而开放湖滨空间,推动西湖东岸与城市融合的一系列规划举措,包含了标卖土地、建设商铺、修建环湖马路以及公园、举办西博会等一系列内容。学者张燕镭在其论文《杭州近代城市规划历史研究(1897—1949)》中提出,这一举措表明了当时国民政府已经对西湖景观加以控制,使湖山胜景向“现代城市中的城市公园”发生转变。
② 西湖现代公园广泛使用了西方园林的设计手法,1950年代由孙筱祥设计的花港观鱼就是其中一个代表。花港观鱼依赖场地本身较为多样的地形,使用了流动空间理论,根据空间体量和尺度等属性的差异来对空间构图做出不同定义,从而利用山石花木,通过连续、渐变等手法区分、连接不同主题。科学的造园方式丰富了游览体验,使人在空间序列之间体味情绪变化,感受传统意境。除此之外,孙筱祥先生还在同一时期主导了杭州植物园的规划,对玉泉鱼跃的设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① 将玉泉与石林小屋进行对比,玉泉还原了后者庭院所展现的清幽迷幻的空间氛围,以其匀质而小尺度的空间转换和对重复景物的多角度攫取来混淆空间差异。因此在建造层面上,可以合理地规避古建筑对材料和装饰相对要求更高的形式表现。除此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社会舆论环境对造型繁复的仿古建筑亦不甚宽容,因此采用仿古建筑的做法在当时的经济条件、生产水平、和社会观念下都存在不小的创作压力。
作者简介:
方北辰/1994年生/男/浙江杭州人 /硕士/自由建筑学者(杭州 330103)/专业方向为建筑史、建筑设计理论
翁子添/1990年生/男/广东汕头人/本科/广东园林学会盆景赏石专业委员会(广州510642)/专业方向为风景建筑设计、岭南盆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