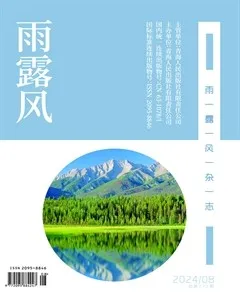乡土中国新气象的书写
2024-10-14廖涛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土地是历代人赖以生存的基础。在各类文学作品中,土地常被赋予“母亲”“哺乳”等象征意义;在神话传说中,土地是盘古身躯的一部分化育成的中原大地;在历史战乱中,土地往往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道教中的后土娘娘等尊神,也进一步强化了土地在宗教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乡土文学作为中国文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自五四时期起,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乡土记忆是中国作家难以消逝的记忆,每个时期的乡土书写都承载着不同的社会经验和情感寄托,随着新时代社会的变革,乡村必然发生变化,与之而来的乡土叙事也必然发生新变。
一、新时代乡土中国的书写
作为生于大地、长于大地的中华儿女,乡土是根植于内心深处的记忆。五四时期起,众多乡土作家的书写都落脚于故乡:用年少的眼光回忆乡土,用知识分子的目光审视乡土。故土与乡愁,一直是中华儿女所拥有的共同情感。乡土文学百年的沧桑发展,突出表现了现实主义的批判姿态。乡土写实派中鲁迅的《阿Q正传》、台静农的《天二哥》、彭家煌的《陈四爹的牛》、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等,体现了作家们以现代理性精神审视愚昧农民,将对落后麻木人性的揭露以及批判性的哲学思考融入对人物和故事的叙事中,至此乡土批判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韩少功、李佩甫、贾平凹、迟子建等作家的创作中,反思与批评仍旧是乡土小说的主旋律。而新时代下,乡村振兴战略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打破了传统乡村的稳定结构,在“常与变”之间,乡村焕发出勃勃生机。作为一直具备现代性特征的乡土小说,在每一次社会文化大动荡的时间段中,都表现出不同的思想特征和艺术特色,此刻,与时俱进书写社会主义新农村更是赓续传统乡土小说的现实主义美学,以日常生活经验化的书写与宏大史诗的叙事结合讲述中国乡土新变。
新时代乡土文学应走向何方?如何回应时代之问?这是新时代乡土文学能否保持自身朝气、再创辉煌的关键。当下,乡土中国正昂首阔步走在乡村振兴这一道路上,对于新乡土文学的书写应聚焦于时代新变,真切反映现下农村的新气象新变化,这是“文学下乡”能不能走得远、走得好的关键。近年来,乡土文学的书写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挖掘乡土传统,侧重乡村历史的文化意蕴,注重乡村自然与美好人性,如王跃文《漫水》承接了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追忆余公公和慧娘娘的一生,用醇厚质朴的乡音描绘漫水村的风俗习惯、美好人性;阿来《云中记》中祭师阿巴回故乡悼念汶川地震中伤亡的村民,通过阿巴的视角,展现千年古村云中村的历史与文化,体现地震过后人们所迸发的生命力;付秀莹《陌上》着眼于乡村女性的生活琐事,表现当下普通的乡村日常生活,刻画了芳村这一精神故土……二是聚焦于乡村新变,侧重农村现实,记录乡村振兴、美丽乡村、脱贫攻坚等重大战略的实施,如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跟老百姓交心,以小见大,用贵州山村从贫困到振兴的变化,突出乡建的时代感、地方性、泥土味;赵德发《经山海》塑造了吴小蒿等一批有担当、有能力的基层干部,生动呈现齐鲁大地乡村振兴的改革历程;王松《热雪》更是聚焦民营企业对振兴乡村的作用,融入评剧元素,在乡土中国新气象的书写上充满老天津味,极具个人特色;陈涛《在群山之间》把个人扎根乡村建设的经验与文学写作融合,平实的笔墨饱含对农民的悲悯与深情,展现乡建下情理之间的村民与村干部的不易与艰难……
2022年,中国作协推出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旨在挖掘展现当下新时代中国农村在多方面巨大变化的文学作品,多角度全方位展现时代变迁中的乡土中国,诉说鲜活的山乡故事,塑造血肉丰满的人民典型,以人民为中心,创造出飘散着泥土气息的新时代文学精品。这也是文学积极呼应时代的有效而有力的创新性举措,体现了文学人的责任意识和担当勇气,新时代作家、理论家需要继续认真思考并在实践中生成解答[1]。该创作计划的提出引领新时代乡土文学扎根人民、深入生活,用真诚与热情书写乡土中国的新气象。该计划倡导要牢牢抓住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乡村脱贫攻坚的主题、主流,抓住新乡村发展变化的主轴、主体,以文学力量激发乡村振兴的高昂斗志与坚定信念,真实真切反映社会主义新农村,展现前进中的乡土中国。在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一批乡土佳作相继涌现,如杨志军《雪山大地》对草原建设的时间跨度书写以及对建设者的致敬,乔叶《宝水》对宝水村转型乡村旅游的日常化叙述,凭《本巴》获奖的刘亮程也被认为是继沈从文、汪曾祺之后新乡土文学代表作家之一。在近年的影视作品中,《山河锦绣》全景式展现脱贫攻坚伟大历程,塑造了新时代社会主义农村奋斗者群像;电影《十八洞村》以十八洞村的真实故事为原型,深入展现湖南湘西乡村在政策下脱贫的历程,诠释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全面脱贫……在新时代下,如何讲好山乡巨变的中国故事,需要紧跟时代步伐,以现实主义美学体现变化中人民的奋斗参与和创造活力,真诚地面对大众与社会生活。
二、《宝水》中乡土新气象的体现
在乔叶的《宝水》中,作者丝毫不回避自己城乡重叠的身份,用“离去-复归”的视角讲述返乡的故事,以主人公地青萍的情感史与村庄的发展史为线索,在两条线索中又穿插乡村的“变与常”,形成鲜明对比。作品以幼年与中年地青萍对故乡的不同感受切入,运用多重视角展现对故乡的回忆与现下宝水村的新变,得出唯有回到乡村才能获得内心平静的结论。不同于其他作家书写回归故乡,乔叶选择了离故乡不远的宝水村,实写宝水村的发展,暗写故乡福田庄的变化,贴合现下乡村振兴的真实发展,从人物塑造、内容安排、地方性与现代性的融合等方面着手塑造了作为美丽乡村的宝水村,展现乡村在现代社会中激发的勃勃生机,突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奋斗之志与创造之力。
第一,在人物的塑造上,作品开篇介绍主人公地青萍身患失眠症,实际上 “失眠症”是对现实的映射,是现代人在城市生活的各种重压之下精神状态的表征:失眠、抑郁、焦虑、恐惧等心理精神问题层出不穷。地青萍返乡治病是表面的情节,作者实际探讨的是乡土自然的“疗愈”作用:乡土能对抗城市文明疏离、冷漠的社会氛围,能够在必要层面与一定程度上为反哺城市以及知识者的匮乏提供新的价值和意义可能[2]。作者通过乡土与城市、故乡与他乡等形成对照,展现想象与经验的落差,从而借闲适自得的乡村生活抚慰内心 。文中用生动俏皮的方言与女性作家的细腻笔触塑造出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自我和解的地青萍,孤苦的九奶,敢骂敢恨的大英,真才实干的乡建专家孟胡子等。
乔叶在《宝水》的书写中形成了镜像对照,宝水村与福田庄,九奶与“我”的奶奶。作者情感史上的两个命运截然不同的乡村,一面是他乡宝水村在乡村振兴政策下时代的新变,是赞歌;一面是故乡福田庄的衰落标志传统乡土的逝去,是挽歌。因为奶奶与父亲“维人”的农村人情伦理世故,以及对父母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导致“我”极度厌恶故土。选择宝水村,既符合“我”治疗失眠症的意图,又刻画了乡村的新气象,表明越来越多的人为寻找乡村、寻找自然而出走城市。在九奶与奶奶的对照下,真正开启地青萍对故乡的和解。在与九奶的“扯云话”中,她发现九奶与奶奶的做派、气息极其相似,逐渐真正理解奶奶的良苦用心,也终于找到当初未能听到奶奶临死之际的愿望:回来就好。在与九奶的交往中,她对故乡由排斥到接纳甚至怀念,加深了对 “老家”意义的深刻理解。以及文中结尾“宝水如镜,一直都能让我看见她。”[3]再次印证作者安排的镜像对照,以地青萍进入他乡之后所经历的一切使自身完成对故乡的和解。
第二,在内容的安排上,乔叶结合了自身实践经验,将对故土的怀念以及与当下乡村现实发生的新变紧密联系,将数多年“跑村”与“泡村”经历融合,这些经验的叠加最终成为其笔下正在由传统乡村转变为旅游、民宿和农家乐的新型社会主义乡村宝水村。在乡村振兴的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方面上,五管齐下,统筹进行乡村建设,我们能够看到传统的乡村开始发展文旅产业,各家开农家乐,办民宿;有回归家乡工作的团委书记小曹,来宝水实习的大学生肖睿和周宁;村史馆的建设;让小朋友们去评村里的环境;还有真抓实干的宝水的行政班子,以及宝水作为美丽乡村的代表,在乡建上得到当地政府以及人民的关心与重视等。这无疑是响应了时代号召,书写山乡巨变的潮流,呼应了时代的重大主题。但往往宏大主题的书写容易脱离实际,容易成为福柯所谓“你以为你自己在说话,其实是话在说你”[4]。而《宝水》以平淡而自然的方式展开叙述,以外来者“我”截取一年的时间,按二十四节气来记录宝水的变化,以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为顺序,提出了宝水旅游业由学习到建设到成熟面临的问题:村内如何划分招牌序号,如何解决垃圾问题,如何保证卫生达标,如何对食宿定价;村外如何解决节假日堵车问题;如何处理与游客之间的矛盾,如何宣传宝水村等,这些问题的发生与解决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随着宝水旅游业的推进一步步暴露出的,夹杂在乡村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里。
第三,《宝水》还体现出地方性与现代性的融合,乔叶着重突出了河南乡村的独特魅力,她巧妙将河南的简称豫拆成文中的象城和予城,体现了对故土深切的热爱。地青萍作为宝水村的外来者,既是旁观者也是建设者,这种复杂的身份也体现出作者对当代乡村发生翻天覆地巨大变化的态度。现代性最突出地体现在乡村FvBs0wEopBn5N2IMXJIWeQ==的巨大变化中,地方性最突出地表现在语言上。虽然文中主要还是以书面语言为主,但也融入了大量的方言俚语与民间习俗,使得人物鲜活,内容生动,比如用“中不中”“恁”“扯云话”等标志性的河南方言以及敬仓神、喜丧等对应地方性。这些方言习俗,意味着一种重要的稳定性,即地方性。《宝水》以春夏秋冬季节的交替以及按二十四节气来叙述,同时证明农业在乡村的发展上永远占据着重要地位。“挖茵陈”“早春花”“种谷”“吃碾馔”等无一不透露着鲜活的农村气息,用这些农俗农规自然过渡,显示了《宝水》平淡而自然的地方性,与作者的本意契合。传统乡村的地方性与现代性融合,乡土中国在新时代的发展下所激发的活力产生了“治愈”的疗效,新气象的书写表明传统的乡村生活发生新变,所带来的不只是乡村经济的发展,还有与城市文明的对照下,对城市文明压力的弥补。
三、结语
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乡村是伦理社会,靠人情维持,而不是靠法律维系。“我”在出走以及成长之后理解了乡村的社会结构和伦理人情,一直积压在内心的矛盾得到释怀。这不仅是一场治愈失眠症之旅,更是精神的洗涤之旅。乔叶笔下的新乡村既传统稳定、和谐安宁,又能接受新变,能豁达包容离家的游子,是集自然风景、淳朴风俗于一体的“世外桃源”,突出挖掘了乡村新变下劳动人民的纯美。
自五四始,城乡对立的二元意识一直存在于现代社会。然而,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乡村已逐渐开始摆脱人们记忆中的落后与贫穷,展现出在中国式振兴下激发的勃勃生机。全面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意味着国家以巨大的勇气与担当投身乡土振兴,随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持续推进,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将乡村按城市建设模式复制。乡建要结合当地特色,以人民为中心,建设成为人民满意的故土。当前,乡土中国中的差序格局虽仍是由各个私人关系联系所构成的网络,但伴随着社会变革,乡村所展现出的活力与包容性,正成为缓解人们城市文明压力的重要场所,毕竟作为一直靠土地生活的祖祖辈辈以及子子孙孙都需要汲取土地的气息。
面对现代城市的压力以及乡村的新变,乔叶找到了“回归乡村、回归自然”的方法,表现乡村力量的生生不息,以及书写现代化新型乡村的建设,为写作乡村开辟出新的创作源泉,以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见证与参与乡建,展现了当下人们对乡村的两重情感,一是对故土生活的怀念——乡愁,二是重视乡村生活的新变——乡村振兴。在这两重情感的叠加下,一幅和谐交融的乡村图景徐徐展开。在乡土中国的书写中,乡愁并不是唯一元素,尤其新时代下的山乡巨变,为乡土经验的写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为乡土文学如何向外界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好中国形象、打造好中国名片提供了新内容新经验,也要求创作者们追求具有时代精神高度和深度的中国表达,实现乡村书写的社会价值。当下,文学创作作为意义的再生产过程,需要紧跟时代步伐,打破对传统乡村书写的固有框架,突破旧视野下的乡村概念,从中发现新变,让人从中获取新知。
作者简介:廖涛(2000—),女,湖南益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注释:
〔1〕钟媛.“新时代山乡巨变与新乡土小说”学术论坛综述[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4):215-219.
〔2〕曾攀.时代的喻象及其精神样本:论乔叶长篇小说《宝水》兼谈新乡土叙事[J].小说评论,2023(6):130-135.
〔3〕乔叶.宝水[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
〔4〕福柯.福柯说权力与话语[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