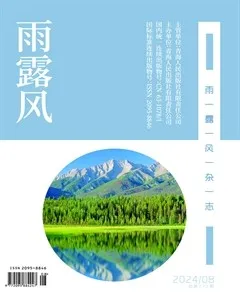拉康镜像理论视角下女性自我身份的构建
2024-10-14毕克寒汤言薇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的镜像理论认为,主体的认知和成长是在与他者的相互联系中产生的。主体只有通过“他者”这个象征性的语言介体才能成为具有社会功能的人,同时主体是他者的他者。日本白桦派作家有岛武郎的小说《一个女人》的女主角早月叶子,作者通过她与他者木部、仓地以及大他者——明治维新带来的生活环境与思想的激烈碰撞和冲突,展现了早月叶子鲜明的人物形象。文章将以雅克·拉康的镜像理论为切入点,探讨《一个女人》中叶子自我身份的追寻过程。
一、镜中本我与他者
有岛武郎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他从小接受东西方不同教育,在前往美国留学后对文学产生兴趣。他于1911年起在《白桦》杂志上发表长篇小说《一个女人》,其中清晰展现了他本人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
《一个女人》被评为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杰作,讲述了女主人公早月叶子在日本资本主义飞速发展,西方道德观、价值观迅猛冲击的时代下短暂而坎坷的一生。故事围绕着叶子与数位性格、家境迥异的男人间的周旋展开。尽管叶子可以看作自我觉醒的日本近代女性的典型,但因社会地位和道德标准的束缚,让敢于与命运抗争的她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认为,从出生6个月起到第18个月,婴儿看到自我在镜子中的形象后能够逐渐辨别出自我(镜子不是单纯指真正的镜子,而是任何反射性表面,例如母亲的脸),从而产生了模糊的自我意识,该阶段被称为镜像阶段。镜像阶段是主体的形成阶段,是主体的本质。尽管婴儿一开始仍会混淆自身形象与现实,但逐渐会认识到该形象具有自体的性质,并最终接受该形象就是自体形象。拉康便据此提出,“我们只需将镜像阶段理解为一种认可即可”[1]。
同时,拉康指出:人类自我意识并非孤立形成,而是在与他人的关系和互动中逐渐建立起来的。“镜像不只是在婴儿时期发挥作用,作为他者,他对人类的塑造贯彻始终。由于本质的缺失,他需要外在他者不断地充实和确认自己。”[2]换而言之,“人的‘自我’是在‘他者’的干预下完成的,是一个将‘他者’内化的过程”[3]。拉康还对“他者”做出区分,即“小他者”(autre / other,可用对象 a 表示) :涉及最初镜中自己的虚幻影像和父母、家庭、身边的朋友对自己的点滴影响等;和“大他者”(Autre/Other,可用对象A表示):涉及时代背景、社会需求、思想传播等大的社会环境。
二、小他者对主体叶子的影响
《一个女人》的故事叙事聚焦于女主角叶子与男性间的情感冲突,她的人物经历正与拉康理论中提出的镜像阶段相对应。而她在各个人生阶段对现实的反抗,正如婴儿目视镜中影像后做出的反应,即对“他者”行为的不认同。作为主体,对叶子个人来说,对她影响最深的两位他者分别是木部和仓地。
(一)主体叶子与小他者木部
作者将女主人公早月叶子设定为一位贵族小姐,从小在优渥的环境中成长。此时日本资本主义迅猛发展,西方道德观、价值观猛烈冲击着社会,在身为基督教妇女同盟副会长母亲的影响下,她应是较早追求自由主义的女性。木部孤筇是一名随军记者兼诗人,在一场宴会上两人初次见面,一直拒绝男子追求的叶子却对木部产生了莫名的好感。“叶子仿佛从木部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不由得激起了好奇心。”[4]5木部则对叶子一见钟情,尽管听说叶子擅长玩弄感情,但这个瘦小白净的随军记者还是开始追求叶子。频频拜访叶子家,打动了叶子家里人。他对叶子是“在易燃的心里将叶子热烈拥抱”[4]6的狂爱。叶子原是对他的追求持玩味的态度,并不打算认真交往。但随着深入了解,叶子“没想到自己竟会屡屡被木部火一般的热情所燃烧”[4]6。与此同时,叶子母亲出于嫉妒阻碍两人的感情发展,想让木部退缩。但这一行为激起了叶子的叛逆心理,她开始对木部产生了献身的念头:“叶子逐渐沉醉在自己挖成的陷阱之中,她从未体验过如此令人目眩的美妙恋情。”[4]6此时,叶子真正开始审视与木部的关系。
木部作为“他者”,对叶子自我认知的形成有极大影响。主体于镜子以及其隐喻中诞生,自我意识作为主体的基础,是相对于“他者”存在的,而“他者”则是主体的投射。反抗的叶子正处于一个充满矛盾和自我认知分裂的阶段。而当木部成为叶子战胜母亲的“战利品”,两人举行小型婚礼后,叶子逐渐在两个月的柴米油盐中看透了木部的虚伪本质。“意识到已将叶子彻底拥有了的木部,开始把自己从未在叶子面前显露过的懦弱暴露无遗,从内部看,他不过是一个毫无进取之处的,精神萎靡的男人。”[4]7在初期与木部相处时,叶子会因外界对木部战时报道的赞赏,对他的个人形象进行美化。这表明在最初面对“他者”木部时,叶子感到迷茫,缺乏个人的判断力。拉康认为,主体对特定空间的认同会产生幻想,这些幻想始于对身体的碎片化图像的感知,最终构建成一个完整的、具有调整功能的心理架构,对主体的心理成长产生影响。叶子在情感上愿意接近心中那个拥有诗人气质的木部,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让她无法触及镜中的“他者”。这种对立的唯一结果就是毁灭“他者”,切断与“他者”的关系,这也是叶子的选择。心灰意冷的叶子在生活中再次发现自己与木部微妙的相似时,她只感到讽刺与折辱。“木部对叶子的爱越是浓烈,叶子越是觉得以后的人生将百无聊赖。”[4]8叶子若要找回过去的自由无羁,木部就必须被丢弃。但因两者在外貌和性格上存在的共同点,叶子在与木部断绝关系时,也无意中摧毁了自己的一部分。在该镜像阶段中,自我渴望实现身体与精神的和谐统一。再次与木部重逢,叶子内心仍深受煎熬:“叶子感到自己在颤抖,她把激动的情绪集中到双手。”[4]8即使叶子离开了木部,木部对她的感情依然坚定不移。此时,主体的背叛与“他者”的忠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人在二等车厢无言对峙时,木部一直“执拗地盯着叶子不放”[4]9。而这一行为则被叶子认为“他仍然将自己作为女人蔑视”[4]。认识到镜前的自我与镜中反映的他者之间的联系,标志着叶子作为主体的统一和成熟。
(二)主体叶子与小他者仓地
在某种意义上,叶子与仓地的关系重蹈了她与木部的覆辙。叶子听从母亲的临终安排,乘船离开日本远嫁美国时,在轮船上遇见了事务长仓地。因一名曾被叶子玩弄感情的青年在甲板上闹事,前来处理的仓地第一次见到叶子。“一个身材魁梧的船员,见到叶子一脸无奈的样子,忽然大踏步走上前来。”[4]52仓地初次登场便化解了叶子的尴尬,可视为一种英雄救美。“然而,叶子并不只是想着该青年(结合下文,叶子也在想着仓地)。”[4]52“如同初次遇见亚当的夏娃,叶子目光灼灼地注视着这本不稀奇的男子。”[4]54 尽管没有一见钟情,但木部与仓地都带给了叶子较好的第一印象。叶子与木部的结合是对母亲阻挠的反抗,与仓地的爱情又是对素未谋面的未婚夫木村的反抗,可以看作命运的轮回。
这一情节也可以理解为一位他者通过镜像的中介,将自己的形象映射到其他他者上。叶子所感知的并非他者的具体形态,而是他者与自我认知之间的相互映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体察到,仓地对叶子的自我认同起到关键作用。叶子在镜前时,往往身旁有仓地的形象投射到镜中。叶子在船上无依无靠,渴望仓地的爱与支持,是她此时“支离破碎”的主体整合自我认识的关键一步。
仓地在开往美国的轮船上担任事务长一职,他身材魁梧,孔武有力,掌管船上大小事务。仓地外表粗犷狂野,而叶子外形的柔弱无助几乎完全在他的对立面。仓地形象也象征男性力量,暗示当时日本社会仍由男性建立与维护秩序[5]。叶子虽然追求自由,却总把希望寄托在男性身上,似乎没有考虑过依靠自己的力量求得生存。“叶子所尝受过的一切经验都让她感到遭受男性束缚的危险。然而命运是这样捉弄人,与此同时,叶子又是没有男人就一刻活不了的。”[4]98她刻意在仓地面前花枝招展地表现自己,是因为她视仓地这一他者为镜中影像,并将其视作自身形象,从而认同镜中形象。叶子的美貌与要强的性格同样深深吸引着仓地。“倒是唯有那事务长,即使偶尔与叶子打个照面,他那肆无忌惮、目中无人的眼神反而使叶子的视线退缩了。”[4]69独自登船的叶子无依无靠,与田川夫人交恶后急需靠山,便更想得到仓地的爱。叶子与木部同居两个月后开始感到排斥,而在与仓地的相处中则渴望亲近和认可。这一对比加剧了叶子在自我认同过程中的挣扎和痛苦。对叶子而言,她与木部只有物质上的交流,但“若能抓住仓地的心,往后自己就有精神依托了”[4]111。所以她在船上组建自己的势力,与人为善,得到了仓地的青睐,两人最终开始了不伦之恋。对叶子来说,真正的突破是在轮船停靠美国西雅图后,她反抗母亲安排的婚约,留在船上不愿登陆。当面临分离时,她才意识到她作为个人对仓地的过度依恋。“想到她和木部共同生活不到两个月,而和仓地,则像是离开一天也受不了。”[4]114这一刻,叶子心中对他者仓地的痴迷达到顶峰。
三、大他者对主体叶子的影响
自我感知并非自动获得的。个体的自我概念中融入了社会因素,个人的成长深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先行研究中,有“小说中叶子的死主要不是她个人的过失,也有社会的责任”这一观点。小说中的人物都受到现实社会环境、思想变迁以及战争的影响。《一个女人》以西方思潮激荡、社会环境变革为背景,描绘了一个原生家庭优渥的日本女性短暂而坎坷的一生。其中展现的日本社会环境变化与西方思想的传播,对情节发展起着无可替代的推进作用。
(一)主体叶子与大他者——西方思想
小说的故事背景设定在明治维新后,此时的日本社会思潮广受西方影响。民主思想的传入促进了近代日本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在国家、民族、个人身份重构的历史背景下,近代日本女性也开始重新对自我身份进行认定,对自我主体价值进行探索追求。对叶子而言,最初是在家庭中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叶子的母亲信奉基督教,并担任基督教妇女同盟的副会长,为基督教妇女同盟事业奔走,作为长女的叶子深受母亲的影响。进入的学校由美国人担任校长,学生时代她的一举一动引领校内的时尚风潮。“十五岁的时候,用卡扣代替纽襷束系裙子,使之在女学生中风靡一时。”[4]4日本明治时代中期,尽管政策发生了变化,但文化和思想领域并没有经历彻底的革新,封建思想和传统观念仍然深深植根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女性,她们一面受益于文明的开化,接受了中等甚至高等教育,形成了“自由、民主、独立”的自我意识;但另一面,在改革不彻底的社会环境中,她们也体验到了困惑、孤独、不安和恐惧。在主体面对他者时,大他者(思想)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这种影响通常在无意识层面上发生,且非常强烈。所以说无意识是大他者话语的体现。
小说不仅描述男女间复杂的情感关系,也反映主体如何被传统思想限制。叶子在与木部关系更进一步后,内心仍不将他视为自己的爱人,因为木部内在虚伪而孱弱。仓地对待叶子亦是如此。虽说他在船上与叶子陷入热恋,甚至在返回日本后宁愿丢掉工作也要和叶子在一起,但仓地也只是在意叶子的身份、容貌。最后,仓地又选择畏罪潜逃,杳无音讯,叶子失去了精神寄托和经济支柱。这一个人选择,是外在思想融入自我意识的结果。
在成长过程中,叶子作为主体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大他者的潜在影响,她难以摆脱传统伦理和教化等抽象概念的束缚。思想这一大他者是无意识秩序的具体体现者,它作为中介参与到镜像中,将“真正”的主体带入语言的领域。拉康认为,由于镜像整体形象的介入,主体经历了某种变容。自我身份是在镜像阶段建立起来的,当人类进入语言的范畴之后,自我的身份就会由他者的语言确立。“为了被他人承认,我只有根据将是者来说出已是者。为了得到他,我用一个名字来呼唤他,而为了回答我,他必须接受或者拒绝这个名字,我在语言中确认自己,但只有像一个客体那样消失在语言中才能做到。”[6]人之所以能够形成自我,是因为自我被嵌入大他者的语言之中,成为大他者的客体,而非与之构成简单的对立矛盾。因此,个体与大他者并非处于纯粹的对立状态。
(二)主体叶子与大他者——生活环境
社会环境的极速发展,最初让这一时代的日本女性有些无所适从。生活上的变化让人们不再互相坦诚,至亲至爱之间渐生隔阂,人性中的美好似乎被社会环境的极速变化给摧毁了。叶子从日本离开,在船上的15天她更换了生活环境,在这样一艘有着日美两国船员的轮船上,她一开始是无所适从的。“她像其他人一样凭依着栏杆,让寂静的春雨打在脸上,眺望着码头方向,可她的眼中空空如也。相反地,仿佛在眼睛与大脑之间,亲近的人疏远的人都无端地匆匆闪现,各自亮出给人最深印象的姿势然后消失。”[4]52为保全自己,叶子开始在船上拉帮结派,与田川夫人抗衡。“厌倦了单调的海上旅行,渴望巨大刺激的男性们不知不觉以两位女性为中心,旋涡一样围着她俩转。田川夫人和叶子之间的暗斗表面上不着任何痕迹,可那却自然而然地给男性们以刺激。即便是平静水面上因偶然吹过的微风而泛起的细小波纹,在船上也是件了不起的事情。男性们似乎无端地感到紧张和乐趣。”[4]83短暂的15天深刻改变了叶子的人生轨迹。某种程度上,小他者塑造了叶子作为主体的身份认同;而在更深层次上,大他者则对叶子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产生了影响。母亲离世、环境变化迫使叶子离开故乡。这些改变驱使叶子寻求新的依靠,最终与仓地产生了感情。由此可见,主体是在个人成长过程中由大他者所塑造出来的,是后天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对叶子来说,大他者虽是外部的存在,却是至关重要的事物。在很大程度上,主体叶子的言行是受他者控制的。
她对木部和仓地这两位他者的态度是由社会制度、环境、体制这个大他者控制的,尽管她个人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自我受大他者牵制的事实。如果能够意识到的被认同为主体,而意识不到的由是成为更加隐秘的无意识,是大他者的隐形和侵占性力量[7]。叶子在经历了家庭的一系列变故之后,踏上前往美国的轮船。船上的经历最终成为她个人认识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比较未婚夫木村和新欢仓地,经历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之后,她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叶子总想把一个男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恰如猫儿戏鼠一样,她从不想放弃任意摆弄男子的那种乐趣。”[4]136她的选择便是离开木村所在的美国,随仓地一同返回日本。可见个人认识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多么地深远。
拉康认为,自我认识是通过与他人的相互参照来实现的,“我”与他者互为他者。这一过程中,人只能在他者身上找到自我认同,个人必须通过这个媒介来实现自我的构建。同时,“我”不可避免地受到大他者的强制性影响,这种影响将外在因素转化为自我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小说中的叶子和木部,以及叶子和仓地都是通过他者视角看待自己的。如果没有他者的形象,他们就难以形成自我认知。在社会风云变幻的背景下,叶子的自我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一种隐性暴力的侵入,不属于个人的社会因素也在逐渐内化为自我。通过审视叶子的人生,可以深刻体会到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的动荡、思想的剧烈变革以及日本女性经历的苦难。叶子的种种行为塑造着她的身份认同,而这一身份认同只有在特定的社会环境里才会被赋予意义。
四、不完美带来的启示
《一个女人》中的女主人公早月叶子,是日本明治维新后自我解放、自我建构的女性形象代表。她对异性及婚姻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日本女性自我意识的成长过程,从该人物的塑造中,读者也可以发掘出作家有岛武郎身为男性对女性群体追求独立意识行为的关怀和支持,他鼓励新时代的女性为爱与理想去奋斗,以新的身份去生活。
虽然叶子的人物形象并不完美,但也正是这份不完美才更为真实地反映出时代女性的局限性。毕竟事物发展的过程是螺旋式的上升,成功的硕果总需要经历挫折方能采摘。前人的经历启发着后代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需要从人格独立开始,人需要在与他者的对照中寻求真正的自我,从而实现个人价值。
注释:
〔1〕埃文斯.拉康精神分析介绍性辞典[M].李新雨,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2〕李幸,姚国军.在“他者”中寻找真实的自我——从拉康的镜像理论看《海上钢琴师》和《楚门的世界》[J].电影评介,2014(13):46-47.
〔3〕冯美.成长中的“他者”与言说主体之间的构建关系探析——以拉康镜像理论看《我11》中主人公的自我确立[J].东南传播,2013(8):98-100.
〔4〕有岛武郎.一个女人[M].商雨红等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
〔5〕梁明霞.论西方女性解放论对日本明治思想界的影响[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S2):98-102.
〔6〕吴琼.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7〕王小燕.从拉康的镜像理论看主体的成长——解读《追风筝的人》[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5(3):9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