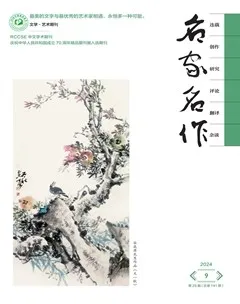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真实论视角下的长篇小说《兄弟》
2024-10-12马翔
[摘 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以历史真实作为艺术创作的底色,在整体符合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展开艺术虚构和艺术想象。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以历史真实作为艺术真实的客观标准,客观呈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揭示了人物与时代的真实关系。同时,余华进一步追求艺术真实的营构,通过荒诞的情节设计和夸张的人物塑造以及狂欢化的语言表达,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中找到平衡。
[关 键 词] 马克思主义文艺真实论;余华;《兄弟》
1859年4月到5月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文艺学、美学进行长期探讨后致信斐迪南·拉萨尔,深入评价了他的历史剧。这两封信集中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看法,从而构成马克思主义文艺真实论的重要内容。从历史走到今天,人们从未停止过对“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这组关系的探讨,比如余华于2005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兄弟》,甫一出版便受到了读者和学界的广泛热议,批评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叙事是否过于荒诞、情节是否失真等相关问题上。本文试回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与艺术的相关讨论上,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真实论的视角重新审视文本,在细读背后考察余华对这组文艺关系的认识与处理。
一、历史真实作为“底色”的《兄弟》
19世纪50年代末,拉萨尔创作的五幕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主要讲述了骑士阶层的代表济金根试图依靠个人力量完成祖国统一,结果兵败致死的悲剧。由于故事情节、人物行动都是德国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所以剧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6世纪20年代德国革命的现实,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读了这部悲剧后,敏锐地发现拉萨尔在创作上的局限:拉萨尔在剧中歪曲历史,有意避开平民派和农民阶级的革命运动,极力美化骑士暴动。马克思切中要害地指出悲剧的根源在于济金根只是按骑士的方式发动叛乱而没有重视城市和农民,一旦诉诸城市和农民,那“就等于否定骑士制度的阶级”[1]170。拉萨尔不仅不肯触及骑士阶级利益,而且不愿暴露贵族的盲从与英雄主义,这就是一种不尊重历史真实的表现。因此马克思为他开出了“药方”:“革命中的这些贵族代表——在他们的统一和自由的口号后面一直还隐藏着旧日的皇权和强权的梦想——不应当像在你的剧本中那样占去全部注意力,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这样,你就能够在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1]170-171拉萨尔认为自己只是想把悲剧的根源归结为“骑士个人策略”的失败,对马克思的意见不以为然。随后恩格斯也切中肯綮地批评拉萨尔把农民运动放到了次要位置,“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您忽略了这一因素,把这个悲剧性的冲突缩小到相当有限的范围之内”[1]177,从而艺术真实也大打折扣,“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根据我对戏剧的这种看法,介绍那时的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会提供完全不同的材料使剧本生动起来,会给在前台表演的贵族的国民运动提供一个十分宝贵的背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使这个运动本身显出本来的面目。”[1]176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张的是以历史真实作为艺术创作的底色。所谓历史真实,是指文艺能生动表现特定历史时期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并能真实反映社会与人物的关系。优秀的文学文本要以历史真实为基石,在遵循其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再进行审美意蕴上的建构,保持文学内核的不变,使文本内外和谐,以此达到艺术真实。“艺术真实的评价标准只能来自其所依据的生活,换句话说,艺术真实的评价标准,只能是生活真实。”[2]17这在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中能得到充分体现。
“我可以写现实了,而且是不躲闪,迎上去,这对我按理说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兄弟》这部小说为什么对我意义重大,因为我能够对现实发言,正面去写这个变化中的时代,把人物的命运作为主线,把时代和他们联系起来,他们的命运都是这个时代造成的。”[3]6《兄弟》从一开始就将叙事的目标对准了历史本身,把我们带回了历史现场,呈现两个客观的时间段: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浮躁纵欲、伦理颠覆。那么,文本究竟多大程度上表现出了历史真实呢?
首先,这种历史真实表现在对典型环境的呈现,即对旧历史与新历史的客观叙述上。当代文学对20世纪60年代的认识经历了从个体创伤的申诉到民族国家命运的理性反思阶段,余华将其延伸到了本体意义上的哲学层面。在《兄弟》上部里,就是对精神狂热与本能压抑的双重否定。“个人在群体影响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突然爆发。”[4]379这种精神狂热的结果就是人物命运被时代所左右。余华聚焦时代中的个体,具体清晰地表达作家对命运的感受与认识。和五四时期鲁迅的时代书写一样,今天我们仍然能在余华所反映的时代话语里找到共鸣。改革开放后,《兄弟》下部把书写的焦点直接对准现实,全面展现时代的面貌与变化。“想象应该有着现实的依据,或者说想象应产生事实,否则就只是臆造和谎言。”[5]17余华的想象在现实生活中都是有迹可循的,这使得他的书写更加具有真实感。在余华看来,《兄弟》所反映的历史真实就是人对私欲的追求和满足,这既是人性的弱点,也是旧时代的悲剧。余华用力透纸背的书写为生存在现代化巨幕下的人类“问诊”,体现出一个作家的艺术匠心。
其次,这种历史真实还表现在对典型人物的塑造及其人物与时代关系的反映上。“我只是一位作家,我的兴趣和责任是要求自己写出真正的人,确切地说是真正的中国人。”[6]36在小说中,主人公李光头的形象是对专制禁欲社会的反叛,余华借他偷看屁股的丑陋情节反映时代中过度压抑本能后的众生狂欢。李光头如一面镜子照出了刘镇群众内心的变态与畸形。通过人物形象的真实再现,余华否定了旧时代下的情感枷锁,抗议被现实麻醉了的个体以及“人”的主体意志的缺乏。同时,余华没有停留在人性真实的层面,而是多角度立体塑造“圆形人物”,提供了另一种人物塑造方案:人性中最自然的爱经受暴力与罪恶后反而历久弥坚。在文本的“血泪”中,我们依然能找到人性的温情一面:宋凡平用美丽的谎言保护两个孩子免受伤害、李兰对宋凡平的爱情刻骨铭心……余华对人性的深刻体悟进一步增强了“历史真实”的反思意味。
《兄弟》以史诗般的气度再现逼真的生活具象,以此形成戏剧张力,融汇时代的诸般痕迹,弹奏个体命运的时代弦音,透视历史的本质。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1]544作家要想取得艺术真实的效果,就必须对现实有深刻的体悟,以一种内在于时代的方式去呈现历史真实,反映时代的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疏离日常经验与现实逻辑,到当下亲近生活、记录历史,转型后的余华逐步缩短与时代的距离,“《兄弟》好就好在它跟这个时代没有距离。”[7]71
二、“虚构”作为直击历史本质的一种方法
虽然《弗兰茨 ·冯·济金根》存在歪曲历史、掩盖现实的问题,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对拉萨尔的创作全盘否定,而是本着“美学和历史”的批评标准,肯定了剧本的审美价值与艺术贡献。《弗兰茨 ·冯·济金根》以其精致的结构和情节设定展开艺术虚构,强烈触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恩格斯指出:“由于现在到处都缺乏美的文学,我难得读到这类作品。”[1]172马克思更是高度评价《弗兰茨 ·冯·济金根》:“它比任何现代德国剧本都高明。”[1]169拉萨尔不仅大胆地想象了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弗兰茨领导的农民运动,而且赋予弗兰茨鲜明的人物个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方面是予以认可的:“对情节的巧妙安排和剧本从头到尾的戏剧性使我惊叹不已。”[1]173恩格斯甚至不否认拉萨尔把骑士济金根看作是打算解放农民的,还帮他“虚构”了将农民运动和平民运动写入戏剧的方法:“至少还有十种同样好的或者更好的其他方法。”[1]177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从个别的、细小的虚构历史去批判拉萨尔,而是对他没有通过艺术虚构与想象来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表示遗憾。
由此可见,在整体符合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是允许艺术虚构和艺术想象的,他们正确把握了艺术真实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进行想象和虚构,而是能否找到想象和虚构的平衡点,来勾连历史的核心要义,揭示人性的客观发展规律。
所谓艺术真实,就是作家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用合理的虚构想象来加工和创造历史。如同厨师精心烹饪美食,面对相同的食材,加工的方式和火候的把握不同,出品的口味则各不一样。由艺术真实加工过的文本,必然追求内涵的丰富、主题的鲜明,更重要的是透过文本看到更深远的现实本质。拉萨尔的创作忽略了这一点追求。而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虽然文本存在荒诞、变形等内容,但是通过魔幻现实主义这种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陌生化艺术处理,揭示了拉丁美洲政治是如何走向荒谬、无理和无休止的悲剧实质,具有很强的艺术真实性。回到余华的《兄弟》,也能看出作家在表现艺术真实上的用心良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体现在情节设计和人物塑造上。“文学的真实是不能用现实生活的尺度去衡量的,它的真实里还包括了想象、梦境和欲望。”[8]106在写作中,艺术真实将现实尺度夸张和放大:少年李光头靠摩擦电线杆发泄性欲、群众对屁股的好奇与狂欢等情节都以超出读者惯常经验的方式呈现,阅读的庄重感被消解。无怪乎有学者评价道: “唯其夸大,才能将禁欲主义的罪恶触目惊心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唯其极端,也才能使后来者更加认清那场禁欲主义的危害。”[9]67余华用夸张、变形、转喻等手段,书写荒诞世界,安排尴尬情节,来表现虚构的“真实”,这些虚构情节完成了个性化的人物塑造和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情节布局,使得小说具有寓言性质,这种艺术真实的完成,也就是作家批判性书写的完成。
其次,体现在语言艺术上。文本随处可见“屌气味”“爽!爽!爽!”这类语言,有人批判小说的语言是满纸狂言、直白暴露,沉迷于“叙事的快感”而走向了粗俗。这种看法未免偏颇,《兄弟》的“粗俗”是真正文学意义上的“粗俗”,具有艺术真实的合法性。这种被叙述统治了自我的“狂欢化语言”,充满了民间风味,毫不回避市井用词,直白浅明,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叙述者在文本中虽然退场了,但隐含作者并未退场,激情而夸张的语言背后是对当下社会浮躁纵欲的批判。余华响应文本人物的性格要求,用一种“用别人的语言将别人的事告诉别人”的叙述方式,让语言跟着人物走,让虚构人物走出自己的道路,发掘人性的复杂与真实。
“我想所有的作家在写作时都在努力寻找真实, 但是每一位作家对真实的把握都是不一样的”[10]89。余华把握“历史真实”的方式是构建文学性的“艺术真实”,用想象和虚构有效地回避现实的局限而走入小说内部,让情感、欲望得到真实的表达,因而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与冲击力。
三、“紧张感”:马克思主义文艺真实论的张力生成机制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文艺真实论中“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这组关系可以阐释为:现实生活是艺术的来源,因此文艺只有通过历史真实才能达到艺术真实,历史真实是艺术真实的客观标准;艺术真实是历史真实的另一种存在形态,是更好表现历史真实的一种方式;符合历史真实的文学可能不一定是艺术真实的,但符合艺术真实的文学一定是满足历史真实的,所以历史真实是艺术真实的必要非充分条件。这种辩证关系恰恰能赋予文学足够的张力。
对余华和他的《兄弟》而言,充分体现了这种“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关系。“长期以来,我的作品都是出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我沉湎于想象之中,又被现实紧紧控制,我明确感受着自我的分裂。”[11]7余华就是属于这种“自我分裂”的作家,一直保持所谓的“紧张感”,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间追求平衡。虽然我们把余华的创作阶段分为前期追求形式创新与内容虚构的“先锋文学”,到转型后回归传统聚焦历史生活的“新写实小说”,但我们可以发现他从未放弃将二者作有机统一的努力:即使是极具先锋艺术感的《现实一种》《古典爱情》《鲜血梅花》等作品,也指向了生活的本相;即使是极具历史和现实生活气息的《活着》《第七天》《文城》,也在着力追求艺术的表现力。
四、结束语
余华曾坦言:“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兄弟》这部作品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真实论的价值意蕴,说明了余华文学思考与尝试的正确方向,也开辟了新的文学图景。正如有学者所说:“无论是面对历史和现实的艺术观念,还是面对叙事内部的表达能力,他都在试图朝着新的目标挺进。”[12]104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赵炎秋.“艺术真实”辨析[J].中国文学研究,2008(3):14-17,21.
[3]余华,张英.余华:《兄弟》这十年[J].作家,2005(11):2-11.
[4][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79.
[5]余华.强劲的想象产生事实[J].作家,1996(2):14-18.
[6]叶立文,余华.访谈:叙述的力量:余华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2(4):36-40.
[7]张新颖,刘志荣.“内在于”时代的实感经验及其“冒犯”性:谈《兄弟》触及的一些基本问题[J].文艺争鸣,2007(2):70-81.
[8]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106.
[9]栾梅健.《兄弟》:一部活生生的现实力作[J].文艺争鸣,2007(2):65-69.
[10]余华,张清华.“混乱”与我们时代的美学[J].上海文学,2007(3):83-89.
[11]余华.作家与现实[J].作家,1997(7):6-8.
[12]洪治纲.在裂变中裂变:论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J].当代作家评论,2006(4):96-104.
作者单位: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作者简介:马翔(1992—),男,汉族,湖南邵阳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