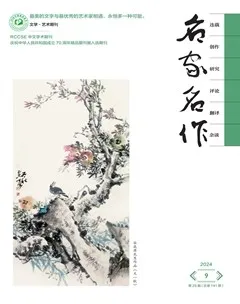以春天的名义回到心灵的故乡
2024-10-12王鹰
又是一年春来临。春江水暖、凛冬散尽,春天是温暖的季节;草长莺飞、柳暗花明,春天是希望的季节;桃之夭夭、万紫千红,春天是美丽的季节。歌咏春天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当春风拂面、春雨如酥、春山如黛,大自然用各种方式撩拨诗人的情思时,诗歌就苏醒和茂盛了起来,汇成心灵的万壑千声,冲击着现实世界的巉岩峭壁,发出清越的回响。我想,每一个诗人的笔下都曾绽放过春天的花朵。
王立世也不例外。他歌咏春天的诗篇有37首之多。可以想象,诗人的生命年轮是怎样随着春天律动啊!那些深藏在心里的柔情和梦想,如临水照花,悄然定格在矮纸斜行上,让我们窥见诗人心中千娇百媚的春天。
一、丰富的意象拓宽了王立世春天诗篇的广度
春天的万物都是美的。于是,流水、小鸟、野草、桃花、南山、原野、春风等都以意象的方式诗化地呈现在王立世的诗歌中,表现了诗人细腻敏感的心灵悸动。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诗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也在变化,单就歌咏春天的诗歌来说,主题也呈现出多样性:或对爱情的礼赞,或对故园的怀念,或对生存的思考,或对人格的写照,或对黑暗的讥讽,或对希望的期盼。他的诗歌在形式上是美的,丰富的意象是千姿百态的大自然的投射;他的诗歌在内涵上是真的,上下求索荟萃了人类心灵探索的集体共鸣。
(一)春天是甜蜜的爱情
《给你寄去一个春天》
亲爱的,我在冬天给你写信
害怕一些无关紧要的人来敲门
鲁莽地打断我,让柔情的笔尖停顿
我想把春天写进信里,装进信封,邮寄给你
你一打开
一行归雁飞过天空
无数花朵绽放在枝头
小河又流过你的故乡
这是一首爱情诗。全诗柔婉深情,构思新颖,诗意丰盈。首先诗人选取了一个很好的立足点——在冬天写春天。冬天给心爱的人写信,一定是饱含了希望和思念。但是诗人没有直接告白,而是宕开笔墨,“害怕一些无关紧要的人来敲门/鲁莽地打断我/让柔情的笔尖停顿”,原来是害怕旁人打扰而不能凝聚心神地给爱人写信,这样写曲折开阖、远近有致,更加突出了专注的深情,又很自然地铺衬反文,让想象的空间顺其自然地归属、结合,真是神来之笔!那么信里写了些什么呢?诗人把千言万语凝练在“春天”这个意象里,给人以无限遐想,化实为虚,化琐碎为典雅。诗人想象爱人收到信的情景“归雁飞过天空”“花朵绽放枝头”“小河流过故乡”,三个不同的意象连绵呈现,既多层次描写春景,也是抒情者心境的反映。物我交融,寓情于景,赋予感情可以触摸的外在形态,写实和象征融为一体,心灵与自然巧妙地契合。而且诗人站在自己的角度想象对方,这样推己及人的写法深得古人精髓。李商隐的“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就是经典的例子。从这里可以看出诗人丰富的文学修养与他对中国古典诗歌意境和表现手法的继承。
(二)春天是生机勃勃的希望
《春风》
透明
但不是一尘不染
吹过杨柳
绿色依依
吹过花园
姹紫嫣红
吹过夜晚
一片漆黑
吹过鸟的身体
变得又暖又轻
这首诗采用了展开式的结构。第一节写对春天的总结:“透明/但不是一尘不染。”春天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万物悄然改变,但又不是不动声色。前面用三个视觉感受来描写诗人眼里生机盎然的春天,三个客观意象连绵往复,最后一节转化成诗人想象中的触觉感受,以“鸟的身体变得温暖”寓意春天的温暖和柔情,以“鸟的身体变得轻盈”寓意人生可以飞得更高。诗人的诗歌情感是丰富的,既有冷静的思辨和观察,又有喷薄欲出的激情。诗人用动态的诗歌语言定格了春天的美。这种美是旺盛的生命力悄悄萌动的美,是为了怒放而紧闭、为了展开而沉默的美。这首诗的客观意象和主观感受层层关联,逐渐向深广处拓展,到结尾处豁然开朗,揭示出深刻的情感和寓意,从而达到诗意的高潮。
(三)春天是缱绻的乡愁
《春天的村庄》
这个春天
带你到我的村庄
不谈情说爱
只谈草色、归雁、炊烟、涛声
还有劈柴、饮马之类的农事
让你亲眼看看
我家中那棵老枣树
又吐出新绿,开出小花
那头没牙的老牛
还在田里低头拉犁
让你体味一下
山坡上散漫的羊群
就像我们丢失的童心
听一听
晚归的牧童
又一次吹响朦胧的黄昏
谈谈我瘦弱的母亲
脸上抹不掉的谦卑
谈谈我沉默的父亲
海纳百川的胸怀
我的村庄
我的亲人
思乡恋亲是人间最普遍的情感之一。古往今来,思乡情感在文学领域是一个永恒的“母题”,而春天又和乡愁有着紧密的联系。春天给人以温暖、舒适、自由生长的感觉,这种感觉犹如回到婴儿时期母亲温暖的怀抱里,回到孩提时期自由快乐的时光里,所以人们才会在春天对故乡和家人的思念愈发强烈。这首诗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春日的田园画,画中是故乡的景致和农事,还有诗人深深眷恋的父母。乡村是古老的,但是蕴含着生机:多年的老枣树吐出新绿、没牙的老牛还在低头拉犁,吹响黄昏的牧童是故乡的未来。诗歌呈现给我们的还是一曲动人的思乡谣。故乡的美不仅有清澈的、纯粹的风光,还有谦卑、沉默的父母。他们是故乡的魂,是诗人精神的源头。诗人用白描式的写法、恬淡平和的语调倾情抒写着对故乡的深深眷恋和精神追寻。诗歌充满生活气息,语浅情深,冲和平淡,却是绚烂之极。
(四)春天是心灵的自适
《我的城在春天沦陷》
我爱卑微的蚂蚁
只搬运粮食,不搬弄是非
我不喜欢金戈铁马
也不喜欢断壁残垣
红尘中,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
花前赏月,月下饮酒
还有前朝的几个女子弹着琵琶
我的城在春天沦陷
窗前的鸟鸣声声慢
门前的柳树垂头丧气
我没有长吁短叹
遗恨的是那些花们
也不知电闪雷鸣、风雨欲来
还在争奇斗艳,不知开给谁看
这是一首咏志诗。“诗言志,歌咏言。”在王立世笔下,春天不仅是浪漫主义的吟唱,也可以是现实主义的批判。起句“我爱卑微的蚂蚁”点明主旨,抒发志向。“卑微的蚂蚁”象征着底层的劳动人民,我爱他们是因为他们忠于辛苦劳作,从不钩心斗角。诗人出身底层,虽然身在官场、咋笔为吏,但难能可贵的是始终保持初心,不汲汲于富贵,不媚俗求荣。 “金戈铁马”“断壁残垣”的残酷和“只搬弄粮食,不搬弄是非”的淳朴形成鲜明的对比,诗人的爱憎和立场旗帜鲜明。承句 “花前赏月,月下饮酒”化自李白的“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诗歌传承了古典诗歌的意境,又更加凝练,构筑了一个自得其乐的世外境界,宁肯孤独地自己陶醉,也不愿同流合污,饱含深深的不屑与悲悯之情。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我的城在春天沦陷”,这里的“春天”既可能是时间上的实指,也是隐喻势力强大的群小之徒。 “沦陷”“声声慢”“垂头丧气”这些词语暗示了诗人的处境和内心的情绪。虽然遭受误解、挫折和打击,但是他没有沉浸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中感伤、颓废,而是志向不改,坦然接受生存境遇的残缺。“我没有长吁短叹”自然地承上启下,拉开了与现实困境的距离,以旁观者的姿态对现实的丑态进行冷静客观的嘲讽,使诗歌具有反讽的意味。这首诗起承转合、层层推进,人性的善恶对比、理想和命运的交织构成了诗歌丰富的肌理。古典唯美的意象、内敛冷峻的感情、古典语言和现代体验之间的结合,扩展了诗歌的张力。
二、童话的意境提炼了王立世春天诗篇的纯度
王立世笔下的春天,无论写爱情、家园还是理想,都是纯净美好的。“树想鸟的时候/春天就来了”(《春天》),“如果缺爱/春天也会长出荒草”(《如果》),“有人想钓小虾/有人想钓大鱼/柳宗元想钓雪/我想钓春天”(《钓》),“我在桃花源里种菊/你在天上种星星/我们种的都是爱情/因为你想在午后采菊/我想在夜晚看星星”(《菊与星》),这些诗歌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意象的堆砌,哲理中有情思,抒情中有寓意,如童年的歌谣一般简单明快、清新自然,轻盈得如同童年时追逐的蝴蝶,在花丛中翩飞。即使是反讽现实的,也是尽量冷抒情,内敛、引而不发,将强烈的情绪控制在诗歌的意象和意象变化中,仿佛初恋的情愫,纯美、干净,有时候还带着一缕淡淡的怅惘,又像春花的甜蜜带着苦味的幽芳。王立世以春天为主题的诗歌创作,是诗人人格的不自觉提炼,是心灵的无意识祛魅。诗人用爱、希望、温暖来滋润心灵,进行诗意化的书写。春天是诗人编织的童话,是一尘不染的精神家园。
三、精神的探索拓深了王立世春天诗篇的深度
无论王立世诗歌中春天的意象如何变化,其所有的意象本质上都指向一个共同的内涵——精神的还乡。
弗洛伊德把人格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我们的“本心”,是阅尽千帆后,内心仍然充斥着渴望,拥有不熄的热情。超我是社会化的理想目标,自我则是二者冲突时的调节者。在现实的生存境遇中,本我和超我不断纠缠冲突,使得诗人内心深处有着隐秘的痛苦和无奈,于是诗歌成为心灵慰藉和涵养内心的出口。当春天敲开严冬的裂缝,涤荡天地,万物萌发,像母亲一样和诗人拥抱时,诗人因景生情,灵魂深处的呐喊像种子一样破土而出,理想主义的春风吹拂,内心的本我和超我合二为一。正如《夹缝里的花》写的那样:“缺水、缺氧、缺光/说开就开/低着头,像一个/不多说话的君子/给这个狭小的世界/留下美和香/凋谢时/也没有一点缺憾。”从这首诗里,我们读出了诗人的自我隐喻。“说开就开”暗示着诗人的蜕变与成长。现实艰难的生存处境并没有磨灭诗人的理想追求,春天激发了诗人更热烈地叩问人生、诗意摆渡的精神追寻。爱情是甜蜜的、纯净的,故乡是温暖的、厚重的,希望是美好的、清新的,这些情感都能让人打开心防,返璞归真,像孩童一样纯粹和真挚,精神和肉体才能融为一体。所以王立世歌咏春天的诗歌,或明媚或凄清,或深情或悲悯,但是整个诗歌的底色都是温暖的。无论是歌咏爱情、故乡还是希望,都是诗人在寻求赤子之心的安顿,丰富的春天意象和寻求精神家园的内涵互为表里。王立世的诗歌中,常常无意识地带着寻找心灵之乡的印记。例如“你睁开眼/深渊之美如梦初醒/窄小的世界/给我带来穿越之快乐/我生命又一次抵达/犹如春风拂柳,细雨润物/让你闭目想象/生命的万千气象。”(《春之舞》) “像一颗青涩的杏/生长在岁月葱绿的枝头/温顺地吸吮着日月精华/一天天变得红润光滑绵软香甜/那时的我一定是一个懵懂少年/在树下贪玩忘了回家/偶尔望见树上你这颗耀眼的果子/一定想爬到树上摘下来/事实上,我只是遐想了好多年。”(《十六岁的春天》)诗人用一生来寻找精神的桃花源。海德格尔曾说过:“诗人的天职就是还乡”。诗人一生都在寻找,最后才发现:灵魂出发的地方,就是心灵的归宿。而诗歌就是这种精神探索的诗意化书写。
踏着春天的鼓点,跟随诗人的引领,在美好的文字里拨草寻径,让心灵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这是所有心存美好的人们的共同心声,也是王立世诗歌的魅力所在。
作者简介:王鹰(1973—),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古典文学、近代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