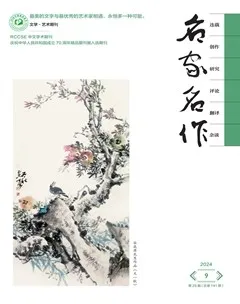中西诗歌孤独心态之比较
2024-10-12杨艺驰
[摘 要] 孤独,是人生的常态。古今中外不乏对“孤独”情感的描写与表达,而相较于小说、戏剧等晚生的文学体裁而言,用诗歌表达“孤独”是中外早期文人墨客的重要手段。其中,唐代诗人柳宗元与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诗歌中有许多都以孤独为创作基调与主题,但同时他们的作品在表达孤独时也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文化背景。以柳宗元的《江雪》和华兹华斯的《我好似一朵流云独自漫游》为例,通过分析两位诗人的意象运用和情感表达,以揭示他们对孤独的理解和诗歌创作的不同之处。
[关 键 词] 中西诗歌;孤独;柳宗元;华兹华斯
一、引言
柳宗元和华兹华斯都与“孤独”有着不解之缘。早期的柳宗元积极参政、心怀远大理想与抱负,一心想要闯出一番天地;但中期受到反动势力的反对,被贬到永州任司马,过着被管制、软禁的拘禁生活,这次贬谪让他从天堂跌入了地狱,前途断送、身体欠佳、环境恶劣,这些都使他内心苦闷、深感绝望。从此之后,“孤独”成为柳宗元的常态,他的重心也转移到思想和文学创作领域,寄情山水、种植花草,但仕途的抱负始终不能释怀,也正因如此,他创作了《江雪》这首诗。而华兹华斯的孤独有其特殊原因。首先,华兹华斯所处的时代正是世界范围内动荡不安的年代,他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等诸多变革;其次,他早年的叛逆思想和晚年的保守思想相矛盾,使他不被世俗大众所接受;最后,作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理论的创始人,其诗歌理论动摇了英国古典主义诗学的统治,这使他的作品在当时不被接受,长期饱受批评与职责……这些都造就了华兹华斯的孤独。虽然都是“孤独”,但柳宗元与华兹华斯的“孤独”略有不同,本文将从两首代表作的意象、情感角度出发,分析中西诗歌中孤独心态的不同。
二、意象的简洁与生动
意象是事物经过概念化在脑中呈现出的形象,是审美主题对外界物象所形成的认知。诗人托物言志,用客观事物反映自己的主观认识,因此诗歌中的意象蕴含着诗人特定的思想感情,是诗人情感的载体。古今中外的诗人墨客都善用意象,让我们来共同领略柳宗元与华兹华斯笔下意象的不同。
《江雪》是一首五言绝句,短短20字,描写的画面极为简单,不过是一个老渔夫在江面上钓鱼;但诗人却用了山、鸟、人、舟、翁、江、雪七个意象,使得原本简单的画面瞬间丰满了起来。
首先,诗人用一半的篇幅去描绘整幅画面的背景,将其尽量扩大,让读者置身于无边的群山之中,感受到自我的渺小,突出描写的对象。山,往往象征着坚韧与高远,但在《江雪》中,连绵不绝的群山却以“千”“万”的广阔,反衬出人物的孤寂与渺小。水,作为生命的源泉,在这里化作了平静的江面,它不仅承载着老渔翁的孤独身影,也映射出诗人内心的宁静与超然。“千”“万”两个数词,也突出下文的“孤”和“独”,形成了强大的反衬效果:在广阔无垠的群山之间,没有鸟儿飞翔、没有人的踪影,只有一位孤独的老人在平静的江面上垂钓。
其次,动词“绝”“灭”的运用将动态景象转化为静态景象,在群山之中本该有鸟儿飞过、行人走过,但在这两个动词的作用下,画面变得极端安静、寂静、幽静,整个画面中仿佛只有老渔翁是有生命力的、是鲜活的,其余的都死气沉沉。“绝”与“灭”二字,不仅仅是物理层面上的消失,更是心灵上的一种隔绝与遗世独立。鸟儿的飞绝,暗喻了世俗纷扰的远离;人踪的消失,则强化了这种与世隔绝的静谧与孤独感。
再次,如果我们把整首诗想象成拍摄一个短片,在拍摄完远处的景色之后,拉近镜头拍摄近景中的渔翁垂钓;但诗人并没有如此,反倒将老渔翁放在了大江之上,使其变得模糊与可望而不可即,形成了遥远的距离感,更凸显了诗人想要脱离世俗的欲望与情感。一叶扁舟,在浩瀚的江面上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却又是老渔翁精神的寄托与自由的象征。老渔翁的形象不仅是自然与人的和谐共存,更是诗人内心追求独立、超然物外精神的写照。
最后,《江雪》中虽然只有最后一个字是雪,但实际上全诗无处不在写雪。雪的意境贯穿在全诗之中,正是因为雪,才让鸟飞绝、人踪灭,由此也可以看出雪之大,足以“绝”“灭”生物的迹象;大雪纷飞、天寒地冻的环境与老渔翁垂钓的形象形成对比,突出了情感上的压抑、绝望与苦闷。
《我好似一朵流云独自漫游》是华兹华斯对自然之美的深情颂歌,同时也是他内心世界的一次细腻独白,其取材于诗人在英格兰乡村湖畔的一次散步。在诗中,自然不仅作为外在景观被描绘,更成为诗人情感与哲思的载体,展现了人与自然之间深刻而微妙的联系。其中充斥着云朵、山川、花草、微风、银河等自然意象,将人与自然有机结合。在诗的开头,诗人就大胆地将自己比作天上一朵肆意飘荡的云,在山川之间自在漫游,这源于“云给人以自在、舒缓、逍遥等惬意的感受,而且云在西方还是孤独的象征”, 当诗人的目光落在金色的水仙上时,他看到水仙花在微风中起伏摇曳,不禁流露出向往之情。那不仅是视觉上的盛宴,更是心灵上的触动。水仙的摇曳生姿,如同银河中的星辰闪烁,不仅赋予自然以超现实的美感,也映射出诗人内心世界的丰富与多彩。这种美不仅仅是外在的,更是内在情感的外化,是诗人对生命美好瞬间的深刻感悟和珍视。
视角从地面切换到天空,那一簇簇水仙花好似银河中的点点星辰,欢欣鼓舞,无限蔓延;视角从天空切换到了海面,波浪随着花朵跳舞,但水仙的舞姿远胜过那闪光的波浪。但这些在诗人散步时都未意识到,直到诗人回到家中,躺在沙发上独处时,他才意识到这份美丽。华兹华斯巧妙地运用云朵、山川、花草、微风、银河等自然意象,构建了一个既宏大又细腻的自然世界。他将自己比作一朵自由飘荡的云,这不仅是对云本身自在特质的直接借喻,也暗含了诗人对无拘无束生活的向往和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在山川间漫游的云,象征着诗人心灵的漫游,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和对内心世界的深度挖掘。
与《江雪》不同的是,《我好似一朵流云独自漫游》中的意象更加鲜艳明媚、富有勃勃生机,并且意象是动态的:漫游的云朵、摇曳的水仙、轻动的微风,给读者营造出欢脱轻松的氛围的同时,也透露着淡淡的孤独,这是一种属于华兹华斯独特的欢乐与“忧戚(melancholy)”并存的孤独。另外,人迹罕至之处往往象征着孤独。在人烟稀少的山谷中却有极其茂盛的水仙,强烈的视觉冲击与对比加强了诗人的孤独感。同时,通过以银河的繁星比喻水仙的众多,更是将自己独身一人与密布的繁星作对比,孤独感跃然纸上。诗人看似在描写美好的自然景象与风光,实则在写自己内心的孤独。在诗的最后,游荡的孤云找到了伴侣,与水仙共舞,不再孤独,也无须四处飘荡,而诗人仍然是孤独的灵魂。
三、情感的消极与积极
(一)表现手法
柳宗元没有直接写“孤独”,但整首诗的字里行间都让读者感到强烈的孤独感,这也是中外诗歌最为不同的一点。中国诗人善于运用景物来烘托人物,以景寄情、以物托情,通过侧面描写抒发内心的情感。而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西方诗人却不同,他常常使用直陈的方式,直接使用大量的表示孤独含义的词句。在《我好似一朵流云独自漫游》中,他使用了如solitude,lonely等直接表示孤独的词,以及wander,vacant,pensive mood等词间接描写孤独。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外诗人在情感的表现手法上存在很大的不同,前者较委婉,后者较直接。另外,与中国诗歌不同的是,华兹华斯为了表现孤独还常常采用重复(repetition/ reiteration)的手法,但这里的重复并不是单个词语的机械复制,而是指表示孤独的意象、词句反复出现,这使得读者不断去思考到底什么才是孤独,诗人描写的孤独又是什么等问题。
(二)情感态度
柳诗之中抒发的情感是复杂而深沉的,主基调是孤独迷惘、失势之悲。被贬之后,他寄情山水、种植花木、钻研佛学,试图通过这些转移自己的无奈与悲伤,但他始终不能释怀,情绪低落、低沉孤寂。“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不仅是对景物的描写,也是对他心境的描写:在这广袤无垠、寂静无声的天地间,鸟飞已绝、人踪亦灭,营造出一种极致的孤寂与荒凉感;在如此宽阔的天地中没有一丝生机、不见一条路径,孤独和绝望感油然而生,恰如其分地展现了诗人被贬后内心的孤寂与绝望,表达出诗人的绝望和“路在何方”的迷茫。这种景象不仅是自然界的真实反映,更是诗人内心世界的象征——在仕途失意、人生低谷之时,他仿佛置身于一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四周是无尽的冷漠与孤独。在孤立无援的处境中,他只能如渔翁独钓般困守,别无他选。故柳宗元的“孤独”是消极的孤独,是四顾茫然、抑郁落魄、寂寞悲凉的。
柳宗元试图通过寄情山水、种植花木、钻研佛学等方式来寻求心灵的慰藉与解脱,但这些外在的寄托并未能完全消解他内心的痛苦与迷茫。他的“孤独”是一种深刻的、难以言喻的孤独,它不仅仅是对外在环境的感受,更是对自我身份、价值及未来出路的深刻怀疑与迷茫。这种孤独带有一种消极的色彩,因为它源于对现实的无奈与接受,源于对自我命运的无力改变。
然而,正是这种孤独与迷惘赋予柳宗元诗作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思想深度。他的诗作不仅是对个人遭遇的抒发,更是对人性、社会、宇宙等宏大议题的深刻探讨。在孤独与迷惘中,他依然保持着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真理的追求,这种精神力量使得他的诗作能够穿越时空的界限,触动后世读者的心弦。因此,柳宗元的“孤独”虽为消极,却也是其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灵魂所在。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而复杂的柳宗元,一个在逆境中坚持自我、不懈探索的文学巨匠。
与《江雪》中“孤舟蓑笠翁”的静谧孤独不同,《我好似一朵流云独自漫游》中的孤独带有一种更加复杂而微妙的情感色彩。它不仅仅是物理空间上的独处,更是心灵深处的一种自我对话与反思。诗人在欣赏自然美景的同时,也在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感受着孤独带来的宁静与思考的空间。然而,这种孤独并非全然沉重,它伴随着水仙的欢舞、微风的轻拂,以及诗人内心对美好的向往,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欢乐与“忧戚”并存的孤独感。这种孤独让诗人更加敏锐地感受到自然之美,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华诗中表达的孤独是一种积极的孤独,这里的“孤独”是solitude,而非loneliness,根据《柯林斯英汉双解大词典》,“solitude”一词指的是一种平和而愉快的孤独状态,而“loneliness”则指一种因无人作陪而感到郁闷不已的孤独状态。华兹华斯热爱独处,孤独可以给他带来创作的灵感,他写道:“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诗人沉思这种情感直到一种反应使平静逐渐消逝,就有一种与诗人所沉思的情感逐渐发生,确实存在于诗人的心中。”因此,他为了创作常常主动地寻求独处,他的独处是为了更好的相处,是辩证的概念。而这种独处既不是远离世界、远离自然,更不是逃亡与逃避;相反,他认为人与大自然不可分割,自然界对于人类幸福至关重要,这与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得出,华兹华斯对于孤独是向往的,孤独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精神愉悦。
四、结束语
柳宗元等中国古代文人在其诗作中展现的孤独,往往与他们的仕途命运紧密相连。在封建社会的官僚体系中,文人的命运往往取决于皇帝的恩宠与朝堂的风云变幻。一旦遭遇贬谪或流放,他们便远离了权力中心,失去了往日的荣光与地位,这种由外而内的孤独感,自然带上了浓厚的悲观与无奈。柳宗元的孤独是对个人命运无常的感慨,也是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它反映了封建文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存状态与心灵困境。
相比之下,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外国诗人,其笔下的孤独则更多地体现了一种主动选择与内心平和。华兹华斯等浪漫主义诗人强调自然与人的和谐共生,他们通过亲近自然、独处冥想等方式,寻找心灵的慰藉与自由。这种孤独不是被迫的逃离,而是主动的追寻,它让人在宁静中聆听内心的声音,与自然界的万物进行对话,从而体验到一种超越世俗的快乐与满足。因此,他们的孤独带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是对生命本质的深刻领悟与热爱。
这两种不同的孤独观,启示我们以更加辩证和开放的心态去看待孤独。孤独,作为人生的一种常态,既可能带来痛苦与绝望,也可能成为我们成长与自我实现的契机。学会独处,并不意味着与世隔绝或消极避世,而是要在独处中学会与自己对话,倾听内心的声音,从而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理解世界。
参考文献:
[1]白凤欣.华兹华斯诗歌中的自然情结[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4):87-90.
[2]John Purkis. 华兹华斯导读[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3]茅于美. 中西诗歌比较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4]王松林.彼“意象”非此“意象”:中西意象论比较[J].世界文学评论,2006(1):185-194.
[5]王向阳.以弗罗斯特的《雪夜林边小驻》与柳宗元的《江雪》为例浅谈西方的意象和中国的意境[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8(9):94-95.
[6]吴文治. 柳宗元评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7]伍蠡辅,胡经之. 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54.
[8]向若怡.如何理解华兹华斯诗歌中表达的孤独[J].参花(上),2020(8):46.
[9]袁宪军.“水仙”与华兹华斯的诗学理念[J].外国文学研究,2004(5):56-61,171.
[10]袁宪军.华兹华斯的《水仙》与诗歌语言[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2):69-71,90.
[11]章燕.“我孤独地漫游”和“水仙”:华兹华斯诗歌两种题目的考证与比较[J].外国文学,2011(2):38-45,157.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文系
作者简介:杨艺驰(2002—),女,汉族,河北石家庄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