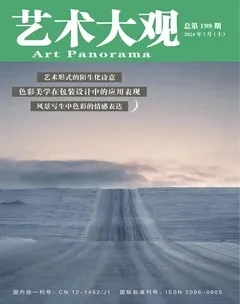表达与呈现——电影剧本创作的有源之水
2024-10-11刘丰恺
摘 要:“表达”与“呈现”,是电影剧本创作的两个核心要素,它们是一种相互依存但呈现主客碰撞的意识,以“呈现”来构建塑造,形成生长;以“表达”来完成信念,实现意义。这是电影剧本创作的两端,它们并非条理清晰的公式,而是一种价值生成的判断。剧本创作要通过呈现来完成表达,作为叙事基础的“呈现”是怎样完成我们从创作的脉络中溯源而来的“表达”,是每一个创作者需要认知和厘清的叙事脉络。
关键词:电影剧作;表达;呈现;叙事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05(2024)19-0-03
生活模仿艺术,电影介入生活,电影剧本创作在当下,既面临复杂的生长环境,同时也在寻找它可能的艺术出口和表达使命。作为编剧,我们更应该清楚,电影剧本的创作不仅仅是一种塑造论,同样,应该是一种表达论。电影在传统娱乐功能和艺术功能的实现外,还在塑造观众的社会意识;它可以推动人们对于某些方面的想象力,修正和改变他们对生活的理解以及自我理解——电影,同样是公共意识的显影。因此,作为一名编剧,既面临着实现愿望的图景,同样也有警惕着自我表达的意识。而这些“旅程”和“目标”,或者说“主题”和“方法”的形成,都应该依托一定的意义系统,或者还原某种生活的既有状态。因而表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绝不能是无源之水,是编剧从概念到概念的迭代游戏,它应该代表某种考量,关照某些命题,因此,我们以表达与呈现为轴线,从创作的角度出发,来思考电影剧本创作的应有之义。
一、风格和样式
毫无疑问,不同的风格样式会决定不同的电影状态。电影类型的多样化是电影艺术存在的特征之一,这是编剧在表达之下应该提纲挈领的基本语言。塔可夫斯基的极具个人特质表达的“诗电影”,希区柯克擅长以精准的剧情和视听调动观众的共情能力,《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以阴暗鬼魅的故事和画面去刺激观众内心的恐惧感,黑泽明的《乱》则用普世的情感链接形成自己的朴素表达。每一个创作者,在思考故事的一开始,都要明晰自己表达的方向,不同的道路决定不同的人物状态,不同的终点需要不同的风景刻画。无论是商业类型片,还是艺术电影,都要有它自己的诉求和样貌。
电影风格是电影美学的一部分,也决定了我们看电影的方式,但当我们从叙事系统的意义介入时,电影风格通常涵盖了不同的电影形式,如叙事类型、记录类型、非虚构类型以及不同地域属性下的集体风格。从叙事上,剧作意义的标准决定创作者对风格变化的理解——是突然的还是逐渐的,是最初展开还是两种力量的斗争?什么类型的解释可以被应用,什么类型的因果机制能够匹配到什么样趋势的影片风格。导演和编剧已经意识到,他们的作品也可以从自我意识参考到风格传统中来定义。风格是可以在文本中被阅读的,对于电影剧本的审视绝不能仅仅是解释性阅读,而应该在理解风格样式和艺术实践的基础上去创作和聚焦。
二、人物
在既有的风格下,我们首先要思考的就是故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人。这个人既包括人,也包括非人,具体来说就是我们故事的主角,这是伴随着我们故事始终的思考。该怎么刻画?他背后的痛苦和真相是真的吗?作为编剧,我们应该很清楚这个人的一切,他的性格决定他的选择,他的状态完成他的动作,他的历史构建他的故事。在现代的剧本创作中,要切忌从概念划入概念,这样的创作方法形成的只是某种景观,某种形象,而不是真正的人的故事。无论是新现实主义的发生,还是好莱坞电影的兴起,我们追根溯源,会发现打动我们的,一定是事件之下的人的喜怒哀乐,一定是作为故事核心人物的挣扎和痛苦。电影作为一种开放式的提问,在完成娱乐使命的同时,一直都在给这个世界提出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思考都是源于关注人的本身。
那么,我们如何去塑造我们的人物呢?
首先,要去寻找的主人公,要对主人公完全了解,我们要知道他的性别、年龄、职业、身份,他的恐惧是什么[1],他的爱好和隐忧是什么——人物的历史支撑人物的性格,人物的性格决定人物的行动——人物是特定环境的产物,塑造人物性格本身就是在建立一个世界。其次,建立有效的人物关系。和生活一样,电影中的人物关系有很多种,但是为了具体地、清晰地呈现我们的表达,一般来说人物关系往往会有一定的设计:如冲突型、对比型以及映衬型等。但需注意,一定要符合人物真实生活逻辑和生态链条。同时,在剧作中,所有人物关系的设计和发展都服务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因此我们要从人物的心理情感和戏剧动机出发去厘清人物与故事、与情节之间的关系,万不能本末倒置,使得人物性格屈从故事情节。
只有普通的人,没有普通的主角。
三、故事
这里所说的故事,既包括我们完成创作的素材,也包括我们将之形成的故事文本。这来源于我们对生活的积累和经验,这种积累既包括文学系统给予我们的滋养,也包括社会事件带来的感知,同样包括日常状态迸发出的灵光。作为创作者,我们要尽可能敏感地触碰和思考,勇敢地探索和捕捉。每一个好的故事后面都藏着一个社会,每一个完成的剧作后面都装饰着漫长的生活。
那么,电影剧作中的故事属性有哪些呢?
(一)戏剧真实和生活真实
电影本质上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有它自在的逻辑链条和价值体系。戏剧真实是指我们在故事本身的系统中能够形成一个自圆其说的,逻辑合理且前后统一的世界状态。戏剧真实可以取材于生活真实,但不必完全服从于生活真实。比如乔治·卢卡斯的《星球大战》系列,里面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外太空,并且有着并不契合日常的光剑、飞碟等武器,但该片本身就是科幻类型,其需要做到的是影片自成世界中的真实和完整。我们经常会看到这种情况,一个在大众看来离奇且不合理的桥段,新手编剧往往会说:“这是我身边真实发生的事情。”注意,真实发生的事情只是我们创作故事的题材,它并不能成为解释戏剧桥段的原因。
生活真实、艺术真实、逻辑真实要触碰到剧作中的心理真实、情感真实和想象真实。
(二)具备故事条件的要素
野田高梧在“剧本结构论”中提出,“角色”“行为”“环境”是故事成为剧本的三个要素[2]。比如,“院子内”是环境,“一个老奶奶”是“角色”,在“晾衣服”的“行为”中会省略一些诸如“衣服挂在绳子上”“慢悠悠地走过去”这些成分。
具备这三个要素能够成为剧本吗?也未必。这三项是故事成立的要素,但光有这三点还不够,还需要一定的戏剧牵引力作为轴线把它们串联起来,也就是说,一个剧本中的不同故事之间要有有机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发展的、流动的,它们共同指向创作者期冀从这个文本中表达的态度。仅仅是一份日常状态的记录不足以成为故事,连续的A、B事件是没有意义的,它们可以是对方的发生前提,也可以是必然因果。因此,要完成一个故事,我们要对现实生活中的事件进行合理的取舍和分析,未必按照事件的原有顺序来写,要将其并置在统一逻辑故事的操作之下,清楚彼此之间的对应关系和意义。
另外,具有和时代连接的故事需要被表达。每一个时代都要紧贴时代的声音,但又正是无数个体的消长进退,才成为此时此刻的人类图景。故事通过内容去反映一个时代,也通过创作记录一个时代。
四、情节
故事不等于情节。故事是画布,情节是让故事展开的具体笔触和顺序。精彩的故事情节,既包括静水流深的温情表达,也包括荡气回肠的情绪渲染,同样也涵盖提心吊胆的阴谋诡计。不同风格的影片需要不同程度的编排和设计,这是电影剧本创作的功能和手段。大卫·波德维尔在《剧情片中的叙述活动》一书中,对电影叙述者有这样一番论述:“在看电影时,我们很少觉察到是在听一个类似于人的实体在告知什么。因此电影叙事更易理解成为建构一个故事而提供的一套信号的组织。”我们很清楚,这套信号的组织是否得当,逻辑是否严密,情理是否通畅,决定着倾听者和叙述者的认知连接。
如何赋予情节一个基本的剧本结构。
首先,因果意识。
E.M.福斯特曾举过一个例子,“国王死了,然后王后死了”,这是一个故事。“国王死了,王后悲痛欲绝,也死了”这就是情节。相比于故事,情节上面不仅有时间上的确定性,更有前后上的因果关系。情节的最主要任务就是在发展变化的事件中,有一条指向主题的暗线牵引彼此。我们既不能一味地追求文本的复杂,情节的复杂,也不能忽略那些重要的,具有戏剧功能的情节节点。需要慎重的是,在繁冗的故事情节中,我们往往会忽略对于人物的关照。相比于宏大而整体,我们更倾向于细节丰富而情节简洁的叙述。
其次,要有发展变化。
在基本的故事情节中,往往都是单向度的因果指涉,这相较于我们复杂的人生来说,总是会变得单薄,因此创作者必须清楚,我们在设计情节时,直线式的由一个事件推出另一个事件,由一种因推出一种果这种方式难免会显得悬浮。用简单的情节、复杂的情感呈现出真实世界的哲学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们要让我们的情节在前后的推进中,跟随人物的心理变化而发生流动的、内在升级的、具有偶然中的必然哲学样式的前进规律。
小的情节可以暗示大的人生,如何在蜿蜒前进的故事脉络中找到生动而有机的戏剧情节。就像挖洞一样,好的创作是“开的口子小,而挖得深”,好的创作是从宏大叙事回归到一个真正的人,从呼喊口号降落到幽微而具体的情节中。
同时,我们设计故事情节时,细节也体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电影来说,在一个精彩的故事框架下面,往往影响故事情节又很容易被忽略的一点,就是作为细节的叙事力量。我们往往能从细节中分辨出一个故事的重量,也能从细节中去完成叙事的推动。在是枝裕和的《无人知晓》中,细节是桌角上逐渐暗淡的口红,在无声中表现了时间的流逝;在阿巴斯《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细节是小男孩阿穆德在作业本中发现的小花,那是漫长一夜中收获的金子般的自由;在《霸王别姬》中,细节是寒冷的北京城中,程蝶衣被断指的隔壁,正是段小楼被规训的叫喊,两人的生命在如此不经意的细节间勾连起来。《春夏秋冬又一春》中的细节是围绕不系之舟般的佛宇延伸而来的各种符号,贪玩的童僧、患病的少女、心经、佛像、古木、寒冰、落雪、老僧等,这些细节的意义,需要每一个观看者根据自身的经历、性格、职业、婚姻状态等去同构完成。它是复杂的,也是模糊的,这是细节在剧作中的突围。
以上,便是在剧本创作中,作为“呈现”的几条轨迹,它们有先后顺序,但绝对不是孤立,它们有创作意识,但不应该是保守,艺术创作是多元而无知的,这些呈现的实现,告诉我们电影剧本创作的某一条红线和基准,它会让我们更加明晰和洞察,更加谨慎和自由。然而,这些理念的生成,归根结底是为了一个形而上的主题服务。
那么,何谓主题?
1.主题要有指向性
区别于具象化的故事,主题本身具有抽象性。很多时候,主题往往由一个概念出发,但要明确的是,概念本身也不是主题,具有方向性的作者判断才是主题。比如,“爱情”“父爱”“母爱”都仅仅是一个概念,并不能成为主题。罗伯特·麦基在《故事》当中提道:一个在冲突的深度和广度上进展到人生体验极限的故事,必须依循以下型式来运行:这一型式必须包括相反价值、矛盾价值和否定之否定价值[3]。因此,我们的主题需要有判断,有指向。比如,“极端的爱就是恨”“缺位的父爱不算是爱”“越界的母爱是深渊”等。
2.主题不是创作的目的
在一开始,我们就强调,避免让剧作成为由概念到概念的迭代游戏,因为这样的创作路径往往会遮蔽故事真正的人物和情感。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是先有主题,还是先有人物?这个问题本质上并不重要,无论从哪个角度入手,最后回归到有机的创作屋檐下的,一定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万不能向某一方坍塌,尤其是借由概念性的主题推导出概念性的戏剧事件,剧作绝对不是冷冰冰的数学公式。电影艺术发展到今天,非常艰难的一个现象是,很多创作者的理论知识和人文知识极其丰富,却难以变成有效的剧作语言。很多具有叙事能力的创作者又鲜有对社会时代,对主题把控的感知能力。由理论到叙事,并不是一件易事。主题是创作路径上极其重要的一个链条,但绝不是目的。
表达凌驾于呈现之上,但并不是裹挟。好的表达引导精彩的呈现,好的呈现走向独特的表达。这种角力式的动态平衡,构成了剧本创作微妙而自洽的内在讲述途径。回到最初,我们试图找到电影剧作的有源之水——“表达”与“呈现”的关系,以及思考我们作为编剧在此时此刻的诉求和理解。我们借助光影声画的呈现,实现某种主题的意义所在。当艺术进入现实,才能改变现实。
以表达和呈现为建筑材料,搭建了一个剧本理论的微型景观。将剧作理论的存在转化为创作的场域,而这片场域的意义系统对我们所有的今天的创作者,必然形成有效的话语机制。电影剧作正在和其他艺术一样,不断探索自己的秩序和身份序列。它逐渐涵盖了自然、音乐、科普、人文艺术、运动等多个领域,但艺术的探究一定是在历史或者在时代的脚印里逐步前行的,因此无论是创作者还是理论研究者,一定要秉承时代的脉络,寻找历史的回音,在反思和追问中溯源故事创作的自我完形,在不断拓宽的电影语言中,建立自我与电影与世界的可能面貌。
参考文献:
[1]黄丹.人物的历史与性格——谈电影剧作中的人物塑造[J].电影文学,1999(06):43-45.
[2][日]野田高梧.剧本结构论[M].王忆冰,后浪,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9.
[3]罗伯特·麦基.故事[M].周铁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