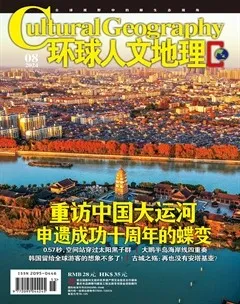南长滩,北长滩
2024-10-10唐荣尧
黄河流过黑山峡中的小观音后不久,两岸对排的群山像两个商量好即将要决斗的摔跤手,身子向下稍微一弯——山势稍微减弱了一下,各自朝后退了半步——给两岸各自腾出了一片狭长的滩地。隔河相望的两片狭长河滩,南长滩是黄河流入宁夏的第一个村,南长滩对面的村民所称呼的《景泰县志》中标注的“北长滩”,则是甘肃省辖内黄河最东边的一个村。
南长滩是宁夏迎迓黄河的第一村,如果从沙坡头区前往那里,得沿着腾格里沙漠南缘的338国道往西而行,至甘肃省景泰县草窝滩镇辖内的十里沟沟口,再顺着这条干沟往里走,两边的山坡因为煤矿开采而裸露着废弃的煤渣,让人恍如进入一个黑色世界。沿途会依次经过由几户人家构成的翠柳村一组、二组,直到河边的翠柳村六组,这里就是当地百姓叫的“北长滩”。我赶到河边时已是黄昏时分,两岸群山犹如双唇,一河涛音自那双唇间流淌而出,吹奏着一曲古老而神秘的歌谣。
从小在黄河边长大,我知道面对大河该有的敬畏与礼数:晨不越山,暮不过河!于是便在暮色中的北长滩台地上寻找扎帐篷的地方。河流是有口音的,并能将这种口音灌输给流经地区的村子。黄河在甘肃省境内流经哈思山后,至下游100多公里的长滩一带,被两岸百姓称为“下河”。这一带人说话基本保持着和上游地区不一样的“语言孤岛”,我的乡亲和这里的村民说的就是“下河话”。
乡音是一台拆除听力交流之墙的推土机,我用下河话一张口,就消除了和村民们对话的障碍。炊烟在屋外的巷子里窜着,我坐在海德格尔笔下的那种“主人的角落”。这里和此时都没有带硬币味道的“诗与远方”,而是有着久违的乡情,有被河声洗刷干净的人心和古老的生活场景。和几位村民在罐罐茶的香气里粗饮,随时会听见谁家小伙子开着拖拉机去翠柳沟的小煤窑里拉来了一车煤,谁上午在地里干农活时和婆娘打了一架,昨夜有狐狸钻进谁家的鸡窝里偷走了一只鸡,谁家的毛驴跑到河边喝水时竟然莫名其妙地冲河面干嚎了几嗓子……对那些路过乡间的游客或想获得一点采访资源的作家来说,这些细碎如乡间路上石子般的话题是没有意思的,但它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亲切,觉得他们谈这些时没把我当外人。其实大河边的不全是波澜壮阔的战争、移民、安置等“史诗般的生活”,更多时候是由这些鸡毛蒜皮甚至有妇女因生活不如意而投河的悲剧构成,这才是河赐予村庄的另一种真实和礼物。
大河南北两岸的村子,在没有出现渡船前,一直靠羊皮筏子的摆渡来保持和对方的联系。两岸之间的往来,让两个村子就像两棵大树,根须向下,向对方所在地不断延伸。那道亲情的根须,连峡里深不可测的河水也阻挡不住,跨山越河般地向对方所在的村子伸去。隔河而居的两个村子,像是以河为棋盘的两个棋手,对望、交流中称呼对方“对岸的邻居”而不是“甘肃的北长滩”或“宁夏的南长滩”——这会被认为缺乏亲情与温暖。
千百年来,扯不断、理还乱、分不清、辨不明的乡情、亲情,如同一口大锅中烩着的蔬菜与肉,散发出浓郁的香味。北长滩村里姓周的和姓胡的多,不少人娶南长滩的女性。南长滩因为地处偏远,女儿往往多是嫁往外乡,未婚男子只能向南翻越重重大山,到山南侧地属甘肃省靖远县的北滩、永新等乡镇去讨媳妇。
一条黄河隔着两个村子,若是错过了白天的摆渡时间,有什么要紧事时,人们会赶忙跑到黄河边,冲着对岸就是一嗓子。犹如从一管唢呐里钻出来似的,穿越河风和涛声的下河话抵达对岸后,对岸住在河边的人家跑出来人,听清楚对方的意图后,会去村子里传个话。不像如今,有了手机,有什么事一个微信语音或电话就能解决。
夜幕逐渐降临,从村子里返回到帐篷边,我把从河边找到的枯木点燃,开始熬粥,完后拿出自己带的饼子,打算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自己的晚餐。忽然看见有手电筒光从村里传来,原来是黄昏时分去村里采访过的摆渡多年的村民胡广智和周世成觉得意犹未尽,打着手电筒穿过夜色而来,在我扎好的帐篷边,就着一河水声讲述两个分居黄河两岸的村子的故事,使我头脑中增添了更多关于南长滩的印象。
山河隔阻,南长滩和外界的交往只能依靠古老的羊皮筏子和后来出现的渡船,从声轻似无的划筏声到吱吱呀呀的划桨声再到突突突的柴油机声,一筏飞渡,一船飞渡,往来间驮负着对岸的南长滩村民们千百年来走向外界的梦想,也构架着对岸和外界的联系。从古老的皮筏到小木船再到现在的机动渡船,水上交通工具的变化书写着对岸那个被河流和群山阻隔的村子通往外界的艰难和努力。
千百年来,浑黄的水面上,一只只渡船、一次次摆渡,送走了多少水边的风情,洗衣的、放牛的、驮水的人影不见了,甚至,随着电器的盛行,连炊烟有一天也会消失,何况还有被涛声埋葬的皮筏制作手艺和民歌小调。河流读懂的是另一种沧桑。
皮筏也好,木船和机动渡船也好,大多的时光里,它们驮负的主角一直是这个小村的村民。和众多散落在黄河边上的无数小渡口一样,长滩渡默默地陪伴着这里的山、水、人、事,让时光老去,让记忆发潮。当年范长江乘坐羊皮筏子顺流而下,留下了对黑山峡的文字记录,却没有关于南北长滩的只言片语。同样,中国第一位女飞行员林鹏侠乘坐皮筏漂流经过这里时,也是匆匆而过,没有留下多少记录。瑞典生物学家安特生、日本学者沪友会、中国学者顾颉刚等等,文人也好,探险家也好,筏客也好,商旅也好,一筏飞渡而过,河水是忠实的伴侣,两岸的村子是匆匆闪动的眼球。没有人书写过这里的掌故风情,即便有若干篇游记出现,也只是应和一下旅游开发的热潮。这些游记或感慨,既不像张承志笔下的大河家(黄河从青海流入甘肃时经过的一处村庄)因一纸文字而出名,也不像风陵渡、茅津渡因为厚重的人文历史被史书收藏。
南长滩就这样寂静地僻远着,长久地孤独着,连个照应都没有。那个晚上,漫天星光下,我在黄河北岸的台地上,坐在篝火熄灭良久的灰烬旁,我在5米之外的地方看着黄河,想着5000年间的这条峡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