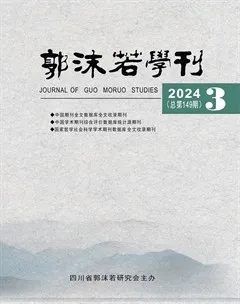继续夯实中国现代出版与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
2024-09-30咸立强
陈思和老师在《试论现代出版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1993年)一文中指出:“现代出版业已经成为知识分子以思想文化为阵地,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钱理群教授在《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纲》(1997年)中认为,直接影响和制约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三大文化要素(背景)是出版文化、校园文化、政治文化,由此提出要“有计划地逐步开展20世纪文学市场的研究,推出一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出版文化丛书》。第一批研究对象确定为商务印书馆(含其主办杂志,下同)、泰东书局、北新书局、开明书店、现代书局、良友图书出版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出版文化丛书》第一本是刘纳教授的《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先行者们的研究设想及其实践为后来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也让后来的研究者们看到了更多的可供补充和进一步研究的点。以泰东图书局与20世纪文学(市场)的关系为例,与创造社合作时期是其“全盛时代”,“全盛时代”之外还有许多值得继续深入挖掘的空间。如果只是盯着泰东图书局的“全盛时代”而忽略了其他,就不能全面地把握泰东图书局与20世纪文学(市场)的关系。和创造社合作之前,泰东图书局直接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纯文学社团——上海新潮社,出版了《新的小说》。创造社脱离泰东之后,泰东像扶持创造社一样,成了白露社的“托儿所”。在泰东图书局,白露社几乎就等于是创造社的复刻。白露社打出来的也是“为艺术”的旗号,文字中也透露出想要打倒文坛偶像的意思,他们编辑的《白露》半月刊(后来改为月刊)是泰东图书局出版发行寿命最长的一份刊物。与《白露》半月刊几乎同时刊行的,还有《泰东月刊》,在革命文学的研究中,这是一份被忽略了的杂志。总而言之,即便是泰东图书局这样一个正在慢慢被人遗忘的小书局,与20世纪文学(市场)关系的研究仍有继续研究的空间和价值,仍然有大量的史料有待搜集、整理和研究。
本专栏四篇文章,第一篇是陈思和老师在这次“新书业与左翼文学的发生——泰东图书局创立110周年暨《中国出版家·赵南公》出版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我的创造社研究肇端于读博时跟着陈思和老师做的课题,而撰写《中国出版家·赵南公》的远因也在于此。当我有机会筹划学术研讨会时,我就想要邀请陈老师出席。我知道陈老师没法去广州,所以就设法把会议办到了老师家门口。即便是这样,也还是差一点没能请到陈老师。会议召开前一周,陈老师告诉我就不提供发言题目了,因为需要过几天等医院里的检查结果出来才能知道能不能出席,让我先把他放在致辞部分。非常非常幸运,陈老师来到了会场,在开幕式上讲述了他和钱理群教授对出版研究的交流,以及自己从事出版、研究出版的心得。这篇文字是我请学生按照录像整理出来的,总感觉有些地方没能复现老师发言的原貌。泰东图书局孵化出了许多中小出版机关,如光华书局、创造社出版部、儿童书局等。第二篇论文的作者刘天艺副研究员从一则新发现的创造社出版部第一次募股章程出发,精到地剖析了“银钱”事项对创造社人际关系的影响,切口虽小,所见甚大。第三篇论文的作者金传胜副教授考证了张静庐回忆录《在出版界二十年》中与周全平等人相关的三处史实,他对张静庐回忆录中“隐笔”与“曲笔”的揭示告诉我们,以回忆录作为论述的证据一定要谨慎。当事人回忆出来的出版史实虽然在场感很强,却也需要注意其中存在一些“陷阱”。第四篇论文的作者邢晓航还是一位在读硕士研究生,她对白露社做了一番梳理,资料工作做得还比较扎实,更年轻一代研究者们的成长才是继续夯实相关研究的生力军!